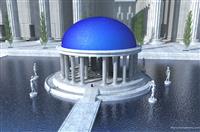一年前在鲁院进修时,认识了北京文友,笔名叫燕子的王姐。由于同年不同日生人,我们姐妹成了课余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当看到她的散文关于非典时期一位白衣天使纯真爱情的故事时,为她清秀的笔锋和美丽的故事情节而深深吸引。她以前当过兵,有大兵的直率坦诚,复员后在大企业里干政工,又有管理人的深沉矜持。总之他乡遇知已,我们一见如故情投志合,相处十分默契。
一年后的金秋九月,我因去北京出版社送审稿子。她得知后匆忙从丰台驻地坐两个钟头的公交,来到我下榻的招待所等候。但事与愿违,我坐的火车晚点,她苦苦等到晚六点方才怏怏离去。
我在她走后十分钟到达。听山东诗人陈景老弟说起王姐很失望的神情,我感到既遗憾又歉意。晚上打通电话时,我竟然不好意思再邀请她了。这么远的路,路上这么多的车堵塞,怎好张口呢。可王姐却爽快地说:"明天一早我去看你。你这么远来京,我们怎么能不见面呢。"那直率中流露出一丝淳朴,那淳朴中包含着一丝情愫。
翌日上午,我和陈老弟在电脑旁审核稿子。可心绪却随着鼠标的游动,飞来飞去飘泊不定。约十点钟,另一位文友杨大姐从东城赶来了。她也是听说我们汇聚北京,正打点滴的她,立刻让儿子开车,专程从东城区赶到海淀区外文出版社。杨姐比我们大十来岁,是最早一批下乡的北京老知青。
我们几个文友相聚在一起,兴奋地谈论一年来各自的情况。杨姐说由于赶写一个知青中篇而累倒了。家中老头风趣地逗咯她,千万不要为文学献身啊!望着年届六旬的大姐双鬓斑白、倦容病态的表情,真为她对文学锲而不舍的执着劲而深深地感动不已。
杨姐由于身体不适,握手告别。当那白色轿车一溜烟儿离去,我的心也就像断线风筝一般。王姐还能来吗?突然手机响了。哇!原来就在杨姐的车拐弯处,王姐急匆匆走下了公交车。
真是无巧不成书,该着有这个缘份吧。我的心悠然轻松起来,王姐依然是那种坦城直率、大大方方的模样,说话直言快语、果断利落。我们几位文友再次聚到了一起,大家在《人民画报》门前合影留念。
言谈话语中得知燕子停飞了。我十分诧异地问:"你挺有天赋的,为什么停笔了呢?"她说出了好多写者类似的想法:整天爬格子太辛苦;写出来的东西无人问津;稿子水平有限不能发表刊登。接着她心满意足地说:"我现在也挺忙乎的。早上去公园晨练,然后上街买菜做饭。下午与同楼退休的姐妹玩玩牌,晚上又去广场练歌跳舞,自我感觉也特充实。"
"难道鲁院进修的学业不就荒废搁浅了吗?"我不解地质问她,她竟平淡地一笑:"五十岁的人了,还能写几年?"我说:"写作没有工龄年限,你看冰心老人,百岁还给孩子们写书呢。再看杨姐,六十多岁了,写中篇都累倒了,还不辍笔呢。"
王姐似乎增加了自信,将我手头散文集的复印稿整理了一些,她不好意思地说:"谢谢你们的鼓励,回家后我要好好温习一番。"
目送王姐离去背影,我万分感慨:去年的燕子还是踌躇满志,满腹经论,展翅翱翔在蓝天碧空中。而今怎么就被舒适安逸的生活而竞折了翅膀?心中不知不觉萌生一丝淡淡的惆伥。
在文学这辽阔浩瀚的蓝天上,燕子你还能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