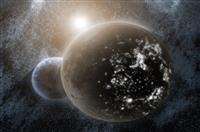
我是一个没有个性的人。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周围环境中充斥着各种有个性的宣言。我有一个迥异于周围大多数人的童年,因为这个,曾经很多年我一度以为我将会是一个长大后迥异于大多数人的人,比如伟人,比如名人。可是后来长大了,我长成了一个混在人群中找不出的路人甲。
在学校的时候,我的成绩不上不下,我也不是一个叛逆张扬、让人头疼的学生。我的存在如同影子一般,沉默而安静。在所有人眼里,我都是一个安静乖巧的没有存在感的存在。除了我自己,谁都不知道有时候我内心癫狂得想与这个世界同归于尽。
他曾经说,你知不知道你有时候沉默孤僻的样子有几分神秘的感觉?
那是这种神秘的感觉吸引了你吗?我不以为意地笑。
我和他的相识说来有些戏剧化。
我中学毕业后来到这个我向往的大城市,在这个地方一个没有学历的年轻女孩能找到的正当工作就那么一样,我做了一个饭店的服务员。那天我本在给他们那一桌倒酒,背后有人猛地一撞,大半的红酒都撒在了他的衬衣袖子上,晕染开来,像颓败的红梅。我有些慌,虽然马上道歉,却不知道遇到这种事会以怎样的结局来收场。
最后我只记得的是他温和的笑容,这种笑容,我从没有在其他人脸上看到过。
后来他又来过两次,和不同的人,每次都会跟我打个招呼,寒暄两句或者开个玩笑说上次便宜我了,应该让我帮他洗衣服。闲下来时,我看着坐在人群当中,言笑晏晏,从不会使人感到寂寞。
后来有一天他突然说要请我吃饭,在肯德基里从不多言的我咬着可乐的吸管跟他闲扯了一下午后我才突然明白,我只所以不爱说话,是因为找不到那个一直愿意听下去的人。
我总会跟他说我经常做的一个梦,一个面目模糊的人在孤岛上,海水从四周涌向他。你到底经历过些什么?总是这么悲观。他吻上我的唇,他的唇不像他的人,冰凉,还有些粗糙。
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单亲家庭的孩子都或多或少有些心理阴影。我也不知道我算不算是单亲家庭成长的孩子。或许,曾经是。五岁那年的记忆是很不好的。黄沙漫天,天幕昏黄的春天下午。父母的争吵声。破碎的杯盘碗盏。暗红色的汤汁挂在雪白的墙上,触目惊心,像一滩肮脏的血。然后是一天的风沙,一段巨大的空白。那是1998年的春天。
1999年秋天,我随着冷漠的母亲去了一个极为偏僻、极为原始的村子。在外面的世界霓虹闪烁、楼高入天,网络悄然兴起,正一步步联通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村子古老原始的如同与世隔绝的桃花源。但她不是桃花源这里是进行古老原始罪恶的好地方。尽管村子里的人看起来都很淳朴善良,可无知愚昧是最残忍的罪恶。那年冬天村子里出了件大事,生出个葡萄胎。是一个十六岁的女孩生的,这个女孩去年刚中学毕业,出来打工被人贩子拐卖到这个遥远省份的偏僻村子卖给村中人,逃跑多次未果,做了会生育的工具。村子里有很多这样的女孩,但她们谁也见不到谁。我很渴望外面的世界。
2000年年后我在大人们躲躲闪闪、小孩们明目张胆的议论声中入学。在这个新的村子,很奇怪大家为什么对我的家事知道的那般清楚。人们都在传我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或者是有一个蹲大狱的父亲的孩子。那年夏天,半夜里我在潮湿闷热中醒来时听到陌生男人的喘息声,旁边母亲的被中有隆起的黑影。我害怕,我只能装睡,紧紧抓着被角,一动不动,渴盼天亮。
那年的初冬,天气越来越冷,家里的空气也很冷清。我放学回家,母亲经常是一个人早早蒙上被子躺在黑暗中。我默默地将冷掉的饭热一热,吃掉后将碗洗掉,我七岁了。我常常祈祷上天能让我快点长大,这样我就可以不用再面对这一室孤清,也可以控制我的生活,控制那个常常脾气莫名爆发,打我,掐我,又常常莫名哭泣的女子,我的母亲。
我喜欢外婆,她不是一位慈祥的老人,但她会笑会生气,跟她在一起没有那种孤清的感觉。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母亲就像一具活的尸体,幽凉阴暗。大年夜那天晚上,我看着她早早躺在惨白色的灯光下,听到外面的爆竹声觉得有点寂寞。我盼望外婆来,可她来不了了,她已经下不了床,并且在三月的一个晚上死掉了。我想,为什么我们大家不一起死掉呢?
我不喜欢跟其他孩子一块出去玩,我总担心会错过什么。我明明是喜欢热闹恐惧冷清的啊,但我自己终于也变成了一个冷清的人。我不爱说话,不爱动,经常发出像母亲一样深夜幽灵般的叹息声。有人说我不像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像一个八九十岁的古怪老人。我确实不是个孩子了,因为我身边已经没了大人,母亲走了。我不知道她去了哪里,什么时候走的,有人说有一天早上看见母亲穿着黑色的大衣,拿着黑色的包。我爱她,但她再不会回来了。而父亲,父亲也不会回来了,他越狱逃跑,被击毙了。
我很小的时候一直想着我要到外面的世界去,有一份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一个家,有一个会笑会生气的家人。
我不知道他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他是我第一个这么亲近的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业务员,二十四岁,大学毕业两年,家在陕西。这是我所知道的关于他的全部。他从不问我的家里情况,我也不愿问,更不愿说。他是一个能让我汲取温暖感到热闹的人,有这点,便足够。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我的梦想,但是每次看到他那温和的样子,我总要忍不住跟他谈起未来,我小时候的梦想。他笑笑,说,好。虽然知道话语是最靠不住的,但我需要这一秒的慰藉来填补内心的恐慌。我想,我不是母亲,我终归是个比她幸福的女子。
这个城市的天气越来越冷了,他的情绪最近似乎也不大好,经常把自己关在洗手间打电话,我一进去就停止说话,怕被我听到什么的样子,我心里有种不安的感觉。
这种不安的感觉得到了证实。回到我们一起租住的房子,他在收拾东西。屋子本就不大,纵使他的行李很少,仍旧搬空了一大半,空荡荡的感觉像可怕的未来迫不及待地要将人吞噬。
家里有事我要回家几天,他说。
你是不是不回来了?我沉静地问。
他愣了一下,皱皱眉,你胡思乱想什么呢?顶多一星期我就回来。这次回去我就把我们的事跟家里说,下次就能带着你回去了。
看着他这副安然的样子,我渐渐安下心来。夜里,我又做了那个个梦,梦见一个面目模糊的人在一座孤岛上,海水慢慢从四周涌来,一点一点将他淹没,海水涌到脖子上,他没有出声。如同一只孤独的鸟。
醒来时我有些不辨时间,发丝湿润凌乱,贴在脸颊上,就如同潮湿而粘稠的生命。茫然了好久才打电话给他。他的声音隔着嘈杂的人声传来,是人世的温度。但我没想到,那是我迄今最后一次听到他的声音。
两天后一直到如今,我一直在拨那个电话号码,一直无人接听,我这才想起除了他的姓名年龄,我对他一无所知。我的心慢慢地沉下去了,其实是我一直不敢面对那个答案。他总说我悲观,可我没说出给他听的是,如果一开始我不悲观,还存有希望,那最后面对那个没多次预想过的结局,我会更绝望,就像现在。
昨天才惊觉我已经两个多月没来月经了,出去买验孕试纸,是阳性。外婆死了,母亲不要我,父亲无法要我,他不见了,这个孩子,如果有机会出生的话,不知道他会不会跟所有人一样。我看着窗外阴影中那些早已枯萎却仍旧凌乱纠缠的藤蔓,想着如果生命也能这样,枯萎时还有人与你纠缠不休,该多好。
夜里我又做了那个梦,海水四处涌来,一点一点,慢慢没过头顶,我一点点靠近,那个人,是个女人。终于看清了,那张脸,我早晨从镜子里看到过,苍白如同鬼魅。醒来看着空荡荡的屋子,我醒悟过来为什么她任由海水淹没而不呼喊,她在一座孤岛上!无法呼喊,在这个寂静的世界,没有声音,只有孤独,绝望的孤独,永恒的孤独,孤独到窒息。
这个城市的天气越来越冷,也许明天就会下雪,我还在等着有人回来,也许永远不再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