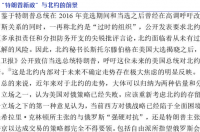核心提示
■ 书籍具体有形的特性,本身就是创造性天才的标志,是代代相传的文明薪火的标志。
■ 手稿的文字常常难以辨认——充满各种错误,但手稿正具有一种诱惑力,是出版了的书籍不具有的。
■ 世界范围的文化是我们共同的事业。但它首先是读者的责任,也是出版商的责任。
想象一下,若没有书籍,我们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
玛雅人在这一点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十世纪的墨西哥。灿烂的玛雅文化创造了代表人类知识的一切:艺术、科学和哲学。但是他们却不知印刷术,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消亡了。
想象一下,如果古登堡没有应文艺复兴之需,适时采用中国人的发明,创造活字印刷术,那么一切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无法想象一个没有书籍的世界
如果没有印刷的书籍,我们的世界将完全不一样。也许它会同鼎盛时期的埃及社会、玛雅社会一样:一个封闭的世界,很难受什么影响,不公正与不公平盛行,严重失衡,无可救药。
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一如我举的例子,古时的玛雅世界——没有民主,法律面前鲜有平等,公民道德水平更是低下。大部分民众,屈服于某几个权高位重的教士、某个太阳王、某些暴君、某些武装的独裁者统治。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处于有教养的僧侣统治之下,在那里,艺术、知识、技术慢慢发展起来,但只为少数人服务。
在这样的一种体制下,知识不是用来交流的,也不是用来谋求民众的进步。它主要是用来在掌握知识的人与大部分只识图画的人之间设立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建立宏伟的庙宇、富丽堂皇的宫殿,甚至像埃及那样,建立金字塔那样令人称奇的墓穴。人民大众,则像奴隶一样建造着这些工程,甚至都不理解这一切的意义。这就是怪龙之社会(la societe du Dragon),正如普洛普在民间故事分析中定义的那样。
没有印刷术,没有文字,我们的文明,西方的或东方的,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也许就会变成过去那些专制而奢华的社会。它们完全依托某个拥有特权的精英人物,埃及的法老、罗马的帝王或者像尤卡坦的玛雅真人(Vrai Homme),这些社会极其脆弱。一点点微小的事儿,一场饥荒、一次传染病、一次宫廷暴乱就足以摧毁它们,使它们化为乌有。野蛮人进入罗马时,暴君的长期统治与部落之间的斗争已经将整个国家摧毁殆尽,而这个国家曾是地中海的绝对统治者。西班牙人深入美洲印第安大陆时,玛雅人辉煌的城市、摩天庙宇、镀金的宫殿已经成了被森林覆盖的废墟。饥民的起义或许推翻了暴君的统治,但是因为缺乏技术手段,他们荣耀的祖先的功勋和知识如今已经难以辨清了。狄亚哥·德·兰达甚至都不需要焚烧手稿、打破神像:它们已经停止存在了。
重写历史总是很吸引人。对于我这样的小说家来说,这可以让心灵得到满足,这对衡量文化与文明的相对性不无裨益——这也使保尔·瓦雷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得出了一个醍醐灌顶的结论:“我们这些文明,我们现在终于明白,我们总是会消亡的。”
事实上,我觉得根本就无法想象一个没有书籍的世界。诚然,现在存在其他传播知识的手段,通过图像、计算机。也许这些新的手段有一天会完全取代古登堡的发明。但,书是与人类文化相关的事物,不仅与他的思维方式相关而且与他双手的形状相关——是一种工具,可以与其他不可或缺的工具如锤子、刀、针、开水壶等相提并论——也可以与其他精致的工具如小提琴、长笛、打击乐器、毛笔、砚台等相提并论。
很难想象有一天书会变成虚拟交流的附属物。书籍具体有形的特性,本身就是创造性天才的标志,是一代代流传下来的文明薪火的标志。也许是一本法律书,一本艺术书,一本力学专著,一本化学或数学书。也许是一本反抗诗集,就像韩语诗人尹东柱(Yong Don Ju)在被日本人枪杀之前所写的关于星星的诗歌,也许是一本现实主义的小说,像老舍的《正红旗下》,也许是一个松散却充满启示意义的故事,如《爱丽丝漫游仙境记》,也许是一本关于生存之道的范本,如伊斯兰苏菲派教徒鲁米的启示录,或者像罗马国王马克·奥勒留(Marc Aurèle)的勇之箴言。抑或,是书中之书,如古登堡曾经印刷的《圣经》,这也是(西方)出版史上印刷出版的第一本书。
文学也有其世俗一面
我对于文学的思考也涉及其世俗的方面。
与小说家威廉·斯泰伦(William Sty-ron)、米歇尔·图尼埃,诗人让·格罗斯让(Jean Grosjean)及雷蒙·格诺一样,我有幸曾作为一个读者为某家大出版社工作过几年。有些人可能不了解这项工作,我可以做一点解释,这项工作主要就是阅读手稿、写出内容概要、给予某种出版意见(大部分时候是不出版的意见)。那时大家把这称作出版社的“阅读委员会”。有人告诉我现如今这一职业正在逐渐消失,现在大家都是请“商业”读者来进行这项阅读工作,他们负责给出意见、建议,不是针对手稿的质量,而是针对手稿的销售力。我觉得有点遗憾。
阅读委员会,就我所知,有益于成就某种大的偏好,发掘出独特的艺术,发现符合个人趣味的作品,那种真诚且完全脱离商业考虑的作品。在《苏菲的选择》的最前面几页,威廉·斯泰伦讲述了作为职业读者的痛苦,阅读某些晦涩的小说或者过于流行的小说给精神带来的疲惫,以及极其主观化的评判方式,在阅读之前,要先嗅一嗅作品的味道,味道要是不对他口味,就彻底否决。
我还记得雷蒙·格诺汇报阅读情况的某些情形,他信奉自己的科幻哲学,往往会把某部手稿的故事重写一遍,读的时候满怀激情,然后一锤定音:绝对不能出版!这个格诺以一种诙谐的方式如此评价阅读工作的价值:“那些不能出版的著作让我受益匪浅。”
文学阅读委员也不是不会犯错。我们都记得阅读委员会拒绝了《追忆似水年华》手稿,还说马塞尔·普鲁斯特的文字是“不忍卒读”。
有时,这些作家读者的偏好倒也能带来好的结果。比如巴黎某个大出版社聆听了委员会全体成员对某部书给出的否定意见,该书要价很高,但明显没有价值,只不过因为作者是某位部长或某个高水平运动员而已;但广大读者,要谨慎得多,才不会被人强迫接受这样的书。
我又想起我曾经阅读过纳格·汉玛迪(Nag Hammadi)《秘密的福音书》手稿的第一个法译本,我与让·格罗斯让都欣然支持出版这本书,但是它却因“商人”的胆怯而被拒绝了——巴黎的大主教禁止出版,因为该书可能会冒犯天主教读者——不料十年后,诞生了一本经久不衰的畅销书:《达·芬奇密码》。
就我而言,阅读手稿往往让我振奋,因为它建立了一种与作者的切肤的联系。手稿的文字常常难以辨认——充满各种错误,但手稿正具有一种诱惑力,是出版了的书籍不具有的。手稿尚未成书,它只是一种期待——我第一次读到素未谋面的一个魁北克年轻人雷·让·杜拉姆(Réjean Ducharme)寄来的手稿时,那种激动的心情,至今我还记得。还有后来读到安的列斯人帕迪克·夏穆瓦佐(Patrick Chamoi-seau)的手稿《德士可》(《Texaco》),我也是非常兴奋。这就是阅读工作所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回报。
既然我今天有机会在这里谈谈文学,我也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我要谈谈我的担忧。
的确,作家的经济状况并不总是很好。一个诗人,一个小说家,要靠自己的写作生存都很艰难。拜伦仅靠出售手稿《海盗》就变得极其富有,维克多·雨果靠《惩罚集》的稿酬就在根西岛(Guernesey)买了一栋房子,那种时代已经很遥远了。最近,文学代理人萨姆尔逊(Samuelson)先生讲述了他是怎么下定决心要从事这项事业的,当初他从美国来拜望让·保尔·萨特,发现这位法国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与随笔作家,一个人生活在一家披萨店楼上的单人间里,眼睛不好,没有救济。克洛德·西蒙,《弗兰德公路》的作者,新小说派著名的代表人物,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也是一贫如洗,只能靠国家文学基金会(la Caisse Nationale des Lettres)发给他的微薄补助度日,如果萨姆尔逊先生知道这些一定会更加震惊的。
出版商对作家的寡情正是众所周知,而作家对出版商的怨恨也是由来已久。有时这种寡情与怨恨还能带来一些有趣的通信,就像塞林纳写给加斯东·伽利玛的这封信,塞林纳大概是这么说的:“亲爱的先生,我听说您将与您的孩子一起去滑雪,欢度圣诞节;我要跟您说,我这里,我的房间里因为没有取暖设备已经结冰了。”
然而也有不少相处融洽的例子,有时与书相关的两方之间甚至会有令人动容的相互忠诚。若没有曙光(le Point du jour)出版社,亨利·米修的作品又会怎样呢?如果没有午夜出版社,新小说的命运又会怎样?如果没有印刷商巴里图(Bal-itout),洛特雷阿蒙又会怎样?既然我已经提到了加斯东·伽利玛的名字,很显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法国文学,以《新法兰西杂志》为中心,加上安德烈·马尔罗、安德烈·纪德、阿尔贝·加缪这些作家,都应对他怀有感激之情。只是我们有些惋惜,必须提到这些例外。
我并不确定如今情况是否改善了很多。商人的控制——我上面提到过——也许让文学的生存甚至是它本身的存在,变得更艰难了。如今,出版诗歌已经成了某种神圣的事业。而小说逐渐变成某种好莱坞式的东西,同样的佐料可以一用再用,只需用某种调味汁调配一下——而且越来越甜腻了。
文学不仅仅能用于自身的庆典
上世纪,种族理论盛行时,文化之间的根本差异被一提再提。以某种荒诞的等级理论为基础,殖民列强的经济成就与所谓的文化优越性被等同起来。这些理论,就像是狂热、有毒的冲动,时不时在某个地方涌现,以此来证实新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的合法性。有些民族也许步履艰难,因为经济落后或技术的陈旧,而没有存在(或话语)的权利。但是,难道人们不明白,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不管他们在哪里,也不管他们发展的水平,他们都使用着语言?每一种语言都是逻辑、复杂、具有结构和分析性的一个整体,可以用来解释世界——可以讲述科学或者创造神话。
只举一个例子,我想说一下巴拿马森林中印第安人的语言安贝拉语(Embera),那些人住在偏远之地,经济非常困难,但是他们在日常语言之外却拥有一种可传达神话的文学语言。难道我们可以说这样的民族是原始的吗?
关于全球化的进程,我们忘记了这一现象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就已经开始了,那时开始了最早的东方和中国之旅。全球化本身并不是坏事。交流促使医学、科学更快地发展。也许信息技术的普及化使竞争更加激烈,却也有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
现在,去殖民化后,文学是我们这个时代男男女女表达自我身份的一种方式,也是要求言语权、维护多样性的方式。马提尼克人埃梅·塞泽尔(Aime Cesaire)的诗歌,马达加斯加人拉哈日玛纳纳(Rahari-manana)的诗歌,魁北克印第安蒙塔涅人利塔·梅色斯托克索(Rita Mestokosho)的诗歌,尼日利亚人索因卡(Soyinka)的诗歌,新喀里多尼亚美拉尼西亚人德维·戈洛代(Dewe Gorode)的诗歌,毛里求斯人阿南达·德威(Ananda Devi)的小说,刚果人维尔费利德·恩松代(Wilfried Nsonde)的小说,新墨西哥美洲印第安人斯克特·墨玛代(Scott Momaday)的小说,拉克塔苏人谢尔曼·阿莱克西(Sherman Alexie)的小说,都让我们明白了世界的复杂性。
世界范围的文化是我们共同的事业。但它首先是读者的责任,也是出版商的责任。的确,加拿大北部印第安人为了能让人听到自己的声音,不得不用征服者的语言——法语或英语来创作,这是不公平的。的确,要让毛里求斯或安的列斯群岛的克里奥尔语有一天会像现在媒体上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五六种语言那样被轻易听到,那纯属幻想。但是,如果通过翻译,世界能听到他们,那么新的事物、某种乐观向上的东西就一定能产生。虽然自葛兰西以来,文化经常被政治工具化,成为政治的幌子,但是走向世界是任何现代人都不能错过的一种历险,不然就会封闭或僵化。
文化,我常常说,是我们共同的财富,是属于整个人类的东西。但要使这成为现实,就应该赋予每个人同样的办法,以接触文化。就此而言,历史悠久的书籍正是理想的工具。它实用、方便、经济。它不需要特殊的技术创举,而且在所有气候下都可以保存。它惟一的缺陷——这也是我特别要向你们、向出版商朋友提出来的——就是在很多国家书籍还是很难获取。
在毛里求斯(我很了解的一个小国家)购买一部小说或者一部诗集的支出会占去一个家庭预算开支的很大部分。在非洲、东南亚、墨西哥、大洋洲,书籍依然是一种不易得的奢侈品。这一弊端并不是无法解决的。比如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出版,设立基金,用于建设图书借阅室或流动图书车,更普及的方法,就是更加注重少数民族语言的需求及创作——有时少数民族的人数还是很可观的——这些都可以促使文学继续成为自我认知、发现他者、聆听主题丰富曲调多样的人类协奏曲的最佳途径。
本报通讯员李钟梅根据勒·克莱奇奥在南京大学的讲座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