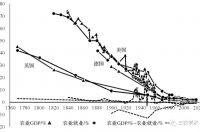尽管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改革的决定(简称“60条”)远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但还是有些亮点。最亮的点莫过于“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与之相应,还有两个市场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一是“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一是“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
然而且慢高兴。这个最亮的点,也是最抽象的原则;在中国的现实中,原则越抽象,也就越不可能实施;这就如同,当你闯了红灯后,立刻会收到一个罚单;但当有人违反了宪法,我们却找不到一项可实施的法律手段去惩罚和制止他。其实在上一届政府之时,市场已经被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制度”,但仍然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包括对许多产业进入的限制,对金融、石油甚至房地产等领域的价格管制,以及“国进民退”的大潮。这种趋势决不会因为把“基础性”换成“决定性”就会消退。
行政部门可能架空改革的几种方式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最能颠覆“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的,是政府中的行政部门。维护市场制度的决定性作用,就是要严格限制行政部门的权力。而中国最明显的宪政缺陷,就是“行政部门独大”。正是这些行政部门掌握着宪法原则等基本原则能否“可行”、“可操作”、“可落实”的关键通道。假定它们是经济人,它们就会采取各种手段削弱、曲解、拖延和驾空这些维护市场的基本原则。
第一种可能是,利用执政党以及整个社会缺乏宪政意识的弱点,将“60条”的次要原则凌驾于主要原则之上。从宪政主义的眼光,我们可以区分“60条”中哪些条款更为基本,而哪些条款是次要的原则。而如果没有宪政意识,就可能认为这“60条”平起平坐;当某一条款和另一条款发生冲突时,就有可能用次要的原则否定主要的原则。例如“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这一条,就明显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相违背,因为国有经济可以利用政治资源获得各种特权,包括垄断权去增强“活力、控制力、影响力”,这就违背了市场的公平竞争和反对垄断的原则。如果没有宪政主义的眼光,“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在“60条”之内就被削弱甚至否定了。
第二种可能,就是利用“解释”来歪曲“60条”,并塞进部门私货。“60条”刚一颁布,就有不少行政部门出来“解释”。例如针对“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中农办某官员马上出来“解释”说,按照旨在保护耕地的用途管制,小产权房仍不合法。且不说,党政某机关只是执政党或政府的执行机关,其官员根本没有对法律和党的决议的解释权;就具体而言,该官员的“解释”是公然偷换概念,因为“60条”已经说明是“农村集体经营建设性用地”,其用途已被规定为“建设性用地”而非“耕地”,与“耕地保护”八杆子都打不着。
第三种可能,是利用技术性理由对抗“60条”。如针对“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一些地方政府会说,为了完成抑制房价的任务,我们必须采取限购或限价的手段,以此对抗“市场形成价格”的原则。由于缺少宪政意识,执政党、中央政府或社会各界经常对这种理由无力反驳。实际上,依宪政主义的眼光,技术性理由或行政性目标的重要性明显低于基本原则,根本无法与后者相抗衡。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前者要服从后者。具体而言就是,当一个社会要求“抑低房价”时,应是在不直接干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的前提下去推行相关政策措施,如鼓励供给、尤其是保护“小产权房”交易安全的政策;把“市场形成价格”当作不可更改的硬约束,才能逼使行政部门的行为走上正轨。
第四种可能,是假装改革。既然市场取向的改革具有政治正确性,一些行政部门就可能把并非改革的、甚至是反改革的举措说成是“改革”。例如,“60条”提出的“利率市场化”目标,已是近几年中央政府改革的方向。但今年7月份央行宣布部分放开贷款利率管制,被宣传为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则是一种假装改革。因为市场价格体系就是一种相对价格体系,如果销售价格放开,而购买价格被管制,这个价格体系就起不到市场价格体系的作用。中国国多年来一直是由中央银行直接规定商业银行的零售利率,将存贷款利率差固定在3%左右,明显高于由市场决定的利率差(约1.5~2%)。利率市场化就是中央银行不再直接规定商业银行利率,而只规定基础利率(再贷款利率,再贴现利率)。很显然,只放开贷款利率,而不放开存款利率,只是有利于银行垄断集团的举措,而不是改革。
第五种可能,就是拖延战术。对于“60条”改革措施,我们最容易想见的,就是相关行政部门以“条件不成熟”或“还需要做大量工作”加以拖延。而这样一拖就可能是相当长时间。例如,1993年的分税制改革提出,“作为过渡措施,近期可根据具体情况,对一九九三年以前注册的多数国有全资老企业实行税后利润不上交的办法”。但一“过渡”就是十四年;到了2008年虽然实行了国有企业上交部分利润的制度,但比例过低(最高10%),且上交的利润又被反投回国有企业。从2008年到2011年,国有企业上交又反投的利润收支相抵竟为负的78.66亿元。一个“过渡”使全国人民近二十年一无所获,还倒贴了许多。甚至在“60条”之内,我们也能看到这种拖延的继续,如“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到百分之三十”。需知道,国有企业一年的账面利润就在万亿元以上。
第六种可能,就是我行我素,根本无视“60条”。这不是因为他们“胆大”,而是因为不少“60条”规定的基本原则,早在更为重要的《宪法》中已有规定,但行政部门和地方政府违反宪法的行为多是明火执仗,并没有受到丝毫惩罚。如“60条”提出,“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已经在宪法中表述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然而这些年来,不少农村居民的土地产权遭到了侵犯。一些地方行政部门借城镇化之机,以极低补偿夺走农民土地,农民若不同意,就滥用公共暴力将他们驱赶,甚至造成一出出家破人亡的悲剧来。我们没有看到哪一个侵犯产权者受到了惩罚。所以他们可以用同样的行为蔑视“60条”。
因而,那些很快就宣布“60条”“伟大”和“深远”的传媒,似乎有点太着急了。一个改革文件能否“伟大”,不在于它说得多么漂亮,而在于它不仅说得正确,而且能够实施。例如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决定》在土地制度改革方面甚至比“60条”走得还远,只是这些改革方案只停留在了文字阶段,甚至在此之后的“《土地管理法》修订草案”中出现了相反的趋势。因而十七届三中全会不会青史留名。
有奖惩与中共改革方案的权威
今天执政党的当务之急,就要寻找落实“60条”明智而可行的道路。至于它是否“伟大”,留给后人去说吧。而所谓“明智而可行”,就是避开行政部门各种驾空手段,把“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变成可实施的原则。
所谓“可实施”,其实很简单,就是要有奖惩。没有奖惩的制度,就不是有效的制度;没有奖惩的宪法,就近乎一纸空文;没有奖惩的“60条”,也不过是60段话。
若要奖惩,首先要把肯定性句式变成否定性句式。所谓“否定性句式”,就是禁止最有可能违反的机构或个人做出违反“60条”的行为。例如,关于表达自由,中国《宪法》第35条是肯定性句式,说“中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很显然,这一宪法条款没有实施的手段,因而中国人民的这一宪法权利没有得到很好保障;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则说,“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这种否定性句式就有效得多,加上在美国可以以宪法为依据进行诉讼,美国人民的相关自由权利得到了更有效的保障。
第二,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以否定性表述形式进入《宪法》。即“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及各级行政机关不得制定违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原则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政策,除非有充分理由说明,该法律等是用来弥补市场失灵、并经立法机关同意。”更具体地,有关市场制度的三个要点,即保护产权,市场定价,和禁止垄断,也要用否定性句式在宪法中表达,即“非经法律正当程序,政府不得剥夺公民或组织的财产”;“政府行政机关不得制定管制价格以代替市场价格形成机制,除非有充分理由说明,该领域的市场定价机制失灵,且经立法机关同意”;以及“政府行政机构不得创立和颁发垄断权,除非有充分理由说明,该垄断权的创立是合理的,且经立法机关同意。”
第三,以这一组否定性宪法条款为依据,就要修改已有法律法规的相关条款,如《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土地管理法》,《矿产资源法》,《电信条例》,等等,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宪法精神以否定性表述写入这些法律法规中。
第四,要在执政党和政府体系中,培育和形成宪政意识,即以宪法为基础的法律体系是一个分层结构,宪法原则要高于和优于其它法律原则,上位法要高于下位法;当发生冲突时,一般法律要服务宪法,下位法要服从上位法;很显然,行政部门制定的政策,更不用说技术性理由,要服从宪法和法律。想用技术性理由对抗成为宪法和法律的“60条”原则,就要受到否定和惩罚。
例如对于国土部和住建部在“60条”刚一颁布之后,就声称“要全面、正确领会”“60条”和高调“坚决叫停”小产权房的行为,就要予以惩罚。它们很显然是用所谓“保护耕地”的技术性理由对抗《宪法》中“农村土地归农村集体所有”和“60条”中的“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的原则。因为很显然,大量小产权房并非耕地上的房屋;北京市国土局的资料承认,他们整治的小产权房的5000亩地中,只有133亩耕地。
第五,宪政意识还包含了,政府各个分支有其权力边界,尤其是行政部门,其职责就是执行宪法和法律,在宪法和法律边界内制定政策,不能僭越权力边界去立法,也就自然没有释法权。执政党或全国人大应该明确指定有释法权的机构。一旦出现行政部门出来释法,就要指出它的非法性,并对其所释之“法”加以驳斥。例如,关于国有企业要定位于公益领域的原则,早有国资委官员将石油、石化和电信等营利性产业包括了进来;这就使得“公益性”这个词毫无约束力。但“公益性”概念不是可以任人曲解的,所以要由权威释法机关根据该概念的学术的和法律的严格含义进行解释。
第六,实际上,现有《宪法》和法律体系已经包含了大量“60条”中的内容,因而,实施“60条”的前提,就是要实施现有的宪法和法律。若要如此,就要依据现有的《宪法》和《立法法》,清理现有法律中违反市场原则的法律或条款。实际上,现有大量的违反市场规则的文件是称不上法律法规的行政文件,如设立石油垄断的38号文件和72号文件;因此,以国务院为首的行政部门马上可以落实“60条”的行动,就是清理和废除国务院及各部委已经颁发的有违市场经济原则的行政文件,其中大量的是设立垄断权的文件。
第七,针对拖延战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将相关部门说“条件不成熟”的领导人免职。广为流传的邓小平的故事可为借鉴。当邓小平刚复出时,提出恢复高考。据说当时的教育部长说,“小平同志,条件还不成熟。”邓小平回答说,“如果你不能干,我知道谁能干。”比较可信的记录是说,邓小平警告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不要成为阻力”(丁晓禾,“1977年邓小平恢复高考内幕”,摘自《涅槃》,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我希望现任领导人能够学习邓小平简练果断的行事风格。实际上,在我们批评行政部门时,我们从不否认,行政部门中人才济济、卧虎藏龙,有大量以社会和国家前途为已任、不牟私利的行政官员,一旦高层领导人通过人事任免表明改革决心,优秀人才自会脱颖而出。
第八,针对我行我素,执政党和中央政府就要采取霹雳手段。实际上,“不可侵犯”不是可以随便说的,如“中国领土不可侵犯”意味着,一旦有人侵犯,就必须用武力还击,惩罚并赶走入侵者。康芒斯说,财产权意味着,当有人侵犯时,你可以指望政府来保护你的财产。当“60条”说公民的财产“不可侵犯”时,就是执政党的一个非常严肃和重大的承诺,即如果在此之后再有一个中国公民的财产受到侵犯,执政党通过其对政府的主导,就要以公共暴力阻止这种侵犯,并惩戒侵犯者。这句话可不是随便说着玩的。
任何一个推动改革的政治领导人都要有思想准备,实施改革可能会遭遇真刀真枪的挑战。美国在1964年通过的民权法案规定,不得在公共场所和公共机构中实行种族歧视;但一些州政府公开反对,如亚拉巴马州州长华莱士决心对抗,在州立大学门口部署了国民警卫队和州警察,不许黑人学生入校。气氛极为紧张,冲突一触即发。这时总统肯尼迪依据美国法律将国民警卫队转归自己指挥,才使华莱士无计可施(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海南出版社,2004,第1000~1002页)。由于不惜在现场武力对抗,以保证新通过的法律得到执行,美国的宪法和法律才得到了尊重,民权法案才会落实。
同样,如果“60条”宣称“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就意味着要对侵犯产权的行为做出及时和有力的反应。这当然不只是对小偷小摸的事情做出反应,而是对颇有些实力的行政部门侵犯公民财产行为做出反应,才能真正显现执政党决心对“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这句话负责。如果现在再有某地某行政部门滥用公共暴力强占农民土地,执政党和中央政府就应及时做出反应,撤消当地党政一把手的职务,并将其逮捕,并以侵犯财产罪予以公诉。否则的话,“60条”的权威顷刻瓦解。
总之,信用的建立不是在开出支票之日,而是在把它兑现之时。在中国普遍宪政崩坏的背景下,“60条”的颁布给执政党及其领导人带来的不是赞誉,而是责任。他们应该意识到“言必信,行必果”的艰难。落实“60条”不仅需要勇气,而且需要智慧。
当今的政治领导人固然面对着强大的利益集团,但如果能够拿出当初毛泽东对抗张国焘的更强大的军事利益集团的勇气来,这些利益集团本不在话下。而最大的智慧,就是看到“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结果,从长远看是对所有的人,包括行政官员和国企高管都有好处的,从而用来瓦解任何对抗“60条”的公然行动和消极怠工。相反,如果不能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真正在中国大地上发挥作用,“60条”就只不过是六十条文字而已,即使还算漂亮。
2013年11月24日于五木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