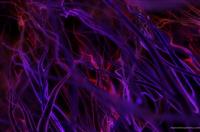
自2008年以来,美国经济经历了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为缓慢、乏力的复苏,被称为“经济大衰退”(Great Recession)。至今美国经济尚未出现一般危机之后复苏期会出现的6%、7%的增长反弹。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美国经济要到2016年增长率才能达到3%。尽管就业率有所上升,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
反观中国,近期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根据世界银行4月29日发布的国际比较计划(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以下简称ICP)报告,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规模将在今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由于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具有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中国经济应该可以在其后继续保持中高速的增长(参见林毅夫刊于FT中文网《中国经济的后发优势》一文)。随着中国继续拉大和美国经济规模的差距,世界经济中心向中国的转移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对于美国情况,著名经济学家们绞尽脑汁,近期美国前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在《波斯顿环球报》上著文倡议,“赋闲劳工+低利率=重建基础设施的好时机。他以纽约肯尼迪机场为例,指出“没人为这个机场感到骄傲”,美国副总统乔•拜登(Joe Biden)更抱怨“拉瓜迪亚机场就像位于第三世界”。萨默斯教授反问,“现在不重建,更待何时?”
其实萨默斯教授的政策建议没有什么新意,中国在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时就采用过。当年受到危机冲击后,中国政府及时推出了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使得中国经济在危机期间维持了稳定增长,并为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经济增长率打下了基础,使之从此前年均9.6%进一步提升到年均10.5%。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后,中国再次以积极财政政策投资于基础设施,从而使得中国经济在2009年第一季度率先于全世界复苏,这些投资也为中国未来增长奠定基础,使其在持续了35年年均9.8%的增长后能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
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不久,笔者(编注:本段皆指林毅夫)在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任上,就根据中国经验,指出全球金融危机仅靠货币金融工具难以解决,要“超越凯恩斯主义”,避免走挖个洞补个洞或发放失业救济的老路,需要运用全球协调的财政政策投资于基础设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电力、道路、港口等能为未来增长消除瓶颈的高收益项目,才能消化全球闲置的巨大过剩生产能力和创造就业,并为发达国家的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使全球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济,能够恢复正常增长和活力。同时,笔者倡导创立“全球复苏基金(Global Recovery Fund)”,之后又提出“全球基础设施计划(Global Infrastructure Initiative)”(亦可参见FT中文网《呼吁全球结构转型基金》)。这一构想最初于2009年2月在皮特森国际经济学研究所演讲时提出,同年3月分别在世界银行、纽约美国外交委员会的午餐会上重申,演讲全文刊登于2009年夏季出版的《哈佛国际评论》。其后,笔者在一系列文章和著作中一再倡导这一超越凯恩斯主义的计划,包括在《西潮到东风》一书的第二部分,2013年1月又在美国经济学会年会的报告和2013年5月《超越马歇尔计划》(与王燕合著)等,这种政策能够创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赢。
这一来自中国经验的倡议开始提出时,国际上响应者了了,现在危机超过5年了,尚未能走出困境,赞同的人越来越多,包括萨默斯这样影响国际舆论走向的著名经济学家在内。二十国集团(G20)的部长级会议也多次重申基础设施投资对于重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美国前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和全球著名顾问公司麦肯锡也将于今年5月底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邀请各国领导人和财政、金融、实业界的领袖召开全球基础设施会议,推动这一计划。可见,引领世界新思潮的观点不见得只能来自发达国家的学者。
尽管发达国家的理论界仍然左右着世界的政策思潮和实践,但是全球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尚未完全从危机后的衰退中完全复苏。当前主张政府不应采取反周期措施的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固然被各国政府在危机中所摒弃,但挖个洞补个洞、给失业救济和打开货币闸门的“凯恩斯主义”的传统经济刺激也已经走到了尽头,即使储备货币国家利用货币霸权推出“非常态货币干预的量化宽松政策”(unconventional monetary intervention,quantitative easing),也未能根本解决发达国家的问题。正如印度央行行长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最近多次公开批评所指出的,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最初导致大量资本流入新兴市场经济体造成资产泡沫,现在的退出又导致大量资本流出,造成外汇储备损失,货币贬值。这种“以邻为壑”的政策可能引致新兴市场国家在“孤立无援”之下,被迫采取竞争性货币扩张以保持国际竞争力,导致出现双输的结局。
在持续的新常态下,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将继续乏力,真实失业率和政府的社会支出将维持在较高水平。同时发达国家政府积累的债务将急剧增长,为了降低政府发新债还旧债的成本,货币政策将持续宽松以降低利率水平,刺激了发达国家国内的资产泡沫,也会如拉古拉姆•拉詹所说的给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管理带来诸多困难。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国的发达国家而言,与其增发货币来发失业救济,当然不如增发货币来支持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全球基础设施计划”,这即能够帮助发达国家走出衰退又能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
既然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界和政策界已经开始向东方看,学习中国在遭到危机冲击经济衰退时的应对经验,倡议以能消除增长瓶颈、创造就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来恢复经济的稳定和增长,中国的学界是否也需要观念上的转变?解决中国经济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是否也可以来自于对自己问题的性质、可动员来解决问题的资源和条件的认识,从而自己寻求解决的方案,而不是一出现问题就向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去寻找答案。是否也可以从自己创造的经验中去总结出新的理论,从而对世界理论的前沿做出贡献?自亚当•斯密1776年发表《国富论》以来,处于世界经济中心地位的国家也就是世界经济学理论研究和思潮产生的中心国家。(具体可参见林毅夫的《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祝贺创刊40周年》一文,刊于《经济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学界是否也应该为世界经济学研究和思潮产生中心向中国的转移做好准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应该是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知识界所应该思考的问题。
注:编者省略部分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