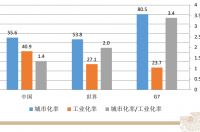如今,欧洲的未来取决于显然不现实的东西:希腊和德国必须达成协议。让希腊和德国不可能达成协议的不是两国政府坚守的立场——希腊要求债务削减,而德国坚持不会削减一个子儿的债务——而是更加基本的东西:希腊是这场冲突中显而易见的弱方,但它在其中的利害关系也要严重得多。
博弈论表明,最不可预测的冲突是那种坚毅的弱方与坚定程度远远不如它的强方之间的冲突。在这一情境中,最稳定的结果总是双方都部分满意的平局。
在希腊-德国冲突中,至少理论上很容易设计出这样一个正和博弈。我们所需要做的只是忽略政治说辞,专注于双方真正想要的经济结果。
德国决心抵制任何债务减记计划。对德国选民来说,这一目标比希腊结构改革的细节重要得多。至于希腊,它决心要获得对其惩罚性的、不利与生产的紧缩的减免。紧缩是在德国的坚持下由“三驾马车”(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施的。对希腊选民来说,这一目标比详细计算30年后国民债务的净现值重要得多。
如果双方都专注于最紧要问题,同时在第二目标上做出妥协,就很容易谈判协议。不幸的是,人类的可错性(fallibility)似乎在与这一理性方案作对。
新任希腊财政部长雅尼斯·雅路法克斯(Yanis Varoufakis)是专长博弈论的数理经济学教授。但他的谈判技巧——在强势和弱势之间以不可预测的方式波动——与博弈论的应有之义背道而驰。雅路法克斯的策略思维是用枪指着自己的头,然后要求赎金否则就开枪。
德国和欧盟决策者认为他是虚张声势。结果,双方陷入了负和僵局,让严肃的谈判无从进行。
这一结果绝不是不可避免的。就在上个月,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如教科书案例般地证明了这类谈判可以也应该取得进展——他巧妙地绕过了德国对欧洲显然需要的货币刺激的反对。
1月22日,欧洲央行宣布启动量化宽松。在此之间的好几个月中,德拉吉与德国人公开争论“红线”原则——即导致协议无法达成的点。德国的红线是债务共同化:不管哪个欧元区国家违约,都不可能共担损失。
德拉吉让德国在这个问题上获得了胜利,他认为这个问题在经济上无关紧要。但是,关键在于他小心翼翼地坚持到最后时刻才做出让步。德拉吉把量化宽松争论的焦点引向风险共担,因此将德国的注意力从重要性远远过之的问题上移开:量化宽松计划的庞大规模足以打破德国对于政府债务货币融资的禁忌。德拉吉在正确的时间在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上做出了让步,而在对于欧洲央行真正重要的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如果雅路法克斯为希腊制定类似的策略,他应该顽固坚持要求债务取消直到最后一刻,然后在这一“原则”上做出让步,以换取紧缩和结构改革问题上的重大利益。或者他可以采取更温和的策略:从一开始就做出让步,承认债务神圣不可侵犯这一德国的原则,然后证明在不减少希腊债务任何面值的情况下可以减缓紧缩。雅路法克斯在无视与和解之间摇摆,结果在两个立场上都失去了信誉。
在谈判中,希腊从一开始就坚持债务削减是其红线。但是,它没有坚持这一立场,将关于债务减免的争论引向德拉吉式的转移注意力战术,而是在几天之内就放弃了这一要求足。接着,希腊又做出了毫无意义的挑衅,拒绝与三驾马车谈判,尽管事实上这三家机构远比德国政府更加同情希腊的要求。
最后,雅路法克斯拒绝延长三驾马车的计划。这就造成了一个毫无必要的截止期——2月28日欧洲央行将撤回资金,有可能导致希腊银行系统崩溃。
希腊的理想主义新领导人似乎认为他们只要依靠民主权力就可以在不进行常规妥协和虚与委蛇的情况下战胜官僚主义反对。但官僚而不是民主才最重要,这是欧盟机构永远不会妥协的核心原则。
结果是在与德国和欧洲的牌局中,希腊又回到了原点。新政府过早暴露了王牌,导致想要虚张声势时也没人相信。
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最有可能的结果是左翼联盟(Syriza)很快认输——就像其他所有被选来承担改革使命的欧元区政府一样,然后回归三驾马车式的计划,只是把“三驾马车”的名头去掉。另一个可能性——尽管希腊银行仍能开张营业——是政府单方面实施一些关于工资和公共支出的激进政策,无视来自布鲁塞尔、法兰克福和柏林的反对。
如果希腊尝试这一单方面无视,欧洲央行将几乎肯定决定在2月28日三驾马车计划截止后中止其对希腊银行系统的紧急融资。随着这一自作孽式的截止期的临近,希腊政府可能会认输,正如爱尔兰和塞浦路斯面临类似威胁时妥协一样。
这一最后一分钟的妥协可能意味着新希腊政府的辞职并由欧盟批准的技术官僚取而代之,就像2012年意大利所爆发的反对贝卢斯科尼的宪法政变。在不那么极端的情形中,雅路法克斯可能丢掉财政部长的职位,而政府其他部分照旧。唯一的其他可能性——当希腊银行开始崩溃时发生——时退出欧元区。
不管以什么形式屈服,希腊都将是唯一的输家。民主和经济扩张的支持者错失了智胜德国、结束德国给欧洲所施加的自我毁灭式紧缩的最佳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