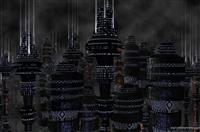创新和全球市场的互动在收入分配制度顶层推动全球不平等和财富聚集效应大幅上升。由于监管保护和全球市场赢家通吃的本质,技术突破在叱咤风云的企业家手中可以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收入。但人们却往往忽视公共资金在创造个人财富聚集效应中的作用。
发展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最近指出,美国新技术基础投资主要由公共基金驱动。具体形式既可以是由美国国防部或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等机构直接出资,也可以采用税收减免、采购及学术实验室或研究中心补贴等间接形式。
当许多研究不可避免地走进死胡同,一般由公共部门承担损失。但最终取得成果的情况却截然不同。一旦某种新技术地位确立,民营企业家就在风险投资的协助下对其进行改造,以适应全球需求、建立临时或长期垄断地位,进而获取巨额利润。而承担大部分研发费用的政府却基本得不到回报。
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特别提到的例子是丙肝治疗药物索非布韦。萨克斯解释说出售该药的吉利德科技公司所拥有的专利直到2028年前一直有效。吉利德可以制定垄断价格:12周的治疗费用高达84,000美元,较之该公司数百美元的生产成本不知高出多少。去年,垄断药索非布韦和定价94,000美元的Harvoni的销售总额高达124亿美元。
萨克斯估计私营部门花了不到5亿美元研究开发索非布韦——上述成本吉利德仅需销售几个星期就可以回收。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曾投入大量资金资助研发该药的创业企业,这家企业后来被吉利德收购。
毋庸置疑民营企业家的想象力、营销经验和管理能力对于新技术成功诞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众多商业创新所提供的低价、高质和消费者盈余显然社会收益巨大。但人们不应忽视政府所扮演的角色。
经合组织和欧盟统计局联合数据显示2012年美国研发开支的31%来源于政府直投。如果加上税收减免等间接开支,该比例至少上升到35%左右。少数私人投资者往往借助上述公共开支获得巨额利润,并因此导致收入过度集中。
有几种方法可以改变现行制度。罗德里克提出设立公共风险投资公司——主权财富基金——即在公共资金资助取得的知识产权中持有股份。另一种办法是在个人或公司利用公共研究成果赚钱时改革税法。
这两种方案各有问题。主权财富基金不能受党派政治的干扰,可能的解决方法是只给他们没有投票权的股份。鉴于原始突破与所创造财富之间的关系很难量化,提高政府资助研究项目的税收可能带来问题。此外还有G-20刚刚 开始解决的全球资本流动性和避税并发症。
可能还有其他办法能够解决问题:那就是像许多市场经济国家那样收紧专利法或对制药等垄断行业实行价格管制。但减少公共资金的研发投入绝不是办法,因为研究和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其实无需巨额回报就能调动积极性;即使出色的创业者也可以接受连续几年50%左右的利润。数倍于此的回报不过是公众给少数个人的大礼。必须同时依靠政策和国际协议让纳税人获得不俗的回报,而不影响精明企业家实现创新产品商业化的积极性。
我们不应低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其中涉及的金额创造新的贵族阶层,可以通过继承将财富传递下去。如果可以通过巨额赞助竞选保护特权阶层的利益(美国现在就是如此),这一问题将系统性影响民主和长期经济效益。可能采取的解决办法远非如此简单,但寻找上述办法却绝对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