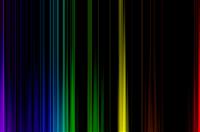
赫希曼传奇的一生:打过仗,从过政,教过学,写过书
马基雅维利在他落魄的晚年,曾给好友圭恰迪尼写过一封著名的信,记述自己伏案写作《君主论》和《论李维》的情形。白天他“四处游荡,捉画眉鸟,拾柴火,跟当地的粗人一起打牌,玩十五子棋”。傍晚回家后,他“脱掉脏兮兮的衣服和靴子,穿上宫廷的华服,与宫廷里的古人一起用餐……毫无羞涩地与他们交谈,向他们请教他们的行为动机,他们也友善地回答我。这时我几个时辰都不觉得无聊”。
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1469—1527),代表作《君主论》。
据阿德尔曼说,毕生喜爱阅读马基雅维利的赫希曼,在写作《欲望与利益》的过程中也像马氏一样,将自己沉浸在与古人对话之中。那时的赫希曼,在卡片上记满了古人的名字和箴言,“与古代哲人一起追思旧邦……连他的衣着都让人想起文艺复兴时代的服装。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大厅里,人们一眼就能认出既博学又衣冠楚楚的赫希曼”。
马基雅维利缅怀旧事,是为了让他的同胞重建罗马人的荣誉意识,赫希曼回到古人中间,则是要唤醒今人对早期资本主义的记忆,恢复他们对其诞生的“奇迹感”。因为在他看来,那个时代的道德焦虑推动着对人性的反思,但人们通常都低估了它内生于传统话语的程度。那是一个在既有的人性论内部发生缓慢变化的神奇过程。
其实,赫希曼本人的一生就是个很传奇的故事。2012年底他去世后,《纽约客》专栏作家格莱德韦尔曾著长文《怀疑的才能》,讲述了他不同寻常的经历。
1915年赫希曼出生在柏林一个犹太富商之家,1933年入索邦巴黎大学,然后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最后是在意大利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这样的教育背景足以使一个人有开阔的知识视野。而在学业之外,他的经历更加不同寻常。西班牙内战期间,他曾投身于共和派反抗佛朗哥的战斗,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在法国马赛大力营救过数千名犹太人,其中包括画家杜尚、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和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加入美军成了一名文官,在意大利参与过对纳粹战犯的审判。战后他先是供职于美联储,参与过马歇尔计划的实施,然后在南美的哥伦比亚为世界银行工作多年。当赫希曼真正转向学术生涯时,已过不惑之年,先后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几所精英大学和机构。他留下的著述并不很多,却常有独特的创见,以至有人认为,他没有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不是他的遗憾,而是诺贝尔奖委员会的错误。
从发展经济学家到观念史学家
确实,赫希曼通常被人视为一个杰出的发展经济学家。他的《经济发展战略》和《退出、呼吁与忠诚》,使他在经济学界享有盛誉。但赫希曼同时也是一个喜欢跨学科思考的人,现代森严的学科壁垒可以成为“专家”躲开质疑的避风港,但在赫希曼看来,却是使人眼界狭窄的知识牢笼。所以我们看到,写出《经济发展战略》的赫希曼,同时也是《欲望与利益》的作者,前者是典型的发展经济学理论著作,后者则是对17和18世纪观念史、甚至是修辞史的精深研究。它的主题虽然涉及经济行为的动机,亦有对斯密和重农学派的讨论,叙事方式却完全回到了古典语境之中,调动的许多知识资源通常不会进入经济学研究视野,例如培根、维柯、斯宾诺莎、孟德斯鸠和米勒等。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清晰看到赫希曼与哈耶克——他自20世纪40年代便喜欢阅读的学者之一——的相似之处。第一,他们两人都是不好归属于任何学科的思想家;其次,与哈耶克的无知理论相似,赫希曼认为,社会生活的复杂性给人类的认知能力设定了根本性的限制,但这种限制本身并不是一个不利因素,反而为人类以纠错方式发挥创造力提供了广阔空间,所谓发现无知要比已知更令人着迷,改进的动力也正是来源于此。这种思想在他写于1967年的名篇“隐蔽之手原理”中有最集中的体现。
或许经历过太多人世间的不测,他对那些以理性假设作为前提的理论推衍一向不以为然,更看重计划的失败为创新提供的机会:“创新的出现总是令我们惊奇,在它出现之前我们不可能想到它,甚至难以相信它是真的。换言之,我们不会有意识地从事这样的任务,它所要求的创新我们事先就知道将会发生。我们能让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的唯一方式,就是对任务性质的错误判断。”无知确实能酿成恶果,但那多是因为政治领袖们的虚妄。他们宣称拥有自己并不具备的整全知识并强力加以贯彻,结果是扼杀了个人根据变化作出调整的机会。
尽管赫希曼本人宣称,《欲望与利益》一书与他过去的经济学著作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我们从这本著作中仍可以看到以上思想方法的运用。他认为,新的观念并不是从外部对抗旧既有体制中产生的,而是内生性危机因素的意外作用。《欲望与利益》导论中的一段话,可以视为这种认识方法的反映:“人们通常低估了新事物乃是源于旧事物的程度。将漫长的意识形态变化或演变描述为一个内生的过程,较之把它描述为独立形成的反叛性意识形态与占主导地位的旧伦理的衰落同时兴起,当然要更为复杂。”新思想的产生类似于一个应激性的进化过程,而应激源只能从它的机体内部去寻找。为描述这个过程的发生,就需要考察和辨别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观念与主张,找出其源头与变异的来龙去脉。
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思想史,往往会发现一种新观念的产生并不是来自周密的论证,而是一些存在于原有话语体系中的“小观念”和“局部知识”,它们在意识形态中看似不占核心位置,更不能提供认识社会的整全知识,但是在某种社会变迁——本书中的例子是商业活动的增加——的刺激下,却具有动摇既有意识形态的强大力量,能够引起社会风尚的深刻变革。
此外,17和18世纪的思想者,与今天的理论家们最大的不同,大概是他们喜欢讨论的不是“主义”,而是“人性”。翻一翻譬如洛克、亚当·斯密和孟德斯鸠的著作,我们便会发现,他们很少讨论以“主义”冠名的各种思想,也不会把带有“ism”后缀的词作为核心概念。毕竟那时的西欧尚未进入“意识形态”时代,其世界观仍是以自古典时代便已形成的各种人性论及其相关概念作为基础。当然,这也是赫希曼能够从修辞学的角度分析那个时代商业伦理的前提。
资本主义早期对“欲望”的新诠释:人性之恶VS道德推崇
像“欲望”和“利益”这类概念,便是能够引出大见识的小观念。《欲望与利益》的副标题是“资本主义胜利之前的政治争论”,由此可知它是一本有关资本主义早期观念史的著作。为了寻找这些小观念的影响,赫希曼必须冒险步入那个丰富而复杂的思想大厦,重建观念序列而忽略其各种思想体系,这使此书更像是对17、18世纪思想生态的一次田野调查。那个时代发生过一场对商业行为的思想推销运动,采用的方式之一,是通过对包含在“欲望”(passion)这个古老概念中的某些成分重新给予伦理学解释,使人们从其负面价值的负担中解脱出来。
据赫希曼本人说,他这本书的构思,肇端于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的一句话: “幸运的是人们处在这样的境况中,他们的欲望让他们生出作恶的念头,然而不这样做才符合他们的利益。”
他由这个表述察觉到,对于人的“欲望”,自17世纪始,一些思想家开始从中区分出一种“利益”的成分,而在过去这样的区分是不存在的。“欲望”中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即对财富的贪婪,一向被基督教认定为人类“七宗罪”之一,奥古斯丁将它同权力欲和性欲并列,称为导致人类堕落的三大诱因。不过基督教神学的希腊化因素也给奥古斯丁的思考留下了烙印,他在谴责欲望的同时,还观察到在不同的欲望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比较而言,权力欲也许比另两种欲望要好一些,它包含着追求“荣誉”和“公共美德”的倾向,可以抑制另一些罪恶。这虽然仍是一种古代世界的欲望观,但它提示了欲望的不同成分是可以进行语义学操作的,这就为以后的“欲望制衡说”埋下了伏笔。
比如,就贪财这种欲望而言,如果决定某种行为是否有利可图是来自经济上的考虑,那么它是否应当被人广泛接受,甚至应当得到赞美和推崇,则主要取决道德上的说服力。就像韦伯在解释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的相关性时所说:赚钱的动机,经济上的利己主义,是每个时代都常见的动机。正如中国有重农抑商的传统一样,它们在欧洲的基督教文明中,过去也仅仅是被人默默接受,而从不给予道德上的张扬。需要一项观念上的重大转变,才能把一种原来被视为人性中恶的因素,变为值得称颂的美德。
道德或宗教在约束欲望时日渐失效
一种发生在语言深处的变化,逐渐完成了这一使命。按赫希曼的分析,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基督教力主戴罪之人当以谦卑为上,文艺复兴之际则出现了十分排斥利益考虑的“荣誉观”和“英雄主义”。然而不知起于何时,这两种价值观开始同样受到怀疑,一种为商业行为的新辩护诞生了。它既不像基督教的谦卑观那样压抑欲望,也不像骑士的荣誉意识那样放纵欲望,而是对欲望加以解剖,区别出它的不同功能。在赫希曼看来,最能代表这种思想转变的,便是维柯下面这段话:
社会利用使全人类步入邪路的三种罪恶——残暴、贪婪和野心——创造出了国防、商业和政治,由此带来国家的强大、财富和智慧。社会利用这三种注定会把人类从地球上毁灭的大恶,引导出了公民的幸福。这个原理证明了天意的存在: 通过它那智慧的律令,专心致力于追求私利的人们的欲望被转化为公共秩序,使他们能够生活在人类社会中。
这段话的意义在于,以往被认定为“人性之恶”的欲望,只要为它注入“智慧的律令”,便可以变为有益于人类福祉的力量。人类持有善恶观或是一个常数,但何为善恶却未必是一个常数,人作为一种能反思的动物,会随着环境的变化对其进行调整。
这一调整的大背景是:文艺复兴以后,尤其是17世纪以后,人们对于用道德教化或宗教戒律来约束人类欲望,已逐渐失去信心,于是他们开始寻找约束欲望的新方法。神的权威既已不足恃,重新解释欲望本身的努力也就随之产生。帕斯卡为赞扬人类的伟大而找出的理由是,人类“已经努力从欲念中梳理出了美妙的格局”和“美丽的秩序”。人的欲望是“有秩序的”,而在理性主义者眼中,秩序永远是美丽的。它的美也许处于欲望者的意识之外,但就如同物质世界一样,可以通过理性的分析对它加以认知甚至操控。
这种基于理性分析的思考,引发出许多非常著名的学说。培根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严肃地思考“如何让一种欲望对抗另一种欲望,如何使它们相互牵制,正如我们用野兽来猎取野兽、用飞鹰来捕捉飞鸟”。斯宾诺莎更是直接断言:“除非借助相反的更强烈的欲望,欲望无法得到限制或消除。”曼德维尔从欲望中区分出奢侈与懒惰,休谟则将贪财与贪图安逸相对照,他们都认为,前者要比后者对社会更加有益。
商业伦理兴起:利益驯化欲望
然而有一个问题。这些见解不管从哲学角度听起来多么动人,它能否落实为一种真正可以制服欲望的制度,仍是非常不确定的。按休谟的著名说法,理性很容易被欲望征服,成为它的奴隶。需要一种新的解释方式,使欲望能够与理性建立起可靠的联系。完成这一解释任务的关键,便是“利益”的概念。
赫希曼在“‘一般利益’和驯化欲望的‘利益’”这一节中,追溯了它的出现与词义变化的过程。最初它是见于治国术中,罗昂公爵提出了“君主主宰臣民,利益主宰君主”一说。继之又有爱尔维修对道德家的讽劝:“假如有人打算劝说轻佻的女人端庄而收敛,他应该利用她的虚荣心去克服她的轻佻,让她明白端庄稳重是爱情和优雅享乐的来源……用利益的语言代替欲望有害的说教,他们便有可能成功地使人们接受其箴言。”另一位活跃在18世纪中叶政论舞台上的英国主教巴特勒,则对利益和欲望的区别作了最清晰的表达:
特殊的欲望有悖于谨慎和合理的自爱,后者的目的是我们的世俗利益,一如它有悖于美德和信仰的原则;……这些特殊的欲望会诱发不利于我们世俗利益的鲁莽行为,一如它会诱发恶行。
在传统的道德说教失效的情况下,“利益”这个概念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它不是一个独立于欲望和理性之外的概念,而是可以成为沟通和平衡两者的桥梁:使欲望变成融入“理性”的欲望,使理性成为替“欲望”服务的理性。这种从利益的角度处理欲望的方式,促成了古老的人性论的一次制度主义转折。由于人们认识到,欲望虽然无法克服,却有可能使之向着利益的方向转化,这不但“能更好地使之(欲望)得到满足”,“在获得财富方面有更大收获”(休谟语),而且较之受单纯欲望驱动的行为后果,它具有另一个明显的优点:可以形成一种社会风尚,使贪婪在商业社会中变得有益无害。
正如斯密在《国民财富论》中所说,长期经商会使商人养成“长时间的勤勉、节约和小心经营”的习惯。曼德维尔在对比商业社会与古代的人格时,这一点说得更加清楚:“未开化者的……种种欲望更游移、更善变。在野蛮人身上,那些欲望比在有教养者身上更经常地相互冲突,争占上风。有教养者受过良好的教育,已经学会了如何获得个人安逸和生活舒适,如何为了自身利益而遵守规矩和法令,常能屈从较小的不便,以避免更大的不便。”当然,这种驯化欲望的利益也使理性不再那么洁净,而是归属于算计利益的个人。然而正是有此一认识,才使得思想家们能够阐述商业活动在敦化风俗方面发挥良好的作用,这在孟德斯鸠“哪里有商业,哪里就有良好的风俗”这类著名的说法中,得到了最好的表达。据赫希曼的考察,用利益去对抗其他欲望,以此推动社会进步,“这种思想已经变成了18世纪相当普遍的智力消遣”。
此外,它对政治生态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商业利益的发展使统治者获得了影响社会的巨大物质力量,后来的福利主义和帝国主义都可由此得到部分解释;另一方面,它使统治者的滥权行为也受到了一定限制。其中作用最为明显的,就是孟德斯鸠所大力赞扬的不动产的增长,它不同于土地这种传统的财富形式,其易于流动性限制了君主的暴虐。孟德斯鸠认为,人类的权欲就像贪欲一样,也是自我膨胀和不知餍足的,但利益的考虑同样能够使之得到驯化。他把当时流行的利益制衡欲望的观点与他的权力制衡理论融合在一起,阐述了汇票和外汇套利可以成为“宪法性保障”的补充,充当对抗专制主义和“权力肆意妄为”的堡垒。用今天的话说,动产持有人可以用钞票、甚至用脚投票,是使宪制得以形成的要素之一。
现代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张,与以往历史上的大规模征服有何不同?
当然,欲望向利益的转化并非没有问题,在很多人看来它会让世界变得“庸俗”,使人生“无趣”。更严重的是,它阻碍了“人类个性的充分发展”。马克思的“异化说”,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都是对这种现象最著名的批判。对此,赫希曼以反讽的口气说,这类指责恰恰表明,早期资本主义辩护家所取得的成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人遗忘了。
透过赫希曼还原的思想史场景可以看到,早期思想家对商业社会寄予希望,恰恰是因为“人性的充分发展”并不可取,而商业能够“抑制人类的某些欲望和恶习,塑造一种不那么复杂和不可预测、更加‘单向度的’人格”。他们对欲望可能释放出的能量有着强烈的道德忧虑,所以才将利益驯化欲望作为商业社会的伟大成就之一。而一个多世纪之后,这项成就却被谴责为资本主义最恶劣的特征。
赫希曼在这本书中与斯密乃至韦伯一样,同样关注理性对资本主义行为合理化的作用,但他用更加具体鲜活的“利益观”取代了韦伯的“新教伦理”。这一论证路径的缺点是没有解释为何资本主义在一个地区得到接受的程度强于另一地区,好处则在于它为认识资本主义发生学提供了一个更加一般性的视角。我们也可以由此重新检讨一个被赫希曼一笔带过,没有深入讨论的问题:现代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张,与以往历史上的大规模征服有何不同?
赫希曼在全书结尾处谈到资本主义带来的“有益政治后果”时,引用了熊彼特的一个观点:“一般说来,领土野心、殖民扩张的欲望和好战精神并不像马克思主义者所说,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避免的结果。倒不如说它们产生于残存的前资本主义精神,然而不幸的是,这种精神在欧洲主要国家的统治集团中根深蒂固。”熊彼特并未涉及欲望和利益之分,但却暗含着这样一层意思:殖民扩张是源于赫希曼所说的“欲望”,而不是“利益”。在很多痛恨资本主义扩张的人看来,这种区分或许没有意义,但忽略这种区分,可能也意味着看不到历史上不断发生的征服与资本主义扩张有何性质上的不同。
我们不必否认,资本主义为殖民扩张提供了强大的技术和物质手段。但这种征伐与扩张的原始动力,与其说是来自资本主义本身,不如说同奥斯曼帝国、蒙古帝国或西班牙帝国的前现代扩张方式的关系更为密切。就如赫希曼所说,在16世纪的西班牙人看来,“尊贵之人靠征战获得财富,要比卑贱之人靠劳动挣钱更光荣,更快捷”。当他们从“大征服”中崛起时,这成了他们特有的基本信念。换言之,它背后的动力是作为“欲望”之古典含义的贪婪,而不是受到现代商业社会推崇的“利益”。
不妨这么说,满足欲望无法使人与动物相区分,获取利益才是文明人的特征。所以,从赫希曼的分析来看,这种扩张与掠夺的现象,也只能视为一种前资本主义欲望的遗存,而不是来自“开明的自利”——工商业阶层对“欲望”的一种独特理解。这个团体也重视民族国家的建设,但是与过去的征服者不同,它的“利益观”使它并不把国家的武力,而是把“温和得体的商业活动”,视为获取财富的主要手段。它最想直接获得的不是金银财宝,而是市场;它所建构的体制,也不同于近代之前的帝国体制,而是被差强人意地称为“资本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