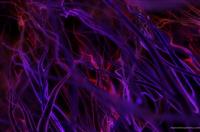华盛顿——
我们似乎正在进入一个巨型工程新时代,各国,特别是G-20国家,动员私人部门大量投资数百万美元(乃至数十亿、数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项目,包括输油管道、大坝、水利电力系统和道路网络等。
目前巨型工程支出每年已高达6-9万亿美元,约占全球GDP的8%,这意味着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投资繁荣”。而地缘政治、对经济增长的追求、对新市场的渴望以及对自然资源的搜寻正在驱使跟多的资金进入大规模基础设施工程。在前所未有的工程扩张潮中,世界领导人和贷款人似乎忘记了过去的代价沉重的教训。
诚然,基础设施投资可以服务于真实需要,有助于满足粮食、水和能源需求的预期剧增。但是,除非巨型工程的兴起得到小心引导和管理,否则它们有可能适得其反并且不可持续。如果没有民主控制,投资者将把收益私人化而损失社会化,采取碳密集和其他对环境和社会有害的方针。
首先是成本效率问题。各国不应该持“小即是美”或“越大越好”观念,而应该建设与目的相匹配的“适当规模”的基础设施。
专场项目管理和规划的牛津大学教授本特·弗吕贝格(BentFlyvbjerg)研究了70年的数据,最后得出了一个“巨型工程铁律”:它们几乎不可避免地将“超支、超时,反复超值超时。”他还说,它们还受制于“非适者生存”,建成的往往是最坏而不是最好的工程。
这一风险因为以下事实而更大:这些巨型工程大多受地缘政治而不是仔细的经济分析驱使。2000-2014年,全球GDP增长了一倍多,达到75万亿美元,而G-7国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65%下降到45%。国际竞争也随着这一再平衡而出现调整,美国开始担忧其霸权遭到新选手和机构的挑战,如中国领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西方领导的机构的回应是积极扩大基础设施投资业务和公开呼吁范式转变。
G-20也在加速启动巨型工程,以期在2018年至少提振2%的全球增长率。经合组织估算,到2030年将需要增加70万亿基础设施投资——每年平均支出略高于4.5万亿美元。比较而言,满足可持续发展目标每年预计需要2-3万亿美元。显然,巨型工程极有可能带来浪费、腐败和不可持续的公共债务。
第二个必须考虑的问题是地球的极限。2015年3月,一些科学家、环保主义者和意见领袖集体致信G-20,警告称加码巨型工程投资有可能给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灾难性伤害。“我们每年所消耗的资源总量已经达到了地球能力的1.5倍,”信中说,“基础设施选择应该减缓而不是加剧这一状况。”
类似地,气候变化政府间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PanelonClimateChange)警告说,“让社会陷入温室气体密集排放模式的基础设施开发和长期产品很难改变或改变成本极高。”事实上,G-20也没有对各成员国在其11月土耳其峰会上递交的巨型工程“愿望清单”做出社会、环境或气候相关标准的规定。
巨型工程的第三个潜在问题是它们依靠公私合作。在人们开始重新关注大规模投资的背景下,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多边贷款机构试图重新设计发展金融,其手段包括(但不限于)建立新的社会和经济基础设施资产类别以吸引私人投资。“我们需要获得机构投资者手中的数万亿美元……将这些资产导向各类工程,”世界银行行长金墉说。
这些机构希望用公共资金抵消风险,以此吸引长期机构投资者——包括对冲基金、保险公司、退休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它们总共控制着约93万亿美元的资产。它们希望,利用这一巨大的资本池能实现基础设施规模扩张、实现此前不可想象的发展金融方式转变。
麻烦在于,实现有竞争力的投资回报需要公私合作。结果,根据伦敦经济学院研究者的研究,它们“不是适合于[信息技术]工程的工具,也不适用于社会关注约束私人部门利益之所在的使用费的领域。”私人投资者寻求的是通过有保证的收入流和确保法律和监管(包括环境和社会要求)不影响利润维持投资回报率。风险在于追求利润将破坏公共利益。
最后,治理长期投资的规则没有有效地考虑将环境和社会风险,这也是工会和联合国环境署所强调的。将基础设施投资集合成投资组合或将开发部门列为资产类别可以大规模地将收益私人化、损失社会化。这一动态可能会加剧不平等性、破坏民主,因为政府——更不用说公民了——缺少制约机构投资者的手段。总体而言,贸易规则和协定将投资者的利益置于普通公民之前,这进一步复杂化了这些问题。
推进巨型工程的做法没有接受过考验,有可能——用致信G-20的作者的话说——“对危险的愿景加倍下注,”我们必须确保任何发展金融方式的转变都必须严守人权和保护地球这一前提,这一点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