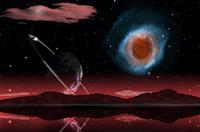公共外交的目标是什么?这些目标应满足哪些要求?如何实现这些既定目标?这都是各国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国家开展公共外交活动需要回答的实践性问题,也是公共外交理论的基本问题。本刊编辑部组织了多位学者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希望引起更多读者的关注,并参与讨论。
赵可金:作为一国的外交工具之一,公共外交的目标自然是执行一国外交政策。但是,与政府外交追求国家利益不同,公共外交是一种致力于打动人心的外交,以人为本是其核心要求。不管采取何种形式,依托何种载体,公共外交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能够吸引人、鼓舞人、说服人、打动人的。那些目标不明、片面追求大场面、搞形式主义的花架子,即使投入再大、人数再多,都无法实现公共外交的意图。
怎样的公共外交才能打动人和说服人从而获得民众的支持呢?公共外交要想实现自己的意图,关键是抓住事物的根本,牢牢把握以人为本的宗旨,尽可能追求打动人和说服人。
洪朝辉:在学理上,公共外交存在许多目的和目标,但在现实中,公共外交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最广范围地利用最多数民众为外交事业服务。基于此,影响公共外交这一目的的主要因素是难以利用最广大的外国民众的力量,参与本国公共外交的建设,要以目的统摄对象而非片面追求对象本身。各国公共外交实践中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个误区,以为公共外交一定是以本国民众为主体、以外国公众为客体或主要对象。
如果这一认识主导了公共外交的实践,那么美国跨国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为了帮助中国获得最惠国待遇,针对美国国会所从事的游说,就被排除在中国的公共外交之外,中国的外交就失去了一支强大的为中国利益而战的美国民众。同样,中国在美的跨国公司也有可能帮助美国政府,在中国推动有利于美国利益的公共外交。
王义桅:显然,公共外交的核心目标就是提升一个国家的软实力。然而,这一认知却受到了美国的干扰。尽管公共外交实践古已有之,但其概念的诞生,打上了冷战期间“和平演变”战略的深深烙印。正如《文化战争》一书揭示的,公共外交为美国赢得冷战立下汗马功劳。冷战结束以后,软实力理论的提出,增进了公共外交合法性,终于摆脱了“和平演变”的影子,名正言顺地登上了大雅之堂。
然而,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本是针对大国兴衰铁律、反对美国衰落论、提振美国霸权合法性而发明的。当冷战戛然而止,美国欢呼雀跃之余,软实力理论不幸助长了历史终结的错误解释,即将苏联体制的自我解体错误地解释为美国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而苏联相反。公共外交被无形中赋予了“天定命运”的宗教色彩。
迄今,美国的公共外交,欲正人,而非正己,崇尚“己之所欲,定施于人”。潜意识地认为自己的政策、制度、理念是正确的,因而极力劝说他人接受。这与孔子理念“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大相径庭。中国传统文化提倡“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与此一脉相承,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逻辑是“改变自己,影响世界。”因此,中国公共外交核心理念应回归古典而非学习美国。
刘宏:与一些学者强调公共外交的目标是塑造国家形象的看法不同,我认为公共外交的目标仍然是为了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既然公共外交的主导力量是政府,而其主要受众是外国民众和官员,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自然成为一个国家公共外交的主要目的。维护主权、统一及领土完整是我们的核心国家利益。在此之下,还有一系列的相关利益,他们因由时间和空间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呈现方式。例如,和平与发展、维系睦邻关系、建构和谐世界,成为我们外交活动的重要一环。但这些理念受到不同国家的政治结构、经济发展、宗教文化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阿拉伯世界所理解的和谐与欧美国家所理解的和谐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外延。
赵可金:首先,公共外交目标要明确。公共外交必须首先要明确锁定自己的外交对象,选择有意义的目标群体。群众是由众多群体组成的,究竟哪些群体会成为目标群体,往往取决于他们的态度。大致来分,无外乎支持我们的群体、反对我们的群体以及摇摆不定的“中间派”三类。很多研究表明,已经理解和支持我们的“铁杆粉丝”是我们的依靠力量,对我们充满偏见的“铁杆反对派”即便再怎么努力也无济于事,争取立场和态度摇摆不定的中间力量是公共外交的基础。
第二,公共外交目标要清晰。不要追求过于抽象的目标,要尽可能把目标分解为可操作、可测量和可监测的指标体系,尽可能掌握公共外交的广度和深度。有人认为,公共外交的目标是追求良好的国家形象,但如果不能将这一国家形象转变为可操作、可测量和可监测的指标体系,结果很可能是水中捞月。
第三,公共外交目标要合理。一个国家确定公共外交要避免过高、过大,超出公共外交的能力所及。一般来说,公共外交不是万能的,一个国家要想通过公共外交获得所有人的支持也是不可能的,只能是根据一个国家的国情和国家利益的要求,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合理确定目标的优先次序。对大国而言,公共外交往往作为硬权力的辅助手段,主要致力于改变形象或重树品牌(re-branding),以获得拥护和追随;而小国公众外交主要是为了引起世界传媒和民众的注意(captureattention),促进他国对本国的了解。在开展公众外交的范围和程度上,大国公共外交往往强调“广”(volume and breadth of message and image),而中小国家突出“精”(nicheareas)。
洪朝辉:实现公共外交目标,在方式方法上必须打破条条框框,不拘一格做外交。在实践中,公共外交主体和客体相混杂的特点,决定了作为中国公共外交客体的美国人,是完全有可能“返客为主”,成为推动中国公共外交的主体。基于“美国人影响美国人”更有效的经验,这种“返客为主”的途径、机制和条件,应该成为中国公共外交的战略战术,更应该成为中国公共外交的一大目标。
必须指出,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民族—国家的概念出现模糊,国界、国籍和肤色已经不是从事公共外交的必要条件。只要有利于中国的公共外交事业,中国就不应该拘泥于公共外交实施的地点和主体。也许美国跨国公司的主观动机是为了争取自身利润的最大化,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在客观上帮助美国民众改变对中国的误解和误信,更不排除他们有能力做成中国政府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所以,为了有效动员、利用和团结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中国的公共外交应该开拓外国民众的资源,推动跨国企业的公共外交。
刘宏:我们在推动公共外交时,要使自己的国家利益以当地民众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话语来表述。这需要我们因地制宜、因时而变,不能以划一的模式来实施公共外交。我们固然需要另起炉灶,建构一套以中国国家利益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和机制(这也是我们目前对外宣传部门的主要努力目标)。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应主动通过所在国家的主流媒体——他们的知名度和中立性相对较高,以灵活的和对话的方式,而不是居高临下的说教,直接或间接地表述我们的国家利益,其目的未必是要使外国人接受,而是希冀获得理解。(例如,通过历史证据、文化和经济联系,说明西藏是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
公共外交的最终目的和最高境界是使外国公众不仅理解,而且接受自己的国家利益,并将之转化为相应的内政和外交。20世纪50年代中国在印尼所推动的公共外交——虽然那时这个名称还未出现——就是个值得学习的事例。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和机制,例如出版和发行大量的有关新中国经济成就和社会发展的印尼文书刊(包括反映新中国建设成就的日历、年画)、文化和艺术使团的出访、接待印尼政府和民间人士、驻当地使领馆与印尼不同立场人士的广泛接触、与当地主流报刊建立密切联系。我们不仅塑造了欣欣向荣的国家形象,而且中国的政治模式和经济发展还成为苏加诺总统在指定国家政策时的学习榜样。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中国的软实力(“一国通过吸引和说服别国服从你的目标从而使你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能力”)还是很强大的。
在今天,虽然有关“中国模式”的内涵和特征还有不少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从我们的周边国家如老挝和越南到中东的埃及,对中国近三十年的发展道路甚为关注,也尝试借鉴我们一些成功的经验。对这些发展中国家而言,以中国的发展道路以及强调中国的发展给他们所带来的机遇,可作为发展中国公共外交的契机之一,这也有助于维护和发展中国的国家利益。
王义桅:中国是传统世俗社会,决定了中国的公共外交缺乏美国宗教般的进取性。中国公共外交理论与实践,必须回归传统文化和基本国情。制订我国公共外交路线图,应区分不同对象与不同发展阶段,回归古典理念。
智:主要针对欧美发达国家,即所谓“以小事大以智”。中国公共外交面临西方话语霸权与普世价值观挑战,不能指望“和而不同”就能息事宁人。对西方公共外交的智慧是让西方真正包容中国的崛起,实现东西方之间的殊途同归,增强我国政治上的影响力。
仁:主要针对周边国家,即所谓“以大事小以仁”。中国公共外交面临周边现实忧虑与历史误读,不能指望“互利共赢”就能让对方心悦诚服。对周边公共外交的仁义,是让周边国家真正感受并欣慰中国包容周边发展的理念,增强我国形象上的亲和力。
悌:主要针对新兴国家,即所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对新兴国家公共外交的悌道,是构筑与新兴国家共同崛起的战略保护带,增强我国经济上的竞争力。
恕: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即所谓“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对发展中国家公共外交的恕道,是让发展中国家真正视我国为命运共同体,增强我国道义上的感召力。
赵可金: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是一个挑战现有格局的力量,随着中国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必然会引起一些国家的防范,特别是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面对中国的崛起,必定会产生某种疑虑和担忧。在经济实力成为第二世界经济大国后,限制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主要来自于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军事威胁论、经济威胁论、发展模式威胁论、新殖民主义威胁论。所有这些“中国威胁论”从根本上都是对中国不理解、不认可和不接受。因此,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如何通过公共外交化解来自国际社会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积极澄清、解释、沟通,让国际社会接受一个和平发展的中国,就是中国公共外交的合理目标。除了消除那些对中国不理解、误会甚至为了故意“寻找敌人”而强加给中国人民的“种种罪名”之外,中国政府还必须根据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和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愿望,充分展现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形象,不断促进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理解,消除误会,带领中国社会以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大国身份加入国际社会。这既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也是全世界追求和平、发展和自由的共同愿望。
王义桅:公共外交在中国已从学术词汇、媒体名词,变成一种政策流行语了。作为本届政府的最大外交亮点之一,公共外交在中国从未受到如此重视。然而,公共外交毕竟是“舶来品”。公共外交热的背后,不乏由于急功近利导致认识上的模糊和实践上的盲目。概括起来,存在“四化”倾向。
一是庸俗化。主要表现是:将公众与外交的联系,泛化为公共外交,或将公共外交简单作为“外交以民为本”的体现。更有甚者,把什么都归结为公共外交,自甘陷入“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的困境,致使公共外交不断被异化、庸俗化。其实,任何时候都需强调,基本政策是根,公共外交是叶,千万不能本末倒置。
二是异化。毛泽东当年说过,美国是钢多气少,所以是纸老虎,而中国则是钢少气多,因此敢跟美国叫板。软实力概念的提出,本为给美国“补气”。然而把握不当,可能成为“气短”的代名词。面对世界“拿中国说事儿”,我国如缺乏整体战略,或怕引发外界猜疑而不敢推行对外战略时,美其名曰“公共外交”,其实违反了国家利益,与公共外交捍卫国家利益的初衷背道而驰,导致公共外交的异化。
三是神化。正如管理能创造效益但不能代替生产一样,公共外交不能解决国力增长的根本动力等问题,对于外界误解也是治标而不治本。这就是公共外交本身的局限。针对国外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傲慢论、中国强硬论,公共外交绝非万能膏药,制度建设和核心价值建构才是根本。况且,做得再好,实力强了人家也必然担心。西方借炒作“中国威胁论”的同时也为刺激、警醒自己。
四是民粹化。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让民众理解和支持外交(在美国,这称为公共事务),本是件好事情。但随着民意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外交如果受制于民意而畏缩不前,怕承担责任、怕背负历史骂名,其结果,就是越来越远离战略。所谓的公共外交,便不幸沦为民粹化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