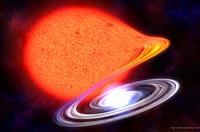一
学术生产在早期阶段便具有强烈的现实情怀。孔子之所以整理诗书等历史文化遗产,就是为了彰显“仁道”,以之来改造春秋以来被权力、财富争夺扭曲的人心与天下。近代,马克思亦曾批判古典哲学多是围绕“抽象”的人类展开学术生产,很少揭示人类实际生活在什么样的“现实”里,其中有何苦难与不义,以及如何重建苦难与不义叠出的世界。到费孝通先生这一代,最初之所以努力发展“科学”的社会人类学,亦是为了“对我们所生活在其中的中国社会有清楚的理解”,创造“一些能改造社会、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即使像韦伯那样高调主张学术生产不该涉及任何人间是非的学者,也无法真正做到将现实情怀从其学术生产中清除出去。
言外之意,提及学术产生的现实情怀时,已不必再去思考学术生产是否应介入现实,而大可以直接探讨学术生产应具有什么样的现实情怀,或者何种现实情怀值得学术生产为之坚守等更有实质意义的问题。就此问题而言,很容易让人想起国内上世纪90年代的学术状况。其时,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许多学者纷纷“下海”,选择留守学院的学者不得不严肃思考:在社会转向经济的巨变时期,留下来做什么。思考的结果往往是“安心做学术”。至于做什么样的学术,留守学者也通过研究民国学术史,给出了前进路径及参照典范。胡适、章太炎、陈寅恪、王国维、钱穆等长期被埋没的民国学人,亦随之翻身成“大师”。似乎只要厘清这些“大师”的学术踪迹,沿着走下去,就能生产出有意义的学术;并且,其中的意义除表现为学术创造、学者人格上的继往开来外,还包括找到了适宜的现实情怀与责任担当,足以在巨变时期彰显学者及其学术生产的政治社会价值。
以胡适为例,其便让许多留守学院的学者走出了上世纪90年代初的迷惘,得以一面安心生产更精湛的“考据”文章,一面努力在公共媒体领域传播旨在推动社会进步的思想“常识”。其他与胡适相比更为书斋化的民国学人,如陈寅恪、王国维、钱穆,则让留守学院的后辈追随者觉得,即使退居书斋一隅,缺乏直接的现实介入,其在“故纸堆”里略显寂寞的历史文化“考据”实践,也照样能肩负起重要的现实关怀,以历史考证及书写的方式在西方文化强势影响犹在的时代,捍卫、延续本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文化命脉与文化精神。耳濡目染的年轻学子亦可能领悟到,看似“百无一用”的书生及其远离现实的学术生产,其实也能承载某种大气的既包纳西方又不失自信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现实情怀。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学领域也有许多留守学者在努力探索富有意义、具有厚重现实情怀的学术生产。相比于文史学者乐于将各自中意的民国前辈列为学术榜样,这些学者选择学术典范时则更重视西方前辈学人,韦伯、福柯、布尔迪厄等西方社会学“大师”的理论遗产随之被齐齐引入国内。从后续进程来看,向西方社会学“大师”学习的学术重建努力可谓相当成功,它不仅为社会学者提供了“理性化”、“科层化”、“权力”、“场域”、“沉默”等众多有效的现实及历史结构分析工具,而且让人看到了学院里的学术生产还可以肩负起另一种现实情怀:它不是通过考察本国历史文化,曲折表达坚守文化认同的“苦心孤诣”,而是直接进入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现场”,使学术生产能够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的种种问题,尤其与农民工、打工女等各类“无名”底层的生存状况及苦难命运,形成紧密关联。
值得一提的是,社会学领域的理论引介与学术生产重构努力,甚至还对文史学界的学术进展产生了影响,乃至使文学、史学等领域兴起理论选择不一的“社会学转向”。以文学领域为例,便有诸多学者不再埋头解读本国文学经典或历史文化遗产,而是像英国伯明翰学派发起“文化研究”那样,通过转向社会学,引入社会学的理论视野与工具,将传统的文学研究改造成深入考察当代中国的文化社会变迁及问题。为拓展学术生产,充分吸收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有的学者还在文学系之外另立“文化研究系”,对当代中国的流行文化生产以及经济社会转型引起的道德、教育、环境危机及农村境遇等展开研究。原本与现实不直接相关、主要以历史文化梳理为主的文学学术生产,即因这些体制及理论重构,而可以“有效参与社会的良性变革”。
至此可以看出,就当代中国人文社会学界的学术生产实践而言,对于学术生产应具有什么样的现实情怀,或者何种现实情怀值得学术生产为之坚守,其实至少已形成两大广为认可的解答:一是退守书斋,以历史文化研究的方式,保卫当代中国仍不能失去的文化认同与文化生命;二是置身当代中国社会“现场”,并以各种有效的理论工具与学术生产直接介入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以期能够优化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我们很难判断这两大现实情怀之间哪一个更值得以身相许,只知道两者之所以能够形成,皆离不开对中西前辈学人的学术遗产展开梳理。对现实情怀尚不明确的年轻学者来说,这一点或许尤其值得重视。
二
21世纪以来的新一代学人要想确立值得追求的现实情怀,其实一点也不难。只要从学术史的角度稍微梳理一下上世纪90年代崛起的当代学人或清末民初的前辈学人,便可以为自己的学术生产打上明确且值得以身相许的现实情怀。对新一代学者来说,真正的困难也许在于,即使现实情怀异常明确了,往往也很难在学院中将其落实在学术生产实践中。有的甚至认为当下学院已生产不出像样的学术,还不如民国时期的学院。这里无意卷入此类厚古薄今的是非之争,而只想围绕包括民国学术生产在内的古今事实,从大学建制、学院体制及背后的干扰力量入手作一些展开,探讨落实现实情怀时可能遭遇的困境。
从教育史的角度看,有无大学建制,以及有什么样的大学建制,对于现代学术发展尤其是学派的形成与壮大意义重大。考察中国社会学发展历程时,亦应当留意大学建制在学派形成中的重要作用。
众所周知,严复、章太炎、梁启超等乃是中国社会学的开拓者。在这些开拓者的努力推动下,清末中国曾兴起一场学术变革运动。不过这场运动主要表现为以西方社会学思想或理论来革新中国传统经史之学,而不是在大学里建立专门机构来发展社会学。值得一提的是,清末一些教会大学曾开设社会学课程。比如,1908年,圣约翰大学就开设了社会学课程。1913年,上海私立沪江大学甚至成立了社会学系。但这些大学建制实验皆由美国人主持,若谈什么学派建设成就,也只是在扩大美国社会学派之于中国教育界的影响。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4年后,康心孚在北京大学正式开设社会学,民国时期由本国学者主持的社会学大学建制由此拉开序幕。可惜,课讲到第三年,康先生便去世了,中国社会学最初的大学建制成就,仅是培养了孙本文等青年学子。而这些青年学子还要坚持十年,亦即从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归国以后,才可延续康先生开启的社会学大学建制事业。
北大社会学系简史
进入1920年代以来,有越来越多的大学乐于将社会学纳入学科体制,且其纳入方式不是仅在法商等科下开设社会学课程,而是创办社会学系。1921年,厦门大学、复旦大学率先成立社会学系。1922年,燕京大学成立社会学系。1924年,由厦门大学分裂出来的大夏大学成立社会学系。1925年,清华升格为大学后同样成立了社会学系。1927~1928年,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也先后开办社会学系。原本只是一门课程的社会学在大学里迎来了体制崛起,而且与“五四运动”以来一度繁荣的学科(如教育学)到20年代中后期突然遭遇学院生存危机不同,社会学在大学里的体制崛起一直没有中断过。比如,以孙本文为代表的综合学派,以吴文藻、费孝通为代表的社区学派等当代社会学子熟悉的中国社会学派,便都是大学建制的产物,也因此这些学派往往还被冠以大学之名,如燕京学派、金陵学派、清华学派。尤其是陈达、潘光旦、费孝通等领衔的清华学派,更是被外界(如史学界)视为“最出色、最成系统”。
而清华学派之所以能成为民国时最出色的中国社会学派,又与清华大学及其社会学系的独特建制密切相关。
学生培养方面,清华自升格为大学起,便在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吴宓等人主持下,定下了独立自主的通识或博雅教育基调,强调在汇通古今中西的基础上从事学术研究,确立专业问题之前都须修读公共必修课程,包括国文、英文、通史、数学、自然科学;之后的培养也重视选修课,且没有院系限制。像费孝通先生到清华求学后,就因体制特殊得以“补习解剖学和动物学”,且因为“研究需要还学了数学”。晚年重建社会学时,费先生仍不忘提醒要改革“许多大专院校仍然是文、理分科,隔科如隔山”的体制状况。
教师学术创造方面,郑航生先生近年曾指出,一种来自美国的说法即所谓“近亲繁殖”对中国的学派建设不利,容易导致学科带头人即使培养出得意弟子,也无法将其留下传承、创新学术。他甚至说:“‘近亲繁殖’的说法,对中国学派发展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相比之下,民国时的清华则不会机械照搬美国制度,而是尊重本国传统的师徒学术传承方式,甚至给学科带头人的得意弟子提供公费留学深造,然后等其回来传承创新学术。对于看中的年轻学者,无论其是否有无清华学脉,只要学术志向、品格与能力确实优秀,便直接让其做教授。尤其是服务5年之后,便可享受带薪休假出国进修,在当时更是绝无仅有。清华体制背景及经费来源本就不一样,加上又有特殊激励,其教授体制待遇在当时堪称最为自由优越。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起,即使北大,也会出现人才南流;而清华则能把许多外面的优秀教授吸引过来。
三
事实上,自民初学院体制逐渐成形、壮大以来,深处其中的学者便很容易背离此前设定的现实情怀。仅仅为保住学院位置便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与各方周旋,无论行政主导,还是“教授治校”,皆如此。以胡适1917年初入北大为例,便曾在蔡元培、陈独秀、章太炎弟子、桐城派、北大学生领袖等多路势力中小心周旋、巧妙援引。胡适堪称善于应付复杂人事,但仍难有宽裕的学术生产时间。等其脱颖而出成为蔡先生器重的新一代学术教育领袖,摊子越铺越大,更不得不将大部分精力用于维持局面与地位。如此何以可能安心践行其当初形成的极具现实情怀的学术生产,即通过“中国哲学史”研究向国人传播“科学”、“民主”等“新思想”。没几年功夫,胡适便因心力憔悴及个人情感无以寄托,不得不任性跑去杭州调整。当代学院里的学者,即使仍在“教授治校”的体制下从事学术生产,亦难逃学院体制内的复杂人情世故,不得不做许多与学术生产无关的低调周旋。耐心,而非牢骚,由此成为关键。
再看学院体制背后的干扰力量,亦存在一大困境,即学者一旦受其干扰,便更容易远离其当初想要关怀的现实。仍以胡适为例,成名之后,胡适交往圈越来越大,但其扩大方向不是平面或往下,而是往上,结果让自己变成了大都市“贵族”中的一员。如艾恺所见,当最初同在北大任教的梁漱溟由上转下从事乡村教育改革时,“胡适正住在上海的租界里,或旅游欧陆去结交洋人及‘洋化’的知识分子,就餐于这个或那个城市豪华的餐厅,时而又在餐余打牌消夜。总之,他过的正是梁漱溟极端鄙视的‘贵族’生活”。
其实,就清华社会学派而言,最值得称道的是其学术追求。从陶孟和起,中国社会学的核心使命就是通过“社会调查”认识苦难深重的中国社会历史与现实。新生代学者也不难领会陶孟和以来中国社会学的学术追求,以及自觉坚守中国社会学的学术初心。但当代学院背后的干扰力量同样复杂,商业性的学术评价机构弄出来的大学排名及学术评价指标,近些年影响越来越大,学院学术生产及发表成果的学术期刊都被其绑架,以致新生代学者很难安心去做“田野工作”,很容易(被迫或主动)把发表SSCI论文当作头等大事,乃至围着西方学术期刊的要求打转,远离苦难犹在的中国社会,或者情愿一年炮制几篇论文,学术生产随之只能远离现实。就此而言,还得改革当前学术评价机制,方可珍视中国社会学的学术追求,形成更多、更优秀的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