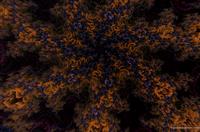导论
迄今为止,学界对民主化研究的热度似乎依旧没有衰减。不过,长久以来存在的一个假定是,“民主”与“民主化”都存在某种“一般模式”,对发展中地区来说,建立民主的过程就是此种“模式”扩散或移植的结果。
这一假定的出现既有理论上的原因,也源自实践中的需求。从理论上来说,任何社会科学研究都追求发现类似物理学中定律的“一般模式”。这种学术上的冲动激励着学者从纷繁的现实中归纳出某种“简洁”且“可重复”的规律。对民主和民主化的研究尤为如此。从实践上来看,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的“民主输出”也需要某种“指挥棒”来引导,以提升可操作性和效率。因而,某种意义上的“理想型民主”就被建立了起来。这样,“民主输出”就可以简化为某种模仿行为。
但一些学者发现,在一些不具备实现民主的“支持性条件”,因而常常被归类为“不可能”或“最不可能”的地方——例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时常会出现成功实现民主的案例。这些案例被称为“异常民主政体”(deviant democracies),贝宁、博茨瓦纳、哥斯达黎加、蒙古以及印度等国,是其中典型案例。这类案例的存在,使得学者们开始反思民主化理论或民主化的“一般模式”。在此背景下,本文选择了博茨瓦纳(Botswana)这个“异常案例”来检视既有的民主化理论。
自1966年独立至今,位于非洲的博茨瓦纳一直保持着民主体制良好运转的记录,但它实现民主的路径并不符合民主发生的“一般模式”。这一“异常性”源自何处?对博茨瓦纳“异常性”的解释又能为我们理解民主与民主化带来什么?本文将尝试回答这两个问题。
2014年10月28日,成功连任的博茨瓦纳总统伊恩·卡马在首都哈博罗内的议会广场宣誓就职。国际在线资料图
一、民主化的“一般模式”
随着研究方法与视野的开拓,当下的民主化研究与过去相比已变得更加精密与复杂。但这并不意味着学者们放弃了建立有关民主化或民主发生“一般模式”的理想。归纳来看,这类“模式”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其一,经济发达产生民主。
由于经济与政治的天然联系,经济发展被众多学者认为是推动民主发生的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因素。几乎每一位民主化的研究者都有证据支持这样的论点,即民主更容易在较发达国家出现。研究者多用人均GDP这一指标衡量“经济发展”,找寻某种能触发民主化的“临界值”更成他们不懈努力的目标。例如,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1927—2008)曾指出,在“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中,经济发展能促进政治民主。在这里,亨廷顿所选定的“中等经济发展水平”标准是“人均GDP位于1000至3000美元(1976年价格)之间。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币值的变动,也有学者认为,这个“临界值”如今已经升至5000(现价)美元。
当然,近来的研究大都承认经济发展与政治变革之间关系的复杂性。换言之,当下已经很少有人坚称经济发展与民主化进程存在线性相关关系,即“经济发展一定会促成民主化的发生”这一命题是站不住脚的。甚至有学者指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进一步的增长反而可能削弱民主政权存在的可能性。
图1. 经济发展与民主概率的关系。 来源:Barbara Geddes
经济发展(development)与民主化之间固然不存在严格的线性关系,但经济发达(developed)或富有与民主之间的正向关系却很少被质疑。据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系教授芭芭拉•格迪斯(Barbara Geddes)所绘制的经济发展与民主(实现)概率之间的关系图(图1),经济发展与民主化之间的确是一种非线性关系(S形曲线)。但是,格迪斯并不否认,经济发展超越某一水平后,实现民主的概率几乎等于100%。与之相若,纽约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等人认为,民主一旦建立,只能在拥有一定经济水平的国家中存活。
其二,现代社会精英促进民主化。
除了经济发达之外,现代社会精英对民主化的支持也成为论者尤其是现代化论者普遍赞同的观点。也就是说,民主的发生需要亲民主精英群体的支持,这类精英群体的最大来源是所谓“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不论是从词源还是历史演进来看,“市民社会”都是与“城市”或“城市化”相联系的,而城市化又被视为社会现代化的重要表征。可以说,城市化之所以是民主化的支持性条件,是因为其“生产”出了新的社会精英。
这里,民主化的机制在于基于城市的新社会精英(经常是组织化的)对基于农村的旧社会精英(据称,对民主化的抵制便来源于此)的挑战。在前者取代后者之后,脱离了传统人身依附关系的新精英之间形成了较为理性化的新关系形态,并通过相互妥协,最终将民主规范作为解决问题的原则。
当然,民主也并非总是社会精英刻意设计的产物,有时可能只是新崛起的精英或阶层对政治体制需求变化的“副产品”。例如,城市中产阶层一方面需要参与政治来阐明自身的诉求,另一方面也极力抵制国家权力可能对其(财产)造成的侵害。
其三,民主观念(文化)支撑民主化。
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内部政治感情、政治态度和政治信仰的统一体。因而,它从本质上来说是观念性的。自1960年代以降,“民主转型与巩固需要某种形态的政治文化”的论调一度被民主化研究者奉为圭臬。尽管有不少人指出,这一论点大多以“民主的文化让人们认同民主从而促成民主”的同义反复形式出现,但近年来,随着各类民意调查与对政治文化定量研究的兴起,这种论点的同义反复性因被赋予更加细致的定义而有所降低。
我们认为,“民主文化”事实上可以分解为两个民主化实现的重要“观念条件”。一方面,民主的实现不应仅依赖于精英的赞同,也应得到广大普通公民的支持;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民众对民主的支持并不能只是“口惠而实不至”,而应成为一种“信念”。在具体评估当中,“民主信念”又被分解为两个要素,一是对民主的“无条件支持”,即在对实际民主运作不满意的情况下仍选择支持民主;二是低度的威权主义取向,即无条件反对且不向往威权政体。
其四,外力助推民主化。
对后发或发展中地区来说,实现民主化的过程均存在外力的作用。在这里,“外力”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是国际干预。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Robert Alan Dahl,1915—2014)在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实行民主政体的国家进行研究时发现,在被选取的29个国家中,有14个是在国际干预作用下实现向多头政体(民主政体)快速转变的。国际干预的首要实施者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其“民主输出”策略主要表现为美国对其正式盟友的民主化改造、美国对其他非西方国家实施“政权更迭”以及欧盟为新成员设定的民主条件。此外,“附带政治条件”的经济援助也是西方国家输出民主重要手段。第二是扩散效应。民主化也可以通过邻国的压力得到实现,一般认为,如果某国周边邻国均是民主国家,那么这种“氛围”和“示范效应”会促进该国民主化的发生。最后,对一些前殖民地来说,宗主国的殖民方式或传统对当代民主的建立也有一定作用。比如有学者指出,相比于西班牙或法国,英国的殖民地较易实现民主化,因为英国殖民的手段较为间接与温和,也更愿意在殖民地建立英式法治,这种基础性条件对于日后的民主化有着促进作用。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外力在一个国家民主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并不是稳定的。其发生作用的效果,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比如融入国际体系的深度、与西方的距离以及外国影响力的强度。因此,外力也并不总能带来民主化。
博茨瓦纳位于南部非洲,面积并不大。但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包括其非洲同侪相比,博茨瓦纳在政治发展上算是“异类”。
首先,博茨瓦纳的民主化进程可谓一帆风顺。自1966年独立至今,其民主体制一直运转良好,并未出现明显的政治倒退现象。图2显示,博茨瓦纳的“政体指数”评分(Polity IV)一直保持在6分(即“民主”)以上(另两个取得如此成就的非洲国家是纳米比亚和毛里求斯)。相比之下,博茨瓦纳周边很少出现稳定的民主国家。例如安哥拉和津巴布韦,不仅一直维持着威权政体,而且还深受旷日持久的内战等政治动荡之苦;其最大邻国南非也曾长期实行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制度。
图2.博茨瓦纳、津巴布韦与安哥拉的政体指数得分变动 数据来源:政体指数网站http://www.systemicpeace.org/polity/polity4.htm
其次,民主政治与政治稳定在博茨瓦纳同时实现。每五年一次的国会选举已成为博茨瓦纳唯一有效的政权更替方式。博茨瓦纳民主党(以下简称“民主党”)通过获得选举胜利而非操纵或强制实现了长期执政,反对党也能做到“愿赌服输”,没有出现“输家政治”式的政治动荡。在最近一次大选(2014年)中,博茨瓦纳国内最大的反对党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主导成立了一个反对党联盟——“民主变革之伞”(Umbrella for Democratic Change)。这一联盟在本次大选中一举拿下57个议会民选席位中的17席,其与另一个反对党国会党(Congress Party)的得票率之和超过了50%,而执政的民主党席位则降至37席,得票率也仅为46%左右(由于博茨瓦纳实行的是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制的选举制度,所以会出现“胜者全赢-过度代表”以及“败者全输-代表不足”的状况)。
图3. 2004-2014年博茨瓦纳各政党在大选中的席位
数据来源:各国议会联盟网站http://www.ipu.org/parline-e/reports/2041_arc.htm(注:2014年“国民阵线”一项统计的是国民阵线与其他小党所组成的反对党联盟的席位。)
再次,更值得注意的是,与印度、蒙古及其他非洲国家不同,民主制为博茨瓦纳带来了良好的治理结果。博茨瓦纳自独立以来,从一个贫穷的国家一跃成为非洲经济发展较快、经济状况较好的国家之一。特别是在1967年发现钻石之后,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并在1985年至1994年间显著脱贫。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经济依旧保持中速增长。据统计,2004年至2007年该国GDP平均增速达到5.5%。到2014年,人均GDP已达7123.34美元,并取得中等偏上的人类发展指数分值(0.68)。
第四,钻石储量丰富的博茨瓦纳避免了一般资源丰富的后进国家通常会出现的 “资源诅咒”现象。在社会政治方面,博茨瓦纳自独立之后没有出现过内战以及大规模的族群冲突,并且成功实现了对腐败的遏制,2015年博茨瓦纳的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 CPI)得分为63,在168个国家与地区中排名第28位。
这样看来,博茨瓦纳的民主化是相对成功的。但这种“成功”却与民主发生的“一般模式”不相符合。
首先,在民主体制建立之时及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博茨瓦纳的经济发展水平都不算高。博茨瓦纳独立之前既无工业也无矿业,其经济停留在农牧业层次,极其落后,曾被西方预测为“无发展希望的地区”。1966年获得独立时人均GDP仅84.29美元,甚至在独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其经济水平都没有达到亨廷顿早先所确定的“民主转型的经济临界点”(即人均GDP1000至3000美元)。九十年代中后期,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博茨瓦纳人均GDP逐渐达到并超过3000美元,经济发展达到“中等水平”。不过,根据某些学者所言,这一经济发展水平并没有很高的民主实现概率(参见本文图1),甚至还可能出现颠覆和回潮。
其次,博茨瓦纳的社会现代化程度不足,难以产生足够的现代政治精英。总体而言,博茨瓦纳在独立并建立民主制度之时,并不存在强大的“市民社会”以及大量的现代社会政治精英。1966年独立时,博茨瓦纳的农村人口比例高达95.4%,到1985年这一数字还在70%以上。时至今日,农村和部落的旧精英群体依旧强大。根据国际性研究项目“非洲晴雨表”(Afro-Barometer)的调查,至今依旧有72%的博茨瓦纳受访者认为传统领袖值得信任。
第三,政治文化亦不足以解释博茨瓦纳的民主化进程。首先,博茨瓦纳与大多数非洲国家一样,有长期的殖民历史,外加社会现代化程度不足,因此有学者认为该国社会在政治上完全是被动的,这一局面甚至在今天都没有改变。独立之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博茨瓦纳上下并没有形成一般意义上的“民主文化”。根据八十年代的一项调查,只有47%的博茨瓦纳受访者认为多党民主选举很有必要,民众更愿意接受精英的统治。非洲晴雨表的调查显示,直至2014年,也仅有64%的博茨瓦纳受访者在支持民主的同时选择拒绝其他各类威权政体(这一指标被用来衡量“对民主的需求”)。这一数字与该国15年前的调查结果一模一样,也远低于毛里求斯的77%和塞内加尔的72%。
最后,“外力”在博茨瓦纳的民主化过程中总体来说并不显著。从其周边的状况来看,博茨瓦纳的民主并非来自邻国的“扩散”。博茨瓦纳独立时,周边大都是殖民地,独立之后还在一段时间内被视为实施种族隔离的南非“潜在的外部影响门户”。另外,如上文所述,该国至今仍被两个威权国家“夹击”。
从西方的干预来看,博茨瓦纳并没有受到来自美国“民主输出”策略的明显影响。那么英国殖民的作用呢?确实有学者将博茨瓦纳的民主化归结于英国的殖民。英国在“殖民撤退”的过程中大都会在殖民地进行“还政于民”式的政制改革,博茨瓦纳也不例外。早在1966年独立之前,当时的贝专纳兰(Bechuanaland,博茨瓦纳1885年起在英国殖民时期的称谓)就在英国的主导下组织了政党,举行了选举。然而,这种论调只能说是部分正确。需要注意的是,非洲大陆的大多数国家都有殖民历史,不少国家也曾是英国的殖民地,它们也在宗主国“撤退”的过程中建立了民主制。但长期保持稳定有效的民主政权在非洲并不多见。
综上,博茨瓦纳是在缺乏民主的“支持性条件”下实现民主转型和巩固的,因而可以被归类为“异常民主政体”或民主化的“异常案例”。
博茨瓦纳等“异常案例”的出现,为民主化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本文将从民主化之前与民主化之中两个阶段出发来探讨该国民主化相对成功的原因。
在第一个阶段即民主化启动之前或曰启动之时,博茨瓦纳已经完成了社会政治整合。这一“先置整合”的完成有赖于三个因素所组成的整合机制。
第一个因素是英国的殖民遗产。
在殖民撤退之时“还政于民”一般而言是英国殖民者的惯用策略,因而这也成为许多前英国殖民地民主转型的滥觞,博茨瓦纳也概莫能外。然而正如前文提到的,除了博茨瓦纳之外,许多国家也曾是英国殖民地,也在英国殖民撤退之时建立了西式民主制度,却没有在之后实现民主的巩固。因此,一方面英国殖民不一定能够带来民主化,至少不一定带来巩固的民主制;另一方面,即便讨论英国殖民遗产对殖民地民主化的作用,也不能只讨论“殖民撤退”而是要观照整个殖民时期。
根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系教授达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等人的研究,总体而言,贝专纳兰即殖民时期的博茨瓦纳拥有一套相对具有包容性的殖民体制。这套体制源自贝专纳兰传统的族群议事大会(Kgotla),这是一种前现代的协商政治形式,在传统精英与民众之间建立了一种有机的联系,在扩大参与的同时也抑制了精英的恣意妄为。由于英国殖民者善于“依俗而治”并且博茨瓦纳并非大英帝国在非洲的核心殖民地,因此英国在建立了殖民秩序后并没有过多干涉贝专纳兰的内政,也没有试图改变其传统的制度。另外,英国殖民者在贝专纳兰建立的一套现代法制以及一些鼓励本土民众(尤其是黑人)参与的制度也具有一定的包容性。
第二个因素是政党及政党政治的制度化。
政党与政党制度是理解博茨瓦纳民主化成功的关键。首先,博茨瓦纳国内各政党发育状况良好。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历史遗产。一方面,博茨瓦纳在取得独立之前,竞争性选举便已存在,这为政党的产生提供了基础性条件。另一方面,博茨瓦纳的独立并非通过发动战争取得,在独立之后也未经历过战争,其建国精英也并非军人出身,结果,博茨瓦纳的军队力量相对较弱,这为博茨瓦纳国内政党和政党政治的发育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其次,博茨瓦纳各政党之间的竞争烈度低且较为有序。博茨瓦纳的政党体制属于温和一党制。长期处于执政地位的民主党依赖政策绩效而非通过操弄意识形态、肆意修改法律、操纵选举或暴力镇压反对党等方式获取竞争优势。1990年之前,反对党在大多数非洲国家里都被认为是非法的,只有博茨瓦纳从1966年开始一直维持了多元主义的局面。在博茨瓦纳,反对党虽不能完全取代执政党,却能对后者实施有效制约,后者也无法绕开前者实施威权统治。例如,博茨瓦纳民主党在决策前时常邀请反对党领导人召开圆桌会议。
再次,博茨瓦纳政党与政党政治的制度化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政治精英的选择。与非洲那些选择一党制或无党制(如军人统治)的政治精英不同,博茨瓦纳“国父”塞雷茨•卡马(Seretse Khama,1921—1980)更倾向于做一个有节制的政治强人。他创立了民主党,但又在独立之时主导制定了一部多党共和制宪法,并将多党制明文载入共和国的宪法中。当其退出政治舞台时,其家族并未继承总统的职位。今天的博茨瓦纳总统伊恩•卡马(Ian Khama)尽管是老卡马的儿子,但他的上台与连任都是通过竞争性选举实现的。
上述事实证明,博茨瓦纳相对制度化的政党与政党政治一方面解决了政治精英的代际更替问题,另一方面实现了政治领域内的整合,有效防止了政治恶斗与政党体制碎片化的出现。
第三个因素是酋长院的设置。
博茨瓦纳民主化的过程并不是一个激进的颠覆过程,相反,存在某种制度上的妥协,从而避免了新旧制度之间的冲突,实现了传统与现代以及新旧精英之间和解,最终保障了新生民主制度的生存。博茨瓦纳制度妥协的集中表现是其宪制中对酋长院(Ntloya Dikgosi)的设置。前文提到,博茨瓦纳的传统制度在殖民时期得到了较好的保留,酋长院便是其中代表。从源流上来看,酋长院既可以被视为前文所言之传统族群议事大会的延续,也可被看做对英国殖民时期“黑人参议会”的继承,并且有了新的发展。
根据最初的制度设计,酋长院由博茨瓦纳八名主要族群的代表、四名少数族群的代表以及三名酋长院特别挑选的代表所组成;在功能上,酋长院有议事权而无立法权;最后,酋长院成员不得有政党背景。因此,酋长院是一个相对去政治化的机构。在其后的沿革过程中,酋长院逐渐成为更加中立、公平的议事机构。进入二十一世纪,经相关法案修订,八大部族逐步去除特权,少数族群的法律地位获得了承认,族际平等得以进一步实现。2007年,随着博茨瓦纳宪法的修正,酋长院的人员构成发生了变化,更具多元性与代表性,对缓和族群冲突起到了推动作用。
比较而言,博茨瓦纳酋长院的设置更加成功,原因包括以下方面。首先,酋长院成功地将传统精英有效纳入民主体制之中。传统精英在新政治体制中的特权、地位和发言权得到了保障,首领们继续得到该国政体中成员们的尊重,消解了他们反对甚至颠覆民主体制的动机。其次,酋长院的设置保证了新精英在国家治理方面的实质权力,同时将他们的言行限制在了一定的制度框架和范围内。特别需要强调的是,通过制定《酋长法》和《地方政府法》等法律,博茨瓦纳实现了国家对暴力的垄断,极大地降低了暴力弥散化的概率。其三,在酋长院的框架下,部族首领没有干预非传统事务如立法和审理刑事案件的权力,这有力保证了现代法制的公平和效力。
在第二个阶段即民主建立之后或者说民主化进程中,博茨瓦纳经历的一些事也值得简要讨论。在这里,我们主要选取的是一个偶然因素——资源即钻石矿发现的时间。
比较历史分析很早就揭示,相同几个事件(events)发生的时序不同会造成结果的差异。在博茨瓦纳的案例中,钻石矿发现的时序大大消解了“资源诅咒”出现的可能性,避免了由此造成的制度退化或民主崩溃。
首先,钻石矿是在博茨瓦纳建立民主体制建立后发现的。独立之前,博茨瓦纳曾被列为“贫矿国”。该国1967年首次发现钻石,钻石矿脉要到1972年才被发现。此时,博茨瓦纳民主制度的约束力已经存在,这使得由钻石产生的财富不至于过分集中于统治精英。现实中,博茨瓦纳的钻石资源收益也的确用之于民,为该国提供了良好的公共服务。其次,博茨瓦纳钻石矿是由外国人先于本国人发现的。首次发现钻石的戴比尔斯公司(De Deers)是一家英国公司,在发现钻石以及矿脉之后,它与博茨瓦纳政府成立了合资公司,因此博茨瓦纳的钻石收益不全是给该国政府。这也促使博茨瓦纳政府决心推进产业多元化(包括农牧业与旅游业),摆脱资源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
以博茨瓦纳为代表的民主化“异常案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首先,“异常案例”的存在有力说明民主化并不存在所谓的“一般模式”。民主化是学术界颇为重视的一个研究议题,也正因如此,研究者往往试图构建所谓民主化的“一般模式”。但是,“异常案例”的频频出现恰恰表明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矛盾。
如前所述,在先前的研究中,众多学者试图将民主化发生的“一般模式”限定在经济发展、精英推动、文化支撑或外力激发等因素的组合范围之内。按照这一逻辑,类似于博茨瓦纳等不具备以上条件的国家便与民主化无缘。虽然众多学者在民主化发生条件的研究中取得丰硕成果,也证明了诸多因素与民主化发生之间有较为明显的相关关系,但这并不代表两者之间存在明确的强因果关系。
第二,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出于理论构建的需要等因素,学者们总是刻意回避异常案例。多数学者在收集客观材料、构建相关关系的过程中,都具有较强的目的性,试图凸显自身理论与其他理论的区别,或是增强理论的自洽。因此,在理论构建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选择性偏差。比如,在许多民主化研究中,人口规模在百万以下的小国均被忽略不计。同时,民主化研究多数是基于民主化发生之后的经验材料与数据,研究者从中进行总结和抽象,进而完成理论的构建。甚至在许多研究中,民主化被论证成结构性因素累积到一定程度之后,必然会出现的结果。质言之,相当一部分的研究认为,民主化是基于结构性因素累积而机械发生的结果。这一逻辑常使民主化的相关研究陷入“二元论”的误区,即某一案例满足某些条件之后,就会发生民主化;或者某些国家缺少了相关条件,则无法建立民主制度或陷入民主崩溃。实际上,此类逻辑并不成立。
推崇结构论的民主化研究,大多数是根据既有结果,有偏好地选择相关案例,而后推导其中的因果关系。这一过程往往会人为忽略异常案例以及某些案例中的偶然因素。民主化的发生,实则更应该是一种概率式的结果。一国满足的结构性条件越多,则发生民主化的概率固然上升;但并不是缺少某些条件的国家完全无法发生民主化。由于某些偶然因素存在,民主化同样可能发生在结构论者并不看好的国家和地区。
第三,需要强调的是,在民主化发生的过程中,诸多相关因素发生作用时,并没有严格的先后顺序。将各个因素的作用顺序一一排列,实质上仍是夸大了结构性要素的作用。事实上,诸多要素很可能是同时发生作用,或是各因素相互影响,相互嵌入,共同促生民主化。民主要搞好,既涉及一套基于民主文本和宪法条款的制度安排,又涉及政治精英与主要政治力量的信念与行为,还涉及最初的民主实践能否常规化、惯例化与稳定化。
除理论意义外,关于民主化“异常案例”的研究还有丰富的实践意义。
首先,“异常案例”的存在,表明在政治实践过程中,民主化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而非孤立过程。一方面,民主化得以发生,并不是仅仅因为具备某一项或某些相互割裂的条件,而是诸多条件共同作用的系统过程;另一方面,民主化也并不是简单的制度移植,而是民主制度结合客观条件,逐步确立、巩固和运转的过程。民主是一种提倡竞争的制度安排,但竞争开放之前的政治整合更为重要。政治整合的缺失,很可能造成民主名义之下的恶性竞争和政治失序,甚至在后来导致民主的倒退与崩溃。在民主制度正式确立之前完成相当程度的政治整合则可避免相关问题的发生,增加民主巩固的成功率。
其次,对民主化的另一个误解是,民主化即意味着与旧制度彻底决裂。实际上,民主化对后发国家来说并不是一个制度断裂的过程,而是民主制度根据其国内客观环境、条件内生的过程。如上所述,与其他民主化失败的国家相比,博茨瓦纳的成功正是得益于制度妥协,即对传统权威的妥当处理。就非洲而言,博茨瓦纳是为数不多甚至是唯一一个避免了新旧制度冲突的国家。
最后,以上两点表明,西方的“民主输出”是一种无效的策略。应该说,民主制度到现在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的安排,更被欧美国家赋予了意识形态层面的含义。特别是美国,总是力图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推广民主制度。然而,美国的民主输出几乎完全忽略了其他国家的客观情况,而只进行简单制度移植。不仅如此,美国民主输出的手段往往是武力先行,因此美国的行径甚至是极端反民主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的“民主输出”是一种忽视先置政治整合的肤浅做法。
(本文原刊于《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第3期,原题:“‘异常民主政体’及其意义:以博茨瓦纳为例”。略去注释,正文有一定简化并由作者审定。经授权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