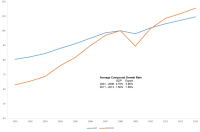——读阿莉·霍奇切尔德《本土的陌生人:美国右翼的愤怒与哀伤》[1]
2016年总统大选,美利坚国家以别样的“政治画风”呈现于世人面前,其突转之速、幅度之大,让许多观察家猝不及防,一时难以回过神来。无论在情感上还是理智上,许多人至今依然无法接受和面对。
在国人眼里,从来以开放包容、从容幽默、优雅得体见称的美国,如今却突然变得如此狭隘、焦虑、敏感。竞选语汇变得如此不堪,政客争权夺利手段也如此下作。而从大选折射出的美国政治状况看,华盛顿权势集团内部的基本政治共识已不复存在,其“症状”似乎确证了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此前对美国政治的系统诊断:统治集团日趋悬浮于社会诉求之外,不仅在利益上出现严重内卷,而且在话语和观念形态上与民众的日常感受发生严重脱节,建制政客沉醉于一整套梦幻般的“政治正确”语汇,下层民众在这套强大的权威体系中日趋感到无力且无助,整个社会弥漫着严重的受挫情绪以及因之而生的不满和怨怼;裙带主义日趋成为权势集团日常运转的基本潜规则,自由民主日趋寡头化;政客被财团势力裹挟,党争渐趋白热化,致使公共事务所必须的基本共识难以达成,导致美国政治陷入彼此掣肘、相互拆台的恶性循环;……思维僵化与权力僵局彼此颉颃,使得任何形式的改革举措变得举步惟艰,民主政治开始陷入了一种“功能失调性的政治均衡”(dysfunctional political equilibrium)。民主制(democracy)俨然沦落为“否决制”(vetocracy)。[2]
面对特朗普的当选,美国主流建制精英哀鸿遍野,万马齐喑,甚至痛心疾首,那些一直被学院派视为理所当然的诸如美国对世界人民的无限责任、无国界式的普遍人权、开放包容等等价值准则遭遇空前挑战,于是诸如“黑天鹅事件”、“反全球化”、“暴民政治”、“民粹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大而化之的所谓分析评论此起彼伏。尽管诸如此类莫名其妙的一概而论充满意识形态评断,且本身混淆视听、不知所云,仍然无法消解美国学院派和主流媒体专栏作家们的兴趣,而中国许多深受这套观念形态陶冶的人士也竞相效尤。可见,在对美国政治和社会现实的感知上,中国主流知识界与美国同行可谓同病相怜,一样麻木不仁。
事实却是,“特朗普现象”绝非“特朗普的现象”,它毋宁是美国社会状况以及政治处境的折射,是观察并理解新世纪美国政治社会的“窗口”。不是强行使现实适应我们脑海中已有的观念,而是依据现实不断修正我们的概念框架,传统的政治知识需要重新检省,从新厘定,有的甚至不得不毅然抛弃。对于中国人来说,与其做大而化之的观念评断,不如对其背后具体的动力机制做具体而微的事实分析,只有这样,庶几可以作为理解问题、反思自身的“借镜”。
美国社会学家阿莉·霍奇切尔德近著《本土的陌生人:美国右翼的愤怒与哀伤》可谓适逢其时,它为我们提供了上述努力的契机。霍奇切尔德荣休前长期担任伯克利大学社会学教授,作者坦承自己在政治立场上属于自由派左翼阵营,但她写作时努力悬置自己的政见立场,进入右翼美国人社区,倾听他们的声音,观察他们的现实处境,理解他们的政治情绪。作者深入被认为是“右翼堡垒”的路易斯安那州,历经五年的深入调研,积累了4690页的采访笔录,以大的问题关怀为起点,同时在实地观察采访中不断提炼具体问题,并循着新的问题线索决定调研方向和侧重点,借以理解研究对象的现实感受和所思所想,洞察右翼人群政治立场背后的社会和精神根源。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研究者时刻保持换位思考的能力,揭示研究对象的“深层叙事”(deep story):即“感受性叙事”(feel-as-if story),通过一套象征性语汇讲述故事,这种叙事“移除了事实,转而讲述人们对事实的感受。这样的叙事吁请身处政治光谱两极的人们先各自后退一步,努力发现对方用以观察世界的‘主观棱镜’(subjective prism)。”[3]作者文笔极具画面感,不仅对美国保守派右翼人群的“深层叙事”做了深入揭示和剖析,而且在社会研究理论方面也具有极强的启发意义。
一、“移情障碍”与美利坚人政见的极端化
进入新世纪,美国社会日趋陷入分裂状态,左右阵营在观念和意识形态上越来越势不两立:在左翼人士眼里,共和党与福克斯新闻网一根筋地反对联邦政府,敌视一切旨在解贫济困的联邦福利政策,俨然成为那些仅占1%的权贵寡头集团的代言人;而在右翼人士看来,政府本身沦为自成一体的权势集团,以各种虚假的名义不断强化政府控制,政客也不惜挥霍纳税人的血汗钱为自己捞取选票。这种分歧本身或许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分歧双方非但缺乏理解对方修正自己刻板印象甚至偏见的任何意愿,反而在自己业已熟悉的阵营内部不断强化已有的政治偏见,一道无形的“移情隔离墙”(empathy walls)使得任何形式的沟通理解进而达成共识成为不可能。与有形的隔离墙不同,这种“移情隔离墙”毋宁是一种深入理解他人的障碍,它使我们对那些有着不同信仰和成长环境的人们无动于衷,甚至充满敌意,我们倾向于对新获得的信息任意筛选并强塞进我们固有的思维框架,我们习惯于从外部认识相对阵营的人们,致使我们获得的信息越多,见识反而越偏狭,立场也愈加偏执。为此,霍奇切尔德一开篇便提出了如下发人深省的问题:“在保持我们信念的同时,是否可能从内部认识他者,透过他们的视角观察现实,理解生活、情感与政治之间的关联,从而跨越移情隔离墙?”[4]而正是这道隔离墙的存在,使得隔离墙两边的人们无法进行头脑清明的分析,形成开明的见解和主张。
如何帮助人们克服他们心中自觉不自觉间形成的那道无形的“移情隔离墙”?正是以科学研究为职志的学者的重要使命。
二、“大谜团”:美国右翼的政治情绪
2016年美国大选地图显示,支持特朗普的“红”州比支持民主党的“蓝”州平均生活水平低下:未婚先孕、离婚率居高不下、高肥胖率、非正常死亡、新生儿畸形率以及低入学率等等。据统计,美国“红”州人口的平均寿命要比“蓝”州小五岁。在美国五十个州中,在“人类发展”(其中包括:平均寿命、入学率、受教育程度以及个人平均收入)方面,路易斯安那位列第四十九位,而该州人口总体健康水平排在倒数第一。工业污染问题在“红”州要严重得多。据美国癌症协会统计,路易斯安那男性癌症发病率高居全国第二,癌症死亡率位居全国第五。
对于象路易斯安那这样的贫困州的人们来说,想必他们更加期待联邦政府的介入和扶持。事实却恰恰相反,这里的人们对诸如EPA(环境保护局)这样的联邦政府机构持普遍的怀疑甚至敌视态度,这与一般广为接受的“经济人”或“理性人”预设背道而驰。事实却是:路易斯安那州有44%的公共预算来自联邦政府资助。而这正是本书作者试图解开的“大谜团”(great paradox):即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与相关区域人们对政府治理污染举措的抵制同时并存。对此,霍奇切尔德发现,以往的相关分析往往忽视了一个关键因素,即政治中的情感因素,它决定着人们对某些政治议题是否给予关注以及关注的程度,决定着他们对特定政治主张是否和在多大程度上产生共鸣。同性婚姻、少数族群、叙利亚难民、非洲饥荒……诸如此类的议题或许足以使自由派人士心潮澎湃,义愤填膺,但对持保守立场的右翼人士来说却毫无共感,他们关注更多的则是自己所居住的社区、宗教信仰、工作机会、税负、持枪权等等。
李·谢尔曼(Lee Sherman),82岁,曾在位于查尔斯湖滨的匹兹堡平板玻璃厂(PPG)工作,该玻璃厂长期向湖中倾泻工业污水,致使湖中鱼类遭到严重污染而无法食用。为此,政府不得不发布湖中水产品食用安全预警,湖区渔民为此蒙受重大损失。而谢尔曼本人正是该工厂向湖中非法倾泻污染物的目击者和参与者,他本人后来由于揭露该工厂的不法行为而遭到解雇。然而,玻璃厂的劣迹本身并未促使谢尔曼转向支持联邦政府,事实却是,从2009年开始,谢尔曼本人即成为“茶党”的积极支持者,而茶党主张取消一切政府的产业政策限制,要求取消“环保局”(EPA)。作者发现,茶党支持者们对联邦政府的敌意来源有三:他们认为政府的干预使地方教会的影响力遭到削弱,继而导致宗教信仰的影响力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趋边缘化;在他们眼里,不断攀高的政府税收,联邦政府用从纳税人口袋里取得的金钱,不但养活了一批整天价无所事事的政府冗员,而且滥施慷慨,造就了一大批游手好闲、坐吃山空的福利倚赖者。非但如此,这种建立在高税收基础上且在道德上看似正当的福利举措,直接危及着美利坚人根深蒂固的属于中产阶级的生存伦理,即通过个人艰苦奋斗实现自我价值的尊严感。长期以来,正是这种生存伦理构成了“美国梦”的基石,它意味着诚实劳动、虔信上帝,遵守规则,倡导正当得利,拒斥不当得利。在右翼保守人士看来,自由派倡导的那些所谓社会运动(诸如“平权运动”、“女权运动”、女性堕胎权、同性婚姻权)制造了一大批无视上述生存伦理的“插队者”,他们的道德底线模糊且随机应变,投机取巧,甚至巧言令色。采访中一位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发出如下抱怨:“或许由于不怎么经常上教堂礼拜,致使他们(自由派)轻忽个人道德。……美国梦本身变得不伦不类、毫无虔敬之心、物欲横流且斯文扫地。”[5]
由此看来,2009年以降感召力日增的“茶党运动”,与其说是一场经济政治领域的政策反动,还不如说是一场旨在捍卫作为“美国梦”基本支撑的一整套中产阶级生存伦理的文化运动。
三、“若有所失”与保守派的“乡愁”
在与大多数访谈对象接触过程中,霍奇切尔德发现,在右翼保守派人士心灵深处,都有一种难以名状的“若有所失”感。这种失落感之所以难以名状,因为它首先不是具体物品的损失,而是某种抽象物即某些价值的失落。对右翼保守派人士来说,这些价值尽管抽象却与他们作为“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清教徒”的生存核心息息相关,是他们作为“美利坚人”的根基所在,尊严所系。
在保守派看来,自由派的那套“政治正确”的道德泡沫正在对美利坚本身进行道德绑架和道德审判。教育系统里甚嚣尘上的所谓“文化多元主义”教条,正在消解美利坚文化的精神内核:在越来越多的自由左翼学者笔下,美利坚人的建国史被解释成一部针对印第安人、黑人等少数族裔的“犯罪史”,作为美利坚国家正当性根基的“民族同化”、“大熔炉”,在他们眼里却成为政治强制、民族迫害的代名词。在这套堂皇的“政治正确”话语的道德裹胁之下,只要你不对黑人、同性恋婚姻、叙利亚难民、非洲饥荒表现出同情并给予帮助,那你马上会被认为在道德上有问题;当你通过勤奋工作以期赢得机会的时候,当你遵守规则耐心排队的时候,那些“政治正确警察”(PC Police)却通过联邦政府出台一系列所谓“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促使那些后来者(移民、少数族裔、女性)随心所欲地“插队”。非但如此,“插队者”对自己的违背公平之举非但没有丝毫歉疚,反而心安理得,认为自己后来先到得理所应当,仅仅凭借自己的所谓特殊“身份”:女性、移民、难民、黑人、同性恋者……更有甚者,只要你对他们的上述做法表现出些许不满或质疑,他们便会立即义愤填膺,颐指气使,甚至暴跳如雷,立即在道德上将你指责为“性别歧视”、“种族主义”、“排外主义”、“恐同症”……如果说当初容忍后来者“插队”实出于的美利坚人的慷慨和礼让,但这种礼让换来的不是“插队者”的困疚和感激,而是他们的得寸进尺,甚至贪得无餍。美利坚人的慷慨在那些因此获益的人们的眼里被视为美利坚人应尽的义务。这不能不在保守派人士内心深处激发起强烈的不公平感甚至愤怒和怨恨:非但那些按理本该属于他们的机会被剥夺,更威胁到他们作为美利坚人的尊严本身,他们曾经引以为豪的中产阶级生存伦理不断遭受挤压,他们精神上的安全感正在丧失。
与这种“若有所失”感伴随的是右翼保守派人士内心深处的难以名状的恐惧感,而与这种恐惧感彼此颉颃的是一种莫名的文化上的“乡愁”(nostalgia),该词源出希腊语,词根nostros的意思是“回家”,而algia的意思是“渴望”。对右翼人士来说,他们作为美利坚人的尊严和地位不仅正在式微,而且那本该属于他们的“文化故乡”正在与他们渐行渐远,即便他们依然生活在美利坚这块土地上,不仅在种族人口上日益沦为少数人群,如今他们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是这块土地的主人,俨然一批“本土的陌生人”。更有甚者,他们发现自己正在被那些善于“插队”的后来者污名化为“没有同情心”、“冷漠”甚至道德上低劣的“红脖子”。这公平吗?
令保守派深感忧虑的是,奥巴马,这位本身凭借自己的特殊的种族身份通过“插队”在美国获得晋身的总统,正在将美利坚国家从真正的美利坚人那里夺走。作为出身于低收入单亲家庭的黑白混血儿,奥巴马最终逆袭为世界上头号强国的总统,这在自由左翼人士眼里被他们交口称赞为所谓美国梦。然而在保守派看来,这恰恰是奥巴马夫妇利用自己的所谓特殊“身份”违背公平原则通过“插队”获得的不当得利。当初的“插队者”正在通过各种手段使“插队”成为常态,成为不言自明的制度化规则。对此,难道“真正的美利坚人”忍心袖手旁观,听之任之?
“U.S.A”,这一特朗普在其竞选造势集会上经常使用的政治口号,之所以能够得到热烈响应,恰恰在于它契合了右翼选民的上述带有“乡愁”情绪的恐惧感。作为一位“情绪型的候选人”(emotions candidate),特朗普所表达的正是他们内心深处蓄积已久的不满和愤怒。正是特朗普使他们找回了久违的作为美利坚人的道德优越感和人格尊严,也只有特朗普这样的“体制外富豪”,而不是华盛顿那帮患得患失、畏首畏尾的建制政客,才有勇气和魄力带领他们戳穿自由派的那套冠冕堂皇的“政治正确”谎言。而特朗普的竞选口号“复兴美国”(Make America Great again)之所以如此具有感召力,在于它不仅承载着显见的经济和政治诉求,更隐含着右翼人士渴望已久的文化和道德使命。
四、结语:濒临破碎的“美国梦”与“特朗普时代”的来临
《本土的陌生人》为我们呈现了美国社会矛盾的诸多细部,这些矛盾不仅表现在社会结构方面,更与人们对这些矛盾的精神感知有关。“特朗普现象”并非特朗普本人制造的“现象”,它毋宁是新世纪美利坚人精神焦虑的反映。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领域,全球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都对一切文化秩序提出了空前严峻的挑战,诸如资本的无节制扩张及其对权力的绑架(如2008年金融危机),日见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文化均质化,等等。在美国,资本的迅速膨胀已经远远溢出了传统新教伦理所能接纳的范围,在资本面前,“我们”与“他们”、“本土”与“外邦”的界线模糊难辨,其在种族文化上的挑战不亚于政治经济领域的挑战。特朗普的当选无疑是对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后果的反拨。作为旁观者,我们不难从中感受到美利坚人无限的悲情和无奈。正如特朗普的一位坚定的支持者所说:“这个国家需要有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将其拉回正轨。”[6]
作为总统的特朗普注定要面对一个四分五裂的美国。如果经济政治上的分裂可以通过有效的政策举措得到敉平,那么文化价值上的分裂则很难在短期内找到有效的解救之道。如何使处在政治意识形态两极的人们能够跨越“移情隔离墙”,倾听对方,摆脱偏见,彼此合作?正是霍奇切尔德写作《本土的陌生人》一书的核心关切,也是“特朗普时代”美利坚国家能否“重回正轨”的关键。
最后,我们不妨摘引作者在书末拟写给左翼人士(包括作者自己)的一封信,对自由派左翼人士,霍奇切尔德这样写道:
“为什么不去了解一下那些处于你们一手制造的‘政治泡沫’之外的人们?先放下安·兰德(Ayn Rand,美国小说家哲学家,代表作《阿特拉斯耸耸肩》);他们是兰德的拥趸,但你们会发现他们并非如兰德的文字给人的印象那样自私。你们或许会发现他们许多人其实很善良,你们会从他们身上学到诸如社群团契、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等诸多品质。你们或许认定那些强大的右翼力量组织者出于自利,通过诉诸右翼支持者人性中的‘邪恶天使’(诸如自私、种族不宽容、恐同症以及逃避那些旨在帮助不幸者的税负的渴望),‘挟制’右翼草根人群。在新奥尔良举行的特朗普竞选造势集会上,上述现象的确不难看到。但它却遮蔽了他们的另一面,即右翼人士作为人的本性中的‘善良天使’:他们即便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依然表现出的遵守规则的耐心,他们的忠诚、奉献和坚韧。诸如此类的品质构成了他们‘深层叙事’的一部分。若能设身处地换位思考,你们或许能够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7]
美国右翼的愤怒与哀伤,困扰的或许不仅仅是美国右翼人士,甚至也不仅仅是美国自身。今天它发生在美利坚,明天或许就会发生在其他国家,甚或正在以不同的“剧情”在其他国家排演。在新世纪,美利坚能否在愤怒与哀伤中找到自我疗救的可能?从而修复濒临破碎的“美国梦”,重树国家的精神和制度根基?美利坚国家的未来将何去何从?这不仅与美利坚人自己有关,更与新世纪人类文明的进程息息相关。对此,我们在隔岸观火,作壁上观的同时,能否有某种程度理智上同情的理解?
注释:
[1]Arlie Russell Hochschild,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Anger and Mourning on the American Right.The New Press,New York,2016.
[2]Francis Fukuyama,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11.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14.中译可参广西师范大学译本。
[3]第135页。
[4]第5页。
[5]第158页。
[6]第228页。
[7]第233-2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