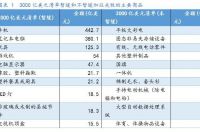一、当代全球化潮流的原本的内在矛盾和冲突
世界政治中的矛盾和冲突并未像一些自由国际主义理论观点所示的那样,由于全球化的急剧进展而迅趋衰减或消退,反而几乎充斥着全球化进程。摩擦、紧张、对立和冲撞不仅很显著地广泛存在于传统的国家间权势关系中,也同样存在于非传统的全球性稠密交往和互相依赖构造中,而且正是由当代全球性国际 / 跨国交往和互相依赖的大发展引发或加剧这后一大类情景。它们概括起来主要有四大类:互相依赖政治包含的矛盾和竞争、全球化进程中的弱势者的不满和争、全球化对落后社会的冲击和分解效应所造成的痛苦和冲突、由于愈益稠密的国际 / 跨国交往而改换了形式或者加剧了的传统国家间斗争。
在一些满怀自由主义幻想的国际关系学者、特别是这样的国际经济学家那里,互相依赖被设想为纯粹的“双赢”或“共赢”关系,即由于互相依赖,每一方都得利,而且只是得利。这种理念的潜在前提,是从亚当 • 斯密和启蒙学派开始迅速形成并绵延不绝的一项根本信条,即市场经济天然地和谐、公平和普惠,自由的商业意味着完好的社会和普遍的国际和睦。由此出发,互相依赖往往甚至多半是不对称的这一点就被漠视了,它们产生的利得在分配上的不均衡(连同产生利得所需代价的不均衡)也一样被忽略了。实际上就抹煞了互相依赖引起的“政治”问题 —— “相对利得”(relative gains)的分配以及各方在交往中就相对地位所进行的竞争或冲突。互相依赖的许多关键问题是围绕着那个传统的政治问题的,那就是“谁得到什么”,或曰“谁得到多少”。不仅如此,在这样的问题上,交往各方的行为本质上服从于一方的所得必是他方的所失这一规律。因而,在非政治领域的互相依赖关系中,几乎总是存在广义的政治斗争,看不到这一点就看不到互相依赖的政治方面,也就不了解互相依赖政治。
当今,全球化进程中最引人注意的矛盾和冲突,概括地说是强势者与弱势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强势者包括拥有或享有以下优势的所有角色:在技术、资本规模、产业和商业运作效率、人才资源等方面居于有利和有力地位,同时还能得到维持和加强此等经济性力量的、相对优越的政治、社会、教育、文化乃至军事性因素的襄助,不管这些襄助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是国内的还是国际或跨国的。这样的强势者显然主要有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以这些国家为主要基地的跨国公司,上述两者内部参与主导、积极投入或至少比较适应经济全球化并能够从中大获其利的经济部门或单位。与此相对,弱势者主要是广大欠发达国家,连同发达国家内那些不能适应技术发展和世界市场变化、从而迅趋衰落的经济部门和单位。当然,在强势者中间也有着相对的弱势者和强弱竞争问题,犹如在弱势者中间存在着同样的区分和竞争一样,何况强弱之分还随所涉竞争领域的不同而有变化。因此,这里所说的矛盾和冲突就其全景而论是异常错综复杂的,当今世界政治格外庞杂和往往令人困惑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此。然而,技术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步伐是那么迅速,由此而来的扶强抑弱、优胜劣汰效应又是那么剧烈,以致其中强者与弱者间的分野、矛盾和冲突显而易见。
其中,特别具有世界大局意义的是一个全球化进程与生俱来的老问题,即发达世界与欠发达世界之间在经济、技术发展程度和生活水平方面的鸿沟。但现在与 20 年前不同的是,欠发达世界的技术落后、世界市场劣势和金融劣势已变得更为严重,在这些领域它们对发达世界的依附也因此加大。不仅如此,在信息技术革命条件下资本跨国流动规模和速度急剧增长也加剧了这一情况,使得欠发达国家的处境更为不利。这就是全球市场固有的不稳定性。
与此相比,当今有一类弱势者的不满(特别是对经济全球化急速发展的不满)表现得明确得多,也显著得多。它们来自各国国内,特别是发达国家内那些很不适应世界市场竞争及其对新技术、新产业结构和新经营方式的要求的经济部门和单位。由于它们通过种种渠道对国家政策施加影响,也由于政府对维持国民支持、社会安定乃至经济和战略意义上国家安全的关切,导致多半旨在保护这些部门或单位的不同程度的“新重商主义”构成了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一个重大现象。这类对外经济政策用关税以外的种种手段保护就业、生产和国内市场,并且人为地刺激出口,争取尽可能大的世界市场占有率和贸易盈余,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称作是这些弱势者同经济全球化作斗争的武器。
全球化进程中的弱势者还包括其余各色各样在利益、信念或情感等方面受到严重冲击并且颇感无助的社会阶层、集团和个人。他们的不满和愤怒由西方发达国家的各种“反全球主义者”表达出来,引人注目。他们不仅强烈不满全球化的某些经济效应,而且强烈不满其生态、文化和社会效应,甚至整个“现代性”(modernity)也在其抨击之列。总之,加速中的全球化进程也在加速“繁殖”其不满者和反对者。不用说,全球化潮流中世界政治的内在矛盾还包括被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思想当作其绝大部分、或唯一决定性内涵的传统的国家间斗争。这里要提到的,只是它们由于愈益稠密的国际和跨国交往而改换的形式或者有时被加剧的某几个方面。
作为全球化的根本表现和根本媒介的这种交往,无疑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增进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社会之间的了解。但由于国家政府和种种社会政治势力往往意欲并且能够施加阻滞和扭曲性影响,再加上民族社会之间的了解存在必不可免的固有限制和片面性,导致这种了解根本不可能达到完全或近乎完全。不仅如此,国家间的互相了解、互相依赖以及对这互相依赖的知晓,并不产生国家间的共同价值观念,也许甚至不产生或不一定产生共同利益感。一个高度整合因而甚少冲突的国际社会,并非需要国家和民族社会互相间有稠密的交往,更重要的是它们要有足够广泛和深厚的共同利益感和共同价值观念,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多种有效的国际共同规则和共同运作体制。正是在全球性交往和互相依赖急速发展的当今时期,发生了大多由美国或美国伙同其若干西方盟国发动的多次国际干涉(联合国的干涉除外),其频繁程度不亚于先前。不仅如此,倘若考虑到上述国际干涉通常兼有“民主化”和“国际法制化”动机,而这些价值观念的上扬又同全球化不无重要关系,那就可以说,全球化是在一个重要方面以新的形式继续甚或加剧了传统的国家间斗争。
在全球化和互相依赖愈益发展的世界,国家间在军事安全领域之外的“位子竞争”(positional competition) 大概在世界政治中占有中心或近乎中心的地位。这类竞争是国家间特别是强国间,就争取经济资源、市场份额、技术优势、威望和政治影响等“位子价值”进行的斗争。按照这套论断的提出者兰德尔 • 施韦勒尔的看法,在理论上和大多数现实环境中,安全是双赢或多赢性质的,而生性不足的“位子价值”是单赢性质的:安全“既可以共同向往,也可以共同分享,而不减少任何一个行为者对它的享有”,位子价值却非如此,例如“倘若每个国家都有(显赫)地位,那就没有哪个国家是如此”。很明显,“位子竞争”乃是多少改换了形式的传统国际斗争,而世界经济和技术越随全球化的发展而成长,这类竞争就有可能越突出甚至越尖锐。
有必要强调一下“1914 年的教训”。第一次世界大战显示,大国间全面战争的爆发可以同它们之间的经济(甚而相当大程度上连同文化)互相依赖看似矛盾地并存。问题在于,“政治冲动可以比经济需要更为有力”,何况往往还有对立的民族情绪、民族主义和其他意识形态理念等一向强劲的力量与这“政治冲动”一齐起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三年,一位德国著作家颇为与众不同地写道: “世界比先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是一个大整体,在其中一切都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但一切也都互相碰撞,互相冲突。”可以认为,撇开其中修辞性的夸张,这句哲理似的断言多少也适用于全球化潮流中的当今和未来世界。
二、当前的变更倾向与全球治理难题
在世界范围广泛流行或共生的跨国价值取向可以称为“全球政治文化”。当前,全球政治文化正在颇为显著甚至急剧地朝本土主义 — 民粹主义 — 民族主义方向变更。不仅如此,与冷战结束以前任何时候相比,国际地缘政治中的大国基本关系可谓强烈动荡,其主要内涵是中美两国间的战略竞争迅速加剧,俄罗斯与美欧强烈对抗,中俄两国间的战略协作则作为这两大事态的一个结果而大为提升。在如此的基本生态中,全球治理规则在一系列功能领域的形成、调整和贯彻面临空前的困难。
与流行了许多年的乐观的自由国际主义时代观和世界观相悖,也与治理全球性、区域性国际共同问题和跨国问题的紧迫需要相悖的是,在当今时期,总的来说,多边机制呆滞和低效,多边合作前景相对黯淡或渺茫。无论要治理的问题是对世界经济衰退威胁、谋求国际金融体制改革或完成多哈贸易谈判,还是海洋争端和海上行为对立、防止核武器扩散、涌向欧洲的中东西亚难民大潮、“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战争或所谓“保护责任”即干预或干涉主义,“全球治理”前景较为暗淡。众所周知,就这些问题而言的全球治理规则的形成、调整和贯彻,难上加难。罕见的重大例外是 2013 年后取得重大进展的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事业,那是依凭中国的巨大奉献和中美两大首要排放国之间的有效协商和协调;七国长时间艰难协商而实现的伊朗核协议也是如此,中国的贡献亦非同小可。然而,现在这两个方面的基本情势由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退出都在发生重大的负面变化。
除了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甚为严重之外,全球治理前景较为暗淡的基本原因有四个:诸多大国利益严厉限制、某些关键性小国“顽固不群”、所涉的广义和狭义的技术问题异常复杂而且新颖、 “全球政治文化”的变更倾向。有讽刺意义的是,尽管有历时多年的多边主义国际合作理论思想滥觞和舆论流行,但目前世界性国际和平和安全领域内唯一屡有真实的定夺权威和下令权能的,仍只是 1946 年设立的联合国安理会!其实,所有这些都属于适逢“艰难时节”的正常情况:恰在这更需要国际广泛合作和多边体制的时候,往往自顾自保优先,合作意愿减退,义务分配困难,体制创建维艰,或已有体制低效。应然往往远异于实然,当今国际“集体行动”的困难远甚于自由国际主义理论学说在先前“较好时节”所料,其时至少世界经济状况良好得多,同时权势格局变动也窄小得多。
全球政治文化正在颇为显著甚至急剧地发生变更,倾向本土主义 — 民粹主义 — 民族主义方向。事实上,在特朗普 2016 年 11 月选胜以前,人们就可以相当强烈地感觉到某种意义上的“变天”趋向。美国特朗普准孤立主义、单边主义潮流的强劲凸显,英国经全民公投产生的令人意外的脱欧决定,比冷战后头二十年远为广泛和频发的经济保护主义,欧洲国家愈益高涨的反穆斯林移民潮舆论和欧洲极右翼运动的更大的势头等,都表现了这一趋向。不仅如此,俄罗斯普京咄咄逼人但颇得国内民心的与西方在战略和军事上的激烈对抗,土耳其埃尔多安政权民粹主义的伊斯兰化举措和急剧集权趋势,在台湾地区台独政党经普选大胜而执政的大众政治大变动,在香港地区的港独逆流,甚或中国大陆的部分显要舆论等,都显示本土主义 — 民粹主义 — 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的风行倾向。这与世界的广泛和深刻的经济、社会、技术、文化和地缘政治动能密切相关。
这类“全球政治文化”的变更倾向应当说是全球范围国际秩序动荡和“裂变”的重要动能和表现,多边机制的总的呆滞和低效在其中就更可理解了。在这样的基本情况下,中国一方面仍要努力在推进全球和区域的多边合作方面起更重大的作用,但另一方面需要广泛和深入地考察全球逆动倾向,认识到中国一国不是足够的全球化国际秩序(或至少自由、开放的全球贸易秩序)稳定器和顶梁柱,甚或还要有一定的“无力回天”的思想准备和政策准备。
自冷战结束前后至今大部分时间里为世人所熟悉的世界已经大致结束,或者至少正在结束。对于中国来说,一个在显著变弱和失序中的美国和西方必然给出非同小可的战略和外交机会,但也将会在中国自身经济和金融相对为难的时候严重地加剧这一困难;另外,美国和西方的变弱和失序可能使得中国中长期在对外战略政策上更加大为发力,大作进取,战略审慎减少。较具体地说,特朗普的战略安全政策和外交政策可能给中国提供一些可以利用的机会(尽管已经证明这些机会比中国许多人预料的小,并且可能包含上面提示的风险),但是这与他对中美经济金融关系造成的伤害相比是第二位的,因为中国现在面临的首要挑战就在经济金融方面,而中美经济金融关系对中国经济金融意义重大。
三、重大和深刻变化中的应对战略
当前,中国在外部世界面对的一大基本形势是对手美国已经或至少正在针对中国动员起来,而且近乎全面动员。也就是说,中美关系形势巨变不仅在贸易阵线上,也在战略阵线、政治阵线和意识形态阵线上。2018 年初起,中美各类基本矛盾全面严重加剧,中美关系急剧地进入 1972年中美冷战结束以来最紧张的状态,虽然仍有难以较早预料的阶段性或情势性的上下波动。中国以及俄罗斯被特朗普政府正式宣告为美国短期、中期和长期的主要对手。入主白宫后两年后,特朗普对增进美国在印太区域的权势大有作为。特朗普签署《台湾旅行法》和与台湾密切相关的《亚洲再保证倡议法》,其政府显著增进与台湾的公开和秘密的军事合作,急剧强化对台湾的外交支持。美国海军战斗舰只穿经台湾海峡的频率近来急剧增大,旨在就台湾问题对中国作直接的军事威慑。美国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已变得比奥巴马政府时期频繁得多、剧烈得多。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2019 年 3 月 1 日更在马尼拉宣布美国将依据1951 年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用美国武力抵御中国对菲律宾部队、飞机和公共舰船的攻击,这被认为是“华盛顿最严峻的警告,针对中国对这战略性水域大部分权利的声明”。“对许多分析家来说,蓬佩奥的声明显然是特朗普行政当局已着手在印太区域‘加强我们的同盟承诺’的最重要行动。”主要针对中国的美日澳印四国印太战略联盟正在构建。
不仅如此,“掠夺”已成为美国抨击中国在发展中世界的经济活动的标准用辞。美国政府新近正式开始在这方面对抗和阻滞中国。特朗普行政当局已大力发动美国战略武力全系列的技术更新和升级,大大加剧至少在西太平洋的对华军备竞争。美国宣布退出冷战末期与前苏联缔结、且在苏联瓦解后继续与俄罗斯联邦履行的中程弹道导弹条约,其主要目的可认为是针对中国对美战略威慑的两大支柱之一 —— 数以千计的陆基中程导弹。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抨击骤然重回中美关系舞台,并且添上对所谓中国大规模干预美国政治选举、政治体制和社会舆论等的激烈指责。美国还对中国高技术贸易和发展施加几近于封锁的空前广泛和严厉的限制,彰显对华贸易战或贸易对抗的真正战略性质。不仅如此,美国朝野对中国政治体制、国内治理方式和对外信息传播的攻击可谓甚嚣尘上。
对于美国正针对中国动员起来的基本形势,中国今后一段时期的紧迫和较持久的任务是依据有张有驰、 “进两步退一步”的常理,用五六年或更长些的时间去实施新形态的“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即大幅度的战略态势收缩和经贸调整奋进,后者以加深、拓宽和加速经济体制改革为基本条件。如此实践的战略目的是争取在相当程度上使美国回到动员以前的较松垮状况,然后中国再谋求新的对外显著进取。
2018 年初以来,加剧变更的世界政治经济隐约地透露出一种危险的“两分”可能性:一方面,美国政府趋于经双边谈判显著缓解与其他发达经济体及其紧密伙伴的经贸矛盾,进而愈益可能与它们分别达成自由贸易或准自由贸易安排,谋求无论以何种方式单边废弃全球性 WTO 体制以后,成功地与之一起构建新的经贸规则体制,范围大致只涵盖发达世界及其紧密伙伴;另一方面,中美之间所有各类基本矛盾严重加剧,连同美国政府施行这种“集团经贸”方针,可能迫使中国少有选择,只能越来越依靠与友好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中的“一带一路”合作国家)从事主要的对外经贸活动。显而易见,总的来说,此类经贸活动对中国和合作伙伴的利润前景相当有限,中国资金将低回报地大量外流,而且与在发展中世界颇为急速的、非常广泛深入的介入相伴的是各类有关纠葛和风险显著增加,这不会给中国带来关键裨益,即大大促进自身系列广泛的技术更新和升级。
因此,中国必须尽最大努力争取减小甚至杜绝世界经济“两分”的可能性。如果从这样的视野看,尽可能最大程度的经久维持和改善中欧、中日、中韩、中澳、中加等双边关系,支持“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有选择的区域或次区域多边经贸合作体制,无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就此而言,谈论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的“重中之重”、因而须优先以对美妥协去争取搞稳搞好对美关系乃偏颇甚或谬误之论。如果像事实上已经或至少正在成为的那样,美国是中国的短期、中期和长期首要对手,那么合乎逻辑和战略常理的推论应当很显然,即要优先争取搞稳搞好与美国以外的发达国家和中国周边国家的关系,以利对付美国这克劳塞维茨式“引力中心”。否则,中国将在客观上间接地显著强化美国的对华战略地位和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