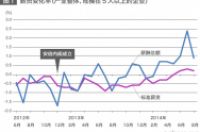引子
政治裂隙(Political Cleavages)是世界政治的主要特征之一。在全球化时代,政治裂隙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内部日益严峻的政治极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发展差异愈发扩大。在美欧等发达国家内部,保守主义孤立主义兴盛、社会团结被撕裂、民粹主义蔓延。在国际层面,美国在动摇现有的国际机制和国际秩序,发展中国家反而成为维护全球自由贸易的中坚力量。全球价值链重构了全球产业结构,导致美欧等发达国家内部制造业空心化,民主体制已经无法支撑产业结构的变化,这是发达国家内部政治裂隙的主要原因。虽然许多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分工体系并受益于全球化,但也被锚定在中低端产业结构中。国际关系已经超越了地缘政治和传统安全领域,对发达国家最主要的威胁来自部分发展中国家在产业结构中的快速攀升。发达国家通过控制全球价值链,抽掉攀升的梯子、堵塞攀升的通道,对新兴国家实施打压,将成为国际关系的常态。
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雇美国人,买美国货”“美国优先”等原则成为其内政外交的重点。在美国国内,两党纷争、意识形态冲突和极端民粹主义撕裂着社会的团结。在国际层面,特朗普政府对传统盟友或战略竞争者挑起了不同程度的经贸冲突;通过“长臂管辖”打压外国公司、逼迫企业和他国政府选边站。在欧洲,英国脱欧、法国“黄马甲”运动、难民危机、恐怖主义等,也成为逆全球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诸如传染病、气候变化、非法移民、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进一步为反全球化支持者提供借口。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国家建构、社会经济发展等问题依然存在,但西方国家出现的政治裂隙(Political Cleavages)对国际秩序产生更加深远影响。
冷战结束后,“全球化”成为世界共识,并推动了世界经济不断繁荣;信息技术革命,通过虚拟世界重构了全球关系。冷战结束的最终标志并非是苏联、东欧的政治体制解体和华沙条约组织的终结,而是苏联集团融入西方资本主义的贸易和产业分工体系,因此福山“历史终结论”成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政治注脚。新自由主义强调减少政府干预、实现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自由化,“华盛顿共识”成为发展中国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意识形态支柱。全球化在全球资本快速流动和区域经济高度融合两个层次同时展开。在全球层次,跨国公司成为全球化的重要行为体,助推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形成;在区域层次,地理毗邻国家间的金融、贸易、人员快速流动与融合,有效地实现了新自由主义关于释放市场力量的主张。
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全球化,资本呈现双向流动:金融资本流向了美国、欧洲,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帝国成为金融资本边际收益率最高的区域;制造业资本则流向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具有丰富廉价劳动力、强烈的经济发展政策驱动力等特点,因而发展中国家愿意吸引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中国家需要主动融入西方发达国家建立的国际机制中,成为全球价值链的组成部分,进而实现经济腾飞与发展。新自由主义主张的贸易投资自由化重塑了全球产业结构,形成了复杂的全球分工体系和全球价值链。
跨国企业战略、全球劳动力市场细分、全球供应链和生产体系共同构成了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超过三分之二的国际贸易是通过全球价值链进行的。全球价值链打破了传统贸易生产和交换的界限,一项产品从研发、零部件生产到装配终端产品的整个过程,是在多个国家和区域完成的。每个国家或区域,只须关注生产体系中的某项环节,无须生产完整的最终产品。全球价值链让国际贸易统计数据变得极为复杂。传统货物贸易只需要一次性计算最终产品的出口和进口,而价值链贸易是无法用净进口或者净出口方式进行计算,因为加工产品在供应链中向上移动时跨越国界。科技含量越高的产品,全球价值链越复杂。
全球价值链可以从产业类型等级、生产区域、核心网络三个维度划分。首先,按照产业类型等级,全球产价值链可以分为技术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基础产业。这是一种金字塔式的垂直结构,发达国家的产业主要集中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即全球价值链的顶端;发展中国家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即全球价值链的底端。产业类型是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最主要的标准,价值链越顶端,国家数量越少。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的过程,就是从价值链底端向顶端攀升的过程。
其次,按照生产区域,也就是价值链的地理分布,可以分为区域内全球价值链(intra-regional GVC)和区域间全球价值链(inter-regional GVC)。这种分类,以位于全球价值链顶端的美欧发达国家为地域圆心进行划分,具有“发达国家中心论”的主观标准。2000年至2017年,全球价值链的变化以“北美工厂”(Factory North America)的份额逐渐下降,而“亚洲工厂”(Factory Asia)的份额快速上升为主要特征。区域间全球价值链总额超越了区域内全球价值链总额的发展,标志着全球价值链的地理变迁过程。
再次,按照核心网络划分,全球价值链包括三大领域:第一领域是价值链上游,包括知识产权、核心技术、核心零部件;第二领域是价值链中游,即终端设备制造;第三领域是价值链下游,即全球物流、消费市场和金融服务。处于核心网络的国家和企业,牢牢地控制着全球价值链,尤其是核心技术和全球市场。核心网络分为企业和国家两个层次。在企业层次,跨国企业是全球产业链的中枢。全球价值链贸易的本质是跨国企业之间贸易或者跨国企业内部贸易。跨国企业控制着核心技术、知识产权、供应链和生产体系。跨国企业的企业战略决定了全球价值链发展的方向、生产结构、生产区域以及市场供给。处在全球价值链中游的企业和市场,其生产和消费,受制于跨国企业的企业战略、供应链和销售策略。
在国家层面,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网络最中心地位,美国通过三级体系控制着全球价值链。第一级体系是尖端技术,这是以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为核心的技术网络。美国政府应用行政和法律手段直接对尖端技术和产品的出口进行管制;第二级体系是全球物流网,这是依靠美国远程军事打击能力为基础的全球运输网络,小到一封邮件,大到原油巨轮,都受到美国军方的保护或控制;第三级体系是金融霸权,这是建立在以美元为结算单位的基础上,同时延展到法律领域,利用金融结算体系和超越国际法的“长臂管辖权”,确保美国企业全面控制全球价值链。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统计,截至2008年,非金融类跨国企业总数已达82000个。跨国企业在当今全球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约占全球产量和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占全球出口总额的一半。跨国企业是全球化的最重要行为体和主导者,它们推动了全球资本流动,形成了复杂的全球价值链和中枢网络,而且能够直接影响参与全球分工的国家的经济政策。
1.跨国企业的特征
跨国企业具有三方面的优势:所有权(ownership)、地域选择和价值链控制力。首先,所有权优势是指跨国企业对技术、特殊设计、品牌等知识产权和生产过程拥有所有权。因此跨国企业往往是技术密集型企业。其次,跨国企业拥有地域选择的优势和能力。从供给侧的角度,跨国企业要衡量自然资源、劳动力供给、研究机构和供应商等;从需求侧,跨国企业要计算市场规模。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共同条件,决定了跨国企业的投资区域。再次,对价值链控制力,决定着跨国企业的价值链安全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力。跨国企业把核心技术的零部件生产控制在母公司或者子公司手中,而将非核心技术等生产阶段外包给第三方合作企业进行生产或者最终装配。这种对核心技术的保护以及整合第三方供应链的能力,成为跨国企业最核心的能力,保证了跨国企业的价值链安全。
依据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排序,跨国企业之间也形成了复杂的关系。传统分类把跨国企业分为横向和纵向两种类型。横向跨国企业是指为了避免关税、节省运输等贸易成本,直接把生产企业放在销售市场所在国家或者区域内。而纵向跨国企业则是指随着通讯和交通物流成本的降低,跨国企业根据产品生产的不同阶段,把相应的生产环节配置在生产效率最高、交易成本最低的国家或地区。成本优势、规模经济和知识产权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生产中的不同位置。全球价值链就随着纵向跨国企业的供应链发展而建立起来的。跨国企业之间也严重依赖全球价值链,形成跨国企业间价值链贸易。例如,韩国半导体产业高度依赖日本企业生产的氟化氢等上游原材料,一旦日本企业禁运,韩国半导体产业就会陷入困境。
横向跨国企业主要是以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为主,在他国的企业属于跨国企业的子公司,子公司与母公司之间的生产就形成了企业内部贸易。而纵向跨国企业则更加复杂,既有直接投资的子公司,又有第三方合作企业。跨国企业无须直接投资、无须考虑企业所在国的经营成本,只需要依据产品属性和生产不同阶段,要求第三方企业按照标准进行生产,这就是企业外包的主要形态。因此,纵向跨国企业的第三方合作者的数量、规模和所在地理区域远超自己的子企业。
科技发展对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与变迁有两个主要作用,第一是降低成本,第二是决定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从降低成本角度,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认为,“由于交通运输成本和通讯成本的下降,降低了全球化的商业成本,让产业转移成为可能”。产业外包、海外生产、全球供应链成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产业转移的主要模式。科技水平对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国家影响非常重要,它进一步固化了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国际产业结构。当跨国企业成为构建全球价值链的主要行为体时,不同资源禀赋和科技水平的国家被配置在全球价值链相应的产业类型中。“标准化”、“模块化”和“数字化”将复杂的生产和技术分解到不同国家和区域进行研发或生产,一方面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快速参与全球化进程,成为全球价值链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在跨国企业对全球价值链控制力的配置下,发展中国家及其生产企业被转化为跨国企业全球价值链中的一套编码,从而发展中国家和其产业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固定位置。
这种以跨国企业为核心网络的全球产业链,对全球产业格局和国家发展的影响非常深远。由于现代科技需要大规模资金投入和团队协作才能完成,如果缺乏科技优势,一国将很难进入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跨国企业通过控制价值链上游和全球市场,让包括部分发达国家在内的大部分国家陷入全球价值链悖论中:不加入全球产业链,将会被排除在全球化进程之外,成为一个孤立和封闭的区域;而一旦加入全球产业链,跨国企业通过对知识产权的控制和母国的政治力量,加上科技本身发展的成本和规律,该国家及其产业将被“锚定”在特定产业领域,成为全球价值链编码的组成部分,进而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生产体系中,除非跨国企业发生颠覆性战略失误或发达国家发生严重政治经济危机,否则跨国企业及其母国对全球价值链的控制力很难发生变化。
现代科技的发展与竞争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力非常大,它不仅让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被锁定在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而无法实现在产业链中的攀升,而且一旦新技术(例如工业自动化、人工智能)被大规模应用后,将会替代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产业,将使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家陷入一定的困境。在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时代,发达国家也同样受制于全球价值链和现代科技的竞争。发达国家一旦点错科技树,错过新型科技和新型产业的发展机遇,也将被排除在高新技术的全球价值链之外。例如美国早年分配无线频谱波段,将毫米波预留给第五代移动通讯(5G),而美国政府和军方使用了Sub-6的大部分波段,导致了以华为公司为引领的5G技术无法在美国被使用。美国在5G产业领域出现落后中国和欧洲的趋势,这是美国动用国家力量打压华为的重要原因之一。
新自由主义推动了跨国企业建立全球价值链的潮流,产业外包成为全球价值链形成重要过程。WTO成立以后,加速了产业外包和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和发展。发达国家产业外包让分工从国内走向全球,促使国际经济从传统货物贸易转向全球价值链贸易。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成为WTO成员后,进一步推动了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和变迁。全球价值链是跨国企业总部、跨国企业子公司和第三方合作企业共同构建的研发、供应、生产、物流、销售以及配套金融和法律服务综合体系。
2008年金融危机成为全球产业链重组的重要分水岭。由于危机的影响,2007年至2010年,外国附属公司的全球生产份额下降了4%。但是同期“金砖国家”(巴西、俄国、印度、中国、南非)区域内的外国附属公司发展强劲,以平均每年9%的速度增长。同期日本跨国企业在国外的总产出是其国内总产出的四倍,而中国境内外资企业产出是中国的海外企业总产出的10倍。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和日本的产业结构是相反的。新兴发展中国家成为制造业外包的最大接收国,全球50%左右的纺织服装和电气设备制造被外包给新兴国家。中国是新兴国家中外国附属企业占全球产出权重最高的国家。2014年,外国附属公司全球产量(即制造业)的20%来自中国,而全球80%的服务产业来自OECD国家,其中50%来自欧盟。
由此可见,发展中国家虽然被“锚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一个特定区域,但是新兴国家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全球价值链为新兴国家提供了发展机遇,让本国产业融入全球经济发展之中。全球价值链的兴起使发展中国家能够将自己定位到全球价值链的一部分环节中,而无须生产最终产品。发展中国家改变过去只能出口原材料的产业结构,转向了高附加值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发展中国家能够深入参与全球价值链,从而实现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就业的增长、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和贫困率的下降。
虽然发展中国家受益于全球价值链,但是其对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和消费市场贡献更大。发展中国家是全球价值链中制造业的主要环节,生产出物美价廉的工业产品。发展中国家以牺牲本国环境、劳工权利为代价,支撑了发达国家人民的富裕生活。由于跨国企业控制了全球价值链的技术和销售环节,发展中国家只赚取了加工费和极少份额的供应链利润。全球价值链主要利润源源不断流向了跨国企业总部,跨国企业有了更加充足的资金投入到更新的技术研发中。在以美元为主要结算货币的国际金融体系中,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以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进行外汇储备。这种美元回流机制缓解了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让美国政府有了充足资金支付国内社保和维持军费开支,进而巩固了美国全球霸权。
三、政治裂隙的结构性根源
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服务型经济逐渐影响发达国家的宏观政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不以资源消耗创造财富的服务型经济主张“去增长化”,认为制造业衰退无足轻重。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去制造业”和制造业外包是同步进行的。全球价值链重塑了全球产业结构,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被全球价值链捆绑在一起的时候,既提高了全球生产体系效率、促进了全球产业蓬勃发展,但同时也造成了发达国家国内和国际两个层次的政治裂隙。
在国内层次,由于全球价值链中的制造业环节具有可被替代性,发达国家逐渐丧失了维护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动力和基础。当发展中国家受益于全球价值链的生产环节时,就意味着发达国家的中下层劳动阶层的损失。随着全球价值链贸易的不断深化,发达国家内部产业结构出现重大变化,这是导致发达国家国内政治和社会裂隙大于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原因。全球价值链带来的最深刻影响是全球产业结构的重新调整,全球制造业规模是固定的,当发展中国家快速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环节后,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就逐渐萎缩。
跨国企业、数字经济、金融与服务业让美国GDP账面繁荣。许多经济学家常常以不同产业类型对GDP的贡献率来衡量产业的重要性。在美国,制造业在GDP的比例从1950年的27%下降到2011年的12.2%。2011年,美国金融服务(包括保险和不动产)成为贡献率最高的行业,全部服务业为美国的GDP贡献了77%。然而跨国企业的利润主要来源于知识产权、市场规模和全球产业链的廉价成本,数字经济和金融服务对低端劳动就业市场的贡献并不大,因此掩盖了发达国家内传统的制造业产业工人被排除在全球价值链之外的现实。在美国出现了经济繁荣和制造业衰落、服务业兴盛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人失业并存的现象。
当金融资本的收益率高于劳动的收益率,金融资本的投机性形成的资本收益不平等就会发展为收入不平等,进而社会就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贫富差异。2010年以来,大多数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最富裕的10%人群占有国民财富的60%。另一方面,全球化为企业避税提供了便利。各种“离岸金融中心”为跨国企业提供了合法避税的通道。政府需要通过征税实现财政收入和支付社会福利,然而跨国企业和金融资本的大量利润流向了避税天堂,从而出现了企业获取高利润,但是政府却无法征税而出现财政赤字的悖论,全球化的承诺已经被破坏。
产业结构的变化让发达国家内部的国家与社会、社会与社会的政治裂隙进一步扩大。从产业结构本身来看,劳动密集型产业解决就业,资本密集型产业确保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引领科技。金融、咨询等服务业只能建立在实体经济基础上。产业性质、人口基数、教育水平决定了在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占据产业结构顶端,即在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就业的群体是少数,劳动密集型产业依然是解决就业最大的行业。研究表明,产业外包,不仅对蓝领工人在工资和就业方面都产生了不利影响,而且对白领也产生负面影响。在过去的25年里,美国的风险负担经历了从政府到家庭本身的巨大转变。这是由于不稳定的家庭收入和医疗保险成本的增加、对私人养老金更大依赖以及低水平失业救济金政策造成的。
联邦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美国就业人口的个人收入税,就业率决定了联邦财政收入。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报告,2018年美国联邦财政总收入的83%来源于个人收入所得税(包括社保费),企业所得税只贡献了联邦财政收入6%的份额。同年,美国联邦财政总收入为3.4万亿美元,支出4.5万亿美元,财政赤字高达1.1万亿美元。仅美国联邦财政支付社保、低收入和老年医保就达到了2.16万亿美元,占联邦预算的48%。5个税是美国联邦财政收入的核心,跨国企业对联邦财政的贡献率并不突出。产业流失与社会福利不均衡造成了美国财政赤字。资本收益率大于劳动收益率的结果,不但让美国GDP账面数字与联邦财政的实际收入不成正比关系,而且造成愈发严重的贫富差距。低收入人口能够享受政府食品券(food stamp)、政府医疗保险过上比中产阶级中下层更稳定的生活,社会救济反而刺激了部分群体放弃就业,专门享受政府福利。
产业结构的变化让美国陷入“劳动人口就业悖论”中:一方面许多产业工人失业,传统的工业区变成铁锈地带(Rust Belt),而很多失业群体又不愿意从事农场采摘、近海捕鱼、城市环卫、家政服务等低端劳动就业岗位,这种非工业化、非贸易化的低端劳动市场的缺口只能依赖外来劳工进行弥补,因此出现了大批季节性劳工和非法移民。因而移民问题成为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政治极化的重要议题,进而影响着美国的两党政治和总统选举,让美国政治陷入更加激烈的“文化战争”(Culture Wars)中,政治裂隙进一步扩大。
在过去,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对全球化达成基本共识,因此美国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是在稳定的国内政策和国际机制内完成的。如今为了解决美国国内就业、联邦财政赤字、低储蓄率等紧迫问题,必须重新调整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需要依赖中长期的政策规划,并且政策的实施必须具有连续性。然而政党竞争和选举政治的特性让政策高度依赖总统的偏好,民主体制很难支撑起中长期政策规划,从而让政策处于波动中。在选举政治和政党竞争的刺激下,两党只能采取越来越极端的竞争纲领才能赢得选举,政治裂隙就会越来越大。新自由主义能够释放市场力量,但是却无法保护社会,反而加剧了政治裂隙。这种政治裂隙的根源,就是美国国内的产业结构发生变化。
在国际层次,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经转向了对全球价值链控制力的竞争,价值链安全超越传统安全范畴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之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出现巨大转变。传统的自由主义认为自由国际贸易体制让后发国家的产业无法与发达国家同类产业竞争,因此李斯特(Fried rich List)的重商主义、保护幼稚产业、反对自由贸易等主张是新兴国家的发展模式;张夏准(Chang Ha-Joon)的“发达国家如何踢开梯子”理论,即发达国家利用自由贸易体制,踢开了发展中国家得以向发达国家攀爬的梯子,让发展中国家陷入发达国家控制的自由贸易体系中,使得发展中国家被限制在国际分工的低端而无法攀升。然而如今的现实是美国正在动摇冷战后建立的国际自由贸易机制,反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努力维护。这与李斯特、张夏准的理论截然相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裂隙逐步扩大,最终导致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产生结构性矛盾。
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不足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将全球产业链看作是一种静态结构,发展中国家只能受制于由发达国家及其跨国企业配置好的产业结构,忽略了新兴国家建立全产业链的能力;第二是坚信发达国家在科技领域的主导地位,忽略了发达国家跨越技术鸿沟可能会失败以及新兴国家的“进攻者优势”;第三是只关注如何防止发展中国家在产业结构中攀升,忽略了发展中国家之间可能的协作。这三点可以归结到一条,即新自由主义并不必然带来民主转型、全球化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全球产业链的发展,反而强化了部分新兴国家能够克服民主政治缺陷、通过国家动员能力实施产业政策的体制优势。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放弃原有产业结构,遵循了发达国家和跨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安排。中国在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同时,并未放弃自己的原有的产业体系,因此中国具有两套平行的产业结构。在中国,既有大量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和全球产业分工,又有一套不受发达国家和跨国企业支配的国有和民营企业体系。两套产业体系共同发展,互相竞争也互相协作。例如在中国的通讯产业领域,既有华为、中兴等本土企业,又有诺基亚、爱立信、思科等外国企业,中国市场环境让两套产业体系共同发展。中国既是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不放弃独立自主的产业体系。在发达国家制造业外包造成制造业空洞化的时代,中国却建立起全球唯一的全产业链体系。这种全产业链体系让中国不仅能够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也能够快速在产业结构中攀升,分割全球资本密集型产业,并逐渐在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崭露头角。
其次,随着发展中国家逐渐摆脱贫困,巨大的人口不再是负担,反而形成了劳动力和消费市场的红利。信息产业和数字经济建立在庞大人口基数之上,使用者越多,基础设施成本就越低。一方面,人口数量产生海量数据,反而促进了信息产业和数字经济的发展,例如移动支付、人工智能、5G等。市场规模推动产业规模,产业规模又进一步推动全球价值链的变迁与重构。另一方面,由于发达国家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具有同质性,不可避免在相同产业领域出现竞争,例如三星手机和苹果手机、美国汽车与德国日本汽车的竞争,造成发达国家之间因为产业竞争带来的政治裂隙,因此特朗普对欧洲、日本、加拿大等传统盟友也发动贸易战,以打压这些国家与美国企业的同质化竞争,进而导致世贸组织等国际机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第三,西方发达国家构建的全球价值链,希望把发展中国家锚定在一定的生产环节中,其产业被锁定,发达国家集团掌控全球价值链、固化全球价值链的结构。但是中国在全球产业发展中走出一条不同的路,在自身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同时,协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这就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本质。“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分裂现有的全球价值链,而是打破既有全球价值链的固化结构,让参与倡议的所有发展中国家在产业结构中能够攀升。从产业结构角度,中国给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产业结构中的攀升带来了可能和希望。因此,西方国家希望的一套静态固化的全球价值链和分工体系,与中国引领的动态的产业链攀升和重构进程发生了结构性矛盾,这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治裂隙的总根源。
结论
2008年,当金融危机给西方世界带来恐慌时,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却呈现出高速发展状态。西方国家再一次通过国家干预市场的方式阻止金融危机蔓延,华盛顿共识受到了来自发达国家自身的挑战。新自由主义寄希望于经济全球化带来政治民主化,但是现实却相反。这种政治裂隙的本质是民主体制难以支撑全球价值链塑造的现代全球产业结构。保卫民主价值还是保卫产业安全,成为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面临的重大抉择。全球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是全球化的赢家,而发达国家的产业工人受到的冲击最大。全球价值链改变了全球产业分工和结构,虽然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出现制造业空洞化的趋势,但却享受着发展中国家生产的质优价廉生活用品,因此政治裂隙没有发展成政治冲突。政治冲突并不是天天出现,但是政治裂隙则长期存在。
虽然国内和国际政治裂隙导致逆全球化浪潮变得突出,但是业已形成的全球价值链很难发生逆转。当世界步入由信息技术引发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产业结构和全球产业链的作用更加突出。国际竞争已经超越地缘政治和传统安全的范畴,走向了全面的产业竞争。自第一次工业革命形成的全球产业结构将会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发生巨大转变。发达国家内部的政治裂隙表明,国家的发展不能忽略资本对社会的冲击。从产业结构和价值链角度来看,任何产业部门都不是多余的,并不存在“落后产业”。
新兴大国必须以更加开放的模式融入全球价值链中,但同时也要确保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当前中美两国的竞争,本质上是产业竞争和全球价值链重构引起的结构性矛盾。当中国全产业模式和美国以跨国企业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发生冲突时,自由市场竞争原则就会被国家行政干预所取代。动用国家力量抽掉中国在产业链攀升的梯子、堵塞中国上升的通道成为美国的武器。当贸易战等直接冲突不能阻止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结构中攀升时,经济脱钩和技术脱钩将成为中美之间角力的核心,“长臂管辖”与金融制裁将是美国重要的打压武器,这种结构性矛盾将进一步扩大全球政治裂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