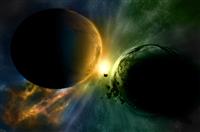
中国作家阎连科曾在《炸裂志》中感慨,我们的国家是新的,但同时又非常古老;它是西方的,但本质上也是亚洲的。它和这个世界在相互改变,并且获得了一种不现实的现实、一个不可能的可能性。总之,它拥有一套看不见的、无形的规章和制度(大意)。
毋庸置疑,当今中国的崛起是世界最重大的发展之一。这重塑了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无论是经济、科技、还是地缘政治舞台上日益强大的力量投射,中国的一切正在史无前例地改变着全球平衡。
如果说我们正在见证一个重大转折点,那该如何从历史角度进行全景式关注?众多研究中国政治或经济的学者倾向于官方角度,即认为中国的崛起是最近40年的事,始于1978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但历史学家却应了解,为了这个崛起,中国经历了远远更长时间。
如果中国的繁荣与自信在某种程度上被定义于21世纪,那也是基于它身后所具备的历史经验与遗产,基于它所积累的克服逆境的能力。
因此有必要对中国近现代史进行再思考。也就是结合过往,对当前动态达成更为精确细微的了解。有几个问题至关紧迫与重要:中国所经历、试验与追求的具体途径到底是什么?现代中国面临的问题与过去相比究竟如何?哪些历史进程与事件影响了当今中国政经制度的起源与转变?简而言之,历史视角将怎样判断中国走向未来时面临的选择?
解答上述疑问的一个基本点在于,我们究竟要回溯多远才能了解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在中国自身的悠久历史中,其实有许多思想与决策与现代性有关。我们可以在一个称为近世的时期(大约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找到起点。这一时期不仅是传统中国走向衰落的帝国晚期,也是未来发展的现代性先驱。它从1644年清朝建立开始,随着许多核心制度的发展,帝国发展达到巅峰。在此期间已经存在或新建的社会、文化等基本制度,塑造了中国随后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轨迹以及政治选择。
因此,我们所指的“近现代中国”应纯粹出于时间意义,是指将近三个世纪的时间跨度,贯穿所有关于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发展的成熟考量。它是指一套持续发展的社会建构,包括建于外来蓝图之上,对特定本土制度进行资源动员、政治利益和经济计划动员的新制度。
我们不应事先假设,世上只有一种普适的或西方式的模式才能定义现代性。这会导致误判欧美以外的现代化进程,并且会错过现代性的许多版本和变体。我们应当看到,中国人在不断地寻求西方现代性的替代品和变体,以对抗西方中心主义的、显性而单一的现代性和现代化观念。
虽然现代性所建立的基础是对近现代事物进行改造,但事实上,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国外的并存正是现代生活的一部分。因此现代性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与过去割裂。而中国传统的社会组织在许多方面不仅继续在政治和经济上有效,还在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现代性在时间和地点上都应是相对的。具体结合到中国,现代性应该是指中国各式各样的参与者持续追求的目标,这个目标是使国家富强。最重要的是,“让中国现代化”这一命题,是由中国人自己时常而清晰地表述出来的,驱动它的是重建一个强大、富裕的先进国家的愿望。
因此,我们在看待中国的崛起时应侧重于中国自身的经验和观点。老生常谈的因素(诸如文化传统的重要性,意识形态的力量以及新旧帝王之间的斗争)不应再重复,而应以中国本身的习俗制度为起点来理解近现代中国。这既可以对近现代中国历史进行广泛而又连贯的探索,又具备文化和政治上保持中立的优势。因为它并不应用外部标准,而倾向于打开中国历史本身,使之进行自身的持续性比较,并预测未来发展的可能性轨迹。
“习俗制度”在社会科学上是指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则,是人类社会为实现合作而建立的社会规律。它使团体成员基于共享规则、共同的期望与价值而相互信任,从而实现良好合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习俗制度对政治决策、社会文化及经济活动产生着深远影响。它深藏于社会记忆与认知模式之中,其无形的基础结构会跨越好几代人,决定着社会的偏好和选择。由于它本身是由个体成员内化的世界观或信念,因此,当社会面临新的情况或挑战时,既存的习俗制度元素决定着应对措施的可能性范畴,并为新情况之下的决策提供默认模式。
基于此,在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时,我们应超越意识形态的纷争,着力整合不同的历史领域,以找到更广泛的制度性结构与形成过程,从而解释为什么中国某些事态会得到发展,而某些领域则相对不足。它不应仅仅局限于统治者、意识形态与文化习俗,还应涉及到社会、经济、法律和正义等因各种原因被忽略的广度。
其特点之一是按时间顺序回顾有关近现代中国崛起的事件,并说明在三个多世纪的发展中,一个发展是如何导致另一个发展。这将为中国雄心勃勃的现代化计划提供合理而平衡的理论叙述,譬如政府、经济、主权、边界、自然资源管理,以及思想史等关键领域是怎样影响了当今中国。
这个过程中,我们首先应该抛弃对政府的偏见:在中国历史上,尽管政府是正式的关键角色和基本利益单位,但它绝不是中国社会制定习俗制度的唯一角色。相反,它应被视为众多代理中的一种。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军阀、叛军、征服者、氏族、行会和地方协会也建立或改变着习俗制度。我们不得不承认各种相关的政治角色及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另一个重点是关键性经济制度的出现与发展,这牵涉到如何思考整个近代中国史中政府与经济的关系。假定统治者及代表试图在某些约束下(如交易成本、国家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对地方精英及关键人事的依赖等)寻求收入最大化,在这种一般性的制度模型中,统治当局的当务之急是为政治制度及其职能筹集资金,因此倾向于通过高收入产权的指定来实现目标。在这种模式下,尽管经济制度强有力地影响着经济成果,但它们本身却是由政府制度和治理系统,或者更近一步地说,是由社会资源分配所决定。
另一个问题涉及到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制度。中国经常被迫应对主权和领土威胁,实际上,纵观其历史,大约有一半时间一直受到外来统治。结果之一便是出现了有效保护边界和领土安全的制度。与此同时,一系列惊人的跨界互动也使习俗、制度和文化得以共享。这使中国通过邻国与外部世界相连,而这种联系的密度与频率亦提出了如何管理向世界开放的问题。
因此,国家主权与边境安全史不仅强调了边界跨越对政府带来的潜在威胁或回报,也强调了中央与外围、跨境交易中维护习俗制度的必要性,旨在管理相关领土组织。这为考察中国边疆问题提供了持续性与多方位的线索。
在中国历史上,自然和环境在塑造人类活动条件时常被忽略,所以我们也应强调习俗制度在规范自然资源使用方面的作用。虽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将人类称为“气候的囚徒”,但是最近,当学者将重点转移到人类对地球的影响上,中国就成为一个典型例子。因为它有着悠久的众所周知的自然灾害史,这造成了损失和破坏,但也迫使社会创造出预防灾害和应对危机的工具。
直到20世纪,中国仍然继承了千年以来为了经济目的而重塑自然的传统,但这导致了不断增长的成本投入以及不断加倍的努力,方能确保空气、土壤和水等基本资源的获取。
最后,任何习俗制度史都应注重思想史的重要性,即思想、观念、符号在社会中盛行的意义。对于社会参与者而言,任何有意义的东西、构成合理选择的一切,都取决于他们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和解释,而这种认识和解释则通过象征系统进行过滤。因此,对于习俗制度的分析而言,符号的文化景观与社会、经济结构同等重要。因此,在考察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时,我们应将重点放在这个社会内部,试图探讨这个群体自身是如何理解社会、政治和全球环境的。
总之,我们应参考习俗制度的演变与发展来考察中国的现代性,以解释中国社会过去做出的选择、以及今天面对的选择。这将揭示中国社会如何利用历史性符号和制度性资源来实现一系列当代目的,包括制度实践与目标设定。中国人至今习惯在中国自身的历史话语体系中进行思考,并以长远眼光构筑世界。根据自身历史经验,他们树立了中国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
历史学者在解读中国时,首先应承认,这个国家或经历挫折与荣光,其自我组织的方式却为世界提供了广泛有力的战略以及富于意义的规则。而这些信息和规则为我们解读中国当前的行为继续提供着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