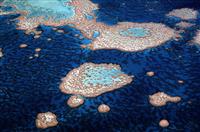
吕朝,NPI公益组织发展中心创始人。曾当过新华社记者,2003年投身公益领域。2006年在上海浦东创办“NPI公益组织发展中心”,设计运作了中国第一个“公益孵化器”,被称为中国公益领域近年来重要的制度创新。
21世纪的头10年,社会公益组织在中国蓬勃发展,NGO、NPO之类的词汇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
NGO,是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的缩写,中文翻译过来叫非政府组织;NPO,是non-profit organization的缩写,即非营利组织。
如今,一个新词横空出世,那就是NPI——non-profit incubator,公益组织孵化器,和前两个词看上去差不多,不过它并不是外来词,2006年才完成商标注册。起先它用来特指上海浦东新区的公益组织发展中心;如今,这个中心在北京、成都、深圳都有了分支机构。
10年前,普通民众对NGO、NPO还很陌生。那段时间,吕朝的主要身份还是商人。
投入公益领域后,他依循习惯性思维,仍喜欢套用商业运作模式,比如创投;他的大多数文章,对公益事业的阐释依然带着浓厚的商业色彩,比如“社会硅谷”、“公益新民营运动”。
尽管“中国公益事业的春天已经到了”的口号喊了很多年,但中国最早的“妇女热线”创始人王行娟近80高龄还在为养活她的几个固定员工而四处奔走;名声在外十几年的自闭症儿童康复机构“星星雨”还只有非常简陋的活动场地……用“乍暖还寒”来形容公益组织在过去10年中的遭遇,恐怕更合适一些。
对于公益事业在中国的发展,吕朝很清楚;和大多数坚守公益的人一样,他比一般人更乐观。草根公益组织同当年的民营企业差不多,过去30年,中国孕育了那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标志性民营企业,我们有理由期待公益行业的联想、盛大……
在他向记者表达这种乐观情绪的今天,全国社会组织的数量已经超过40万,比10年前增长了三倍多。
今年元旦,吕朝写下新年寄语:“首创并复制公益孵化器模式,率先开始公益创投实践,运营上海最大的社区服务中心,首创公益‘广交会’,发起第一个民间公募基金会……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对中国的公民社会建设有所贡献。”
生活在别处
生活本身就是这样累积着平凡,正是这一点点累积起来的经历,让他最后走到了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面前。
2000年至今,是吕朝从商业转向创意公益的10年。此前,和舶来词NGO一样,人们对公益组织还有相当的距离感。
吕朝当过记者,开过公司。他说自己很喜欢米兰·昆德拉的《生活在别处》,“人们总是无法忍受自己生活中的平凡,一些枯燥无味的焦灼,向往着自己的生活其实是应该在别处。”
1992年,吕朝顶着北大中文系学生会主席的光环,进入新华社工作,彼时,新华社记者的身份在县城百姓们看来,还是“中央来人”的级别。日子过得有一点小惬意;不过,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毕业的那一年,全国各地都在唱着“春天的故事”,创造财富的热情空前高涨,下海创业的潮流也召唤着吕朝。
两年后他决定离开。为此他缴纳了8000元“巨款”,那时还没有“违约金”一说,需要他埋单的是新华社的“进京指标”。
凭借做记者时连续三个月对期货行业的调研,他创办了一本叫《中国证券期货》的专业金融杂志。之后,看似很有前景的期货行业却几经浮沉,吕朝的第一次创业不成功。
第二次创业是做广告器材的生意。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内地,除了上海有一些霓虹灯,包括北京在内的大部分地方晚上都是黑漆漆的。吕朝瞄准了这个生意,做得挺红火。30岁不到,他在北京已经有房有车,公司在厦门设厂,在上海开分支机构。
尽管一切都顺风顺水,吕朝还是不安分,他又想着要做点别的事情了。他很快退出生意圈,准备去国外读书。
就在他重新拿起英文书的这一年,他早先出国的同学已经带着风投的钱回北京了,他们还带来一股互联网热潮。吕朝也火速成立一家互联网营销策划公司,第一个月就实现盈利,“就是吸引眼球,大量烧钱,当时国内知名的互联网公司几乎都是我们的客户”。一年以后,公司有了100多人。不过,这股热潮来得快去得也快;随着互联网泡沫的破灭,公司的业务也逐步萎缩。
“生活本身就是这样,累积着平凡,累积着时时的不如意、小纠结、小痛苦,却沉淀着它本身的意义。”
正是这一点点累积起来的经历,让他最后走到了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面前。
差一点和公益失之交臂
没想到的是,吕朝来到上海浦东新区注册创意公益机构,立刻就得到了批复。在此之前,他为NPO中心的注册等了整整10年。
从简历上看,吕朝在2003年就和公益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他应邀担任民政部下属《公益时报》的总编辑。
2005年之前,中国公益组织发展的大环境远未形成。后来成为吕朝真正追求的公益事业,还差一点与他失之交臂。
“要不是一次偶然的交谈,我可能现在仍旧是一个生意人。”在离开《公益时报》之前,吕朝向认识的人一一发去邮件告别,不到一小时,中国社科院的朱传一先生就打来电话,“他让我先不要走,再跟他谈谈”。
这位中国公益组织的先行者,当时和年轻的吕朝只有一面之缘,却把吕朝带上了公益之道。“他向我介绍了好几个公益机构,其中一个就是NPO中心。”这是NPO的能力培训机构,吕朝业余就去那里做兼职,也跟随NPO中心出国考察。吕朝说那段时间心里很舒坦,对公益产生了浓厚兴趣。
后来,NPO中心派吕朝来上海开展工作,业务模式则要求他自己设计。唯一的好消息是,吕朝来到上海浦东新区注册时,立刻就得到了批复;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在此之前,他为NPO中心在北京的注册等了整整10年。
拿到了第一笔资金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召开,第一次用“社会组织”一词代替使用多年的“民间组织”概念。社会公益的春天来了。
要想复制NPO中心在北京的业务模式,在上海几乎不可能,“民间自发的公益组织太少了,你去培训谁呢?”
花了8个月调研,吕朝发现了草根公益组织的一些共性:多数NGO没有场地,缺少设备,很多都是在家里办公;很多初创期的NGO相对边缘,缺乏政府资源,社会资源也无法介入;由于缺乏资源,绝大多数NGO无法雇用专职人员,而专业人员又是一个机构专业化的基础;大多数NGO缺乏能力建设,多数进入这一领域的人不知道怎样做成规范、持续的项目;NGO的注册,也面临法律上的疑难……
这些问题,并不是听几堂培训课就可以解决的。多年的生意场摸爬滚打,使吕朝意识到,可以借鉴企业风险投资的商业模式来创意公益事业,“公益+风投”差不多形成了他脑海中的公益组织孵化器(NPI)雏形。
2006年5月,在去菲律宾度假的空隙,吕朝完成了2万多字的项目建议书,“当时也不知道投给谁”。吕朝一方面不断找业内人士聊项目;一方面到处找企业、找基金会筹钱。
这一过程到处碰壁,一年多的时间,他一分钱也没能筹到。为了省钱,吕朝常常晚上坐从北京发车的火车来上海,在火车上安排自己第二天的行程,晚上再坐火车回北京。
2007年1月,他终于有机会与一家基金会见面,事先说好,见面的最后10分钟由他介绍NPI项目。但是在他之前的公益机构项目谈判并不顺利,本来留给他的短短10分钟都打了对折。
不过,基金会对他的公益组织孵化器概念很感兴趣,承诺给予5万美元投入。这是NPI拿到的第一笔钱。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召开,十七大报告第一次用“社会组织”一词代替使用多年的“民间组织”概念,同时提出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要“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吕朝真切感受到,社会公益的春天来了。
随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中国的NGO完成了在公众面前的第一次集体亮相。汶川大地震,中国的NGO在灾区展示了蓬勃的生命力和自身独特的价值。
井喷中的乍暖还寒
和起初资金上的捉襟见肘相比,2007年底,NPI募集到的资金突破100万元,2008年底达到700万元,去年底接近1500万元。
公益事业似乎进入了井喷的阶段。各种各样的草根组织带着好创意浮现出来。政府开始主动购买民间组织的服务,资助数量和方式也多了起来,六七百家非公募基金会成了NGO的重要资源。
和起初资金上的捉襟见肘相比,2007年底,吕朝的NPI募集资金突破100万元,2008年底达到700万元,去年底接近1500万元。
据吕朝介绍,目前NPI的资金来源有三部分。一是政府购买服务,包括提供免费工作场地。NPI在上海近400平米的场地,就是浦东新区提供的。上海市民政局最近从福利彩票募集的慈善资金中拿出一部分,启动社区服务“公益创投大赛”,大赛策划、执行由NPI承办。二是一些资助性组织的资助,如南都基金会、世界银行等。三是与企业合作(如联想集团)开展公益项目。
拿到第一笔资助时吕朝小心翼翼,他只招了一个人,租了慈善机构一处物资中心的半层楼,吃住都在里头。
NPI也要挑选项目投入,一开始主要是孵化器找公益组织。吕朝说这叫“入壳”,首批5个项目中有现在已小有名气的“多背一公斤”,借助驴友向山区孩子赠送书籍、文具;还有致力于社区公共健康的“上海新途社区健康促进社”……
NPI为这些初创期的公益组织提供关键性的支持,包括办公场地、办公设备、能力建设、小额补贴、注册协助等。为被孵化机构提供专业的指导,让优秀的项目赢得时间和机会去成长,成为吕朝和他的NPI的一大愿景。
几年下来,NPI已成为全国知名的NPO支持性组织,“公益孵化器”——这一带有全国示范作用的创新模式,已经为政府、资助机构、NPO业界、媒体和各方专家所关注,NPI在上海、北京、成都、深圳四地每年孵化30家以上的公益组织。
2009年末,由NPI为主发起成立了上海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这是国内第一个民间发起的公募基金会。
NPI也在这一过程中发展壮大,现在已有专职员工40人,硕士占50%。如今,吕朝要从100份简历中挑选2名员工。
但是,人才仍旧是制约大多数公益组织发展的重要因素。惯常的思维总是认为,做公益的人等同于“活雷锋”,最好是不拿收入的志愿者,即使有收入,也不能太高。这一点,吕朝很不同意,“你不能让帮助边缘群体的人自己给边缘化了,否则,公益不可能成为一个职业。”
“不过,如果你想找一个比企业和政府更加轻松的工作,那就别到NPI来了,在NGO工作丝毫不比在别的地方轻松;如果自以为会被当成特蕾莎修女,那就别来了,这里非常枯燥;如果你想在商业成功之后到公益组织完成从一个‘能人’到‘好人’的‘华丽转身’,那就别来了,这里总被批评;如果你把NPO当成‘职业理想破灭后的疗养院’,也别来了,因为你会从一次幻灭走向另一次幻灭……”这是吕朝给想要投入公益领域的朋友们写的一段话。
公益行业的冷暖,渗透在字里行间。
我的零零年代10问
1 在过去的10年中,世界上发生的哪一件事情让您记忆最深?
■哥本哈根会议。梁漱溟先生曾经有一本书叫《这个世界会好吗?》,今天我也想追问这个问题,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乎个体生存、发展的问题,而是整个地球、环境、人类命运的问题。
2 在过去的10年中,个人生活中的哪一件事情对您影响最大和让您感受最深?
■当然是创办NPI,实现了个人生活和行业的转轨,而此前所有的历练原来都是在为这件事情做着准备。
3 您对自己的零零年代满意吗?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您会重新选择在零零年代生活吗?
■挺有收获。我不喜欢作这样的假设,因为时光不会倒流。
4 您觉得什么是“幸福”?您自认为自己的“幸福指数”(100为最高)是多少?扣分的因素是什么?
■找到自己适合的状态。我打60到70分吧。因为我现在还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过去10年我改变了原来的生活方式,自己很受益,这两三年我也不太生病了,心态好了,自己的使命还在找,找到了就幸福百分百了。
5 您是怎么看待财富的?您希望以什么方式获得财富?
■我认为财富是做事情很重要的资源,不是为了享受。拥有财富的支配权最重要,对于公益事业来说,更关心的是财富的归宿。
6 网络改变了您的生活和生活方式吗?影响到什么程度?
■当然。没有网络几乎就没有办法生活。
7 您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多吗?在一起时的经常性话题是什么?
■并不太多。一般不聊工作上的事情。
8 过去10年,我们身处的社会发生了很多变化,您认为在推动社会进步的一些力量中,道德、文化、教育、法律、科学和制度,哪一种最重要?
■我觉得最缺少的是价值观建设,这和文化有关,和道德也有关。
9 对即将到来的下一个“10年”,您有什么具体期盼?
■中国公益事业能够进入腾飞的10年,应该说现在各种机缘都非常好,大家应该更有信心。
10 您相信“2012”会成为人类地球生涯的“终点站”吗?如果是真的话,在这几年你会选择如何生活?
■不敢判断,但是如果人类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各种力量就会聚合在一起,来避免它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