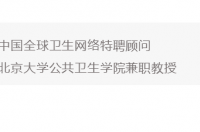注:圆圈表示各省份垃圾焚烧厂数量(10座以上),虚线表示城市生活垃圾的年产生量与处理量存在的缺口(无注明年份的均为2010年数据)。垃圾焚烧厂分布数据由芜湖环保志愿者根据互联网资料整理提供,垃圾缺口数据由王静怡整理。 (冯飞/图)
四个环保志愿者试图敲碎二恶英污染源信息公开的坚冰,但面临的困难远远超乎她们的想象。
在2011年历时七个月绘制了中国民间首个“垃圾焚烧厂地图”之后,安徽芜湖四个关注垃圾焚烧的年轻人开始了一场新“战役”:2011年12月以来的近5个月间,她们陆续向国家环保部、全国31个省份环保部门递交正式申请,要求公开二恶英重点排放源企业名单。
她们申请公开的致癌物二恶英被称为“世纪之毒”,在近年来各地垃圾焚烧厂选址风波之中,二恶英信息公开一直是公众聚焦的关键点。除了垃圾焚烧厂,二恶英污染源还包括氯碱工业、染料工业、造纸废水、金属冶炼等。
在芜湖环保志愿者提出申请之前,河南、四川、广东、青海四省已主动公布相关企业名单,而其他省份的申请回复均不容乐观。直至2012年4月17日截稿日,除了贵州省提供了一份包括317个企事业单位的重点排放源详尽名单之外,天津、云南等六省份称“尚无监测能力”,上海、湖南等七省份回复“相关信息不予公开”,北京回函是“该信息属于国家机密”,而新疆则认为公开该信息“可能对社会稳定造成不利影响”,其他省市至今未有任何形式的回复。
垃圾焚烧厂10座以下的省份数据(排名不分先后)
3月2日,国家环保部给该申请项目负责人丁洁的正式回复是:“我部尚未掌握2011年二恶英排放源信息。”
“各个部门互相推诿自不必说,一些环保厅的电话更是从未打通。”丁洁说。
另一位负责人田倩形容这样的结果为“令人相当不满意的”。早在2010年,国家环保部等九部委联合下发的一份《关于加强二恶英污染防治的指导意见》,已要求每年年底前,“各省级环保部门依法公布应当开展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二恶英重点排放源企业名单。”这也是此次申请的依据之一。
“出台文件往往处于架空状态。”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章元这样评价现今中国的二恶英政策,“没有人去执法、检查、监督,最后不了了之。”
自2008年广州番禺垃圾焚烧选址风波至今,民间抵制行动和二恶英恐慌一直未决。“我们关注二恶英的目的不仅仅是想知道它的状况,是要保证它得到完全控制、达到国家标准。”一直关注垃圾焚烧的民间环保人士、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毛达说,“但现在连最基本的公开都很少。”
而且,国家相关法规只强制规定公开企业名单,二恶英等污染物的数据公开并无具体规定。
两年前,北京市民杨子申请公开高安屯医疗垃圾焚烧厂检测数据,未得到回复。后来她向海淀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最后却因居住距离超过800米,“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被驳回。
类似的例子还有:在2011年,北京达尔问求知社垃圾议题负责人陈立雯先后向四川、北京、江苏等地环保部门申请公开七家垃圾焚烧厂数据,“最后无一例外的是得不到结果,一种情况是根本没有回复,另一种是回复说不公开”。其中向江苏省海安县环保局递交海安垃圾焚烧厂的运行信息公开申请无果后,陈立雯提起行政复议,尽管得到了“责令海安县环保局在15个工作日内重新作出答复”的决议,但最后海安县却以“向上级请示”为由至今未提供任何信息。
在垃圾围城的现实困境之下,垃圾焚烧逐渐成为中国未来垃圾处理的重要方向之一。“十二五”规划的垃圾焚烧厂就超过200座,到“十二五”末将超过300座。而其他二恶英污染源,如纸及纸板总产量,“十二五”规划年均增长4.6%;染料工业总产值将达到8%-10%的年增长率。
全国垃圾大部分进行焚烧处理的日本,在1999年就出台了《二恶英对策推进基本指导方针》:“对健康和环境的影响的实际情况,包含各种数据,以易于理解的形式将其迅速公开。”
一个具有对比意义的细节是,在2011年9月参观名古屋新南阳垃圾焚烧厂的过程中,毛达曾向工作人员提出可否查看二恶英等相关信息,对方现场直接提供了纸质版的详细数据。日本化学物质问题市民研究会成员Takeshi YASUMA介绍称:“大部分的垃圾焚烧厂都在网站上主动公布了数据,日本废弃物管理条例也规定经营者不能拒绝市民要求公开环境数据的申请。”在名古屋市政府网站,其所辖垃圾处理厂名单及二恶英排放浓度、飞灰数据等也已主动公布。
2012年5月1日是中国《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正式实施四周年,“企业排放污染物种类、数量、浓度和去向”被列为“国家鼓励企业自愿公开的信息”。但事实不容乐观,“如果信息不公开,公众如何进行监督?”毛达担心。
田倩和丁洁则说,今后还会进行长期的追踪,“这个信息是应该公开的,我们不是一定要得到名单,而是要推动政府信息公开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