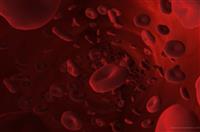NGO的工作说起来没什么稀奇,不外乎“启蒙新知,监督社会”。其最擅长的本领,是发现困难。
发现了困难之后,有些NGO“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地把困难据为己有,然后尝试举全身之力去解决之。过程很艰苦,成果很难料;有时候树敌,有时候积怨,总究很难畅快得起来。
有些NGO则只发现困难,不参与解决,不知道如何把困难推给该解决的社会生态链,结果,善于察颜观色的社会,又以为这是一家空口无凭的机构,只知道浅薄地坐地呐喊,不知道勇敢而聪明地起而行之。
鄙人在环境NGO浸淫时间不足十年,然而作为志愿者之一,也算局内之棋子,井底之浮蛙,多少听到了围城内部的心跳和脉搏,因此,今天斗胆在这里,把如何归位困难,并把如何克服困难或者说如何让困难归位的术数,讲给业内批判。行文所至,难免要举例为证,但这些例子,都只是为了说明事理的方便——因为,大家总觉得,这个世界,需要明白整理的——如果这事理说得不够精妙,那么就只能请大家原谅了,我是个表达上有困难的人,而且经常把不合时宜地把困难转给读者。
世界上之所以有政府,是因为世界上有法律。法律给了政府相应的授权。因此,中国每一步政府部门都着急忙慌地立法,而且在立法中拼命给自己增加权力的砝码,就是为了让自己从“神权天授”走向“政权法授”。
而世界上之所以有法律,是因为人类各个群体在发展的过程中,感觉到某些领域需要逐步规范和理顺,以便世界看上去不那么混乱和随机。但法律确实是不容易立的,法律要的是普遍通则,而人类行为总是乖谬失常;法律要的是稳妥和标准,而人类的表相总是动荡和错位。但无论如何,人类拼命地结晶自己的智慧,让法律看上去至少有“90%以上”的人群适合率。这样,各色法律的执行者在以法律的名义施展威权时,不至于让围观者和当事人遭受起来太过于“内心起冲突”。
由此,我们相信作为公共管理“技术手段”之一的法律,是一种公共意识,是人类持续结晶的一种相对透明和公正的智慧,对辅导人类走向相对正派和高尚的道路是有相当作用的。由此,我们也相信,法律把各种监管和执法的权力,甚至把资源占有的权力“捐赠”给政府,也是相信政府是世界上最大的公益组织,它们能够成为“社会的服务生”,尽职尽责地完成好自己的法定任务。
这时候,NGO的“监督社会”功能就“有法可依”了。并非所有的政府官员都是不可信的,但一定有政府部门和政府官员是不可信的。并非所有的政府行为都非礼乱法的,但一定有些政府部门的行为是经不起法律的仔细推敲的。此时,如果NGO能够发现政府在监管和执法上的失职,无论是政府官员个体的偶然行为还是政府部门的集体共同持续的行为,只要证据确凿,调查到位,揭发得清晰有力,那么,公众一定就会协助NGO,一起把“违法乱纪”的过错,推送到政府的衙门前,让其乖乖地俯首认错,然后痛改前非。
2012年5月初,浙江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视察温州的河流污染,他说了一句一时间传为笑谈的话:“河流污染治理是好成功,要以环保局局长和公用事业局董事长下河游泳为标志,而不以环保局的水质检测报告为准”。一时间,关心温州的,身在温州或者身在温州之外的环保志愿者,连夜行动起来,到处拍摄温州的河流污染,帮助政府痛下治理这些河道的决心,并告诉政府部门,除了官员想要到河流里去游泳,普通公众也想像童年时那样,自由地到家门口的小河里游泳。同时还告诉政府部门,环保志愿者和环保组织,愿意一起监督河流污染的治理,愿意持续监测和公示河流的水质,愿意监督官员们游泳的水是治理而得来的还是头天引自来水充数的。
这样的一个积极参与的过程,其实就是把困难转让给政府、归位给政府的过程。如果这时候,环保组织居然想自己去发明治河之术,那么就与其基本职能大相径庭了。
有些NGO幻想自己有“执法权”,这显然就是“困难僭越”的嫌疑了。有些NGO幻想自己具备比旧有研究体系更齐全的科研能力,这似乎也有“占有不适合困难”的嫌疑。但当社会欠缺某部法律时,NGO参与推动是肯定可以的;当某些法律的执行人手不足时,NGO当一当合作愉快的协警、协管,也是鼓励的;当社会在某个方向的研究不够锐利时,NGO去带动和引领一下也是必须的;当社会的调查提示能力不足,NGO去调查更多的真相并大力传播之,其结果也时常可与媒体的功能相媲美;当相关的教育启蒙工作尚未启动,NGO在当地填补这方面的空白激发社会的共鸣,是很必要的。但NGO绝对不是侦探,不是科学家,不是记者,不是法官,不是教育工作者。
把困难转移给企业
以组织的形态来说,企业也是擅长违法乱纪的“群氓”。如果说政府是忠实地执行法律已经给定的任务,那么企业除了忠实地遵守法律的要求之外,还有一定的自由经济使命所赋予它们的探索性。恰恰是这个探索性给了企业为非作歹的空间。一旦他们瞅准政府有可能监管不到位,或者一旦他们发现政府愿意配合他们共同违法乱纪,那么企业就会成为社会破坏和生态环境破坏的另一个主体。
同样是在这个时候,NGO只要事实调查到位、价值判断精准,完全可以把困难推给企业,让其承担应付的责任,让其承受应受的困扰和煎熬。同样,由于所有企业的违法乱纪行为中,一定有政府的“配合与支持”,那么,把政府列为第二被告,列为同样的困难接收方,也是NGO的从业朋友们,随时可以做的事。
企业又确实是分类的,有著名企业,有不著名企业,有外企有合企,有国家级的国企央企也有地方级的国企央企;有明星般的民企,也有黑作坊般的私企个企。总究,一切以生产商品为目的的个人或者组织,都应当视为企业。
对于那些成气候成规模的企业,无论是不是有政府作为它们的保护伞,可以肯定地说,这些企业最害怕的不是政府官员的视察,不是某个威权部门的罚款,他们最害怕的只有两件事,一是企业自身经营的所有信息的如实公开,二是消费者对它们产品的抵制。企业信息公开,是当前中国的诸多法律所鼓励甚至有所强迫的事,如果没有NGO的监督,那么这些企业可以与政府一起互相默契地玩信息假公开的游戏,但公众只要认真起来,把公开透明的“困难”赠送给企业,让其毫无逃脱和阻塞的机会,那么,企业想要逃避其应尽的职责,就不太可能。
何况还有消费者的呼声来协助。企业的产品,无论是卖给企业还是卖给普通公众,都最在乎自己的“市场占有率”。任何企业如果遭受到了消费者的明确抵制,任何企业如果存在一夜之间退出市场的可能,那么这个企业就会去做任何本来应做之事。如果他们还不肯勇敢地接收NGO快递过来的困难,并竭力去解决之,那么,迎接它们的只有倒闭的命运。当一些企业在瞬间负隅顽抗时,NGO的朋友们恰恰不要气馁,而要偷笑——呵呵,一家企业的冥顽和愚蠢,意味着另外一些企业有展现其聪明发展的机会。企业界的生态演替,就是在这样的“意外”中完成的。有时候,坚持做坏事,意味着离终点不远了。
最近有动保机构想发起对非法销售猫肉的诉讼。中国现在城市里每天有大量的猫被偷走,有的在当地城市就杀戮,有的则运到广东等地去“水煮活猫”。按照中国当前的相关法律,是有一些法律可以用来阻止吃猫肉、偷猫的行为。动保志愿者发现上海某个批发市场有以猫肉冒充兔肉以廉价出售时,马上想到一次性出钱把所有的冻猫肉全都买光,以获得足够有吨位的证据;甚至想到批发市场去开店,然后打入内部,获取更多的证据。
但这样的过程,有把太多的困难转移给了自己。这是企业经营者在违纪,只需要证明有消费者购买到,哪怕只购买一斤,就可以启动诉讼和揭露的事,如果非要“出钱买光”、如果非要潜入内部,可能就有把能量耗费在无用功上之嫌,没有通过聪明的推动,把困难——包括呈现证据的困难——转移到批发市场和监管方的身上。
把社会困难“收编”给自己
政府和企业都是明确负有法律责任的团体,而社会公众则似乎永远是无辜的。在这时候,无论是出于监督的需要还是出于启蒙的需要,把困难转移给公众,是NGO可能最不该做的事情。
甚至应当反过来,NGO要替社会解决困难。也就是说,NGO是社会困难尤其是潜在困难、边缘困难、未知困难、顽固困难的接应者,并通过NGO从业人员持续的努力,把困难转移到该转移的地方,让困难找到该解决和该负责的群体。
以环保组织为例,很多环保组织动不动就想“全民环保”,其实在我看来,这就是典型的把困难推卸给社会的行为,因为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时候,公众可以做任何法律允许的事;在政府监管不严、司法系统不给力的时候,公众甚至可以钻法律的空子成为社会灾难的制造者。又有一些环保组织喜欢搞“小手拉大手”,希望影响小朋友以让小朋友去感染其家庭,在我看来,这也有推卸困难的嫌疑,因为教育本身就是在把责任转移给“别人”,而委托小朋友去引导其家长,就更是把攻坚克难的责任推卸给了尚未成年的一代。
社会有资源也有困难。有意思的是,这些资源和困难是经常转换的,有些资源会成为困难,有些困难会成为资源。NGO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化资源为解决困难的重要能量,同时化困难为有利于社会进化的资源。换句话说,困难到了NGO手里,通过NGO的增持和努力,无论是推给政府还是企业,都将极大地有助于困难的解决。资源到了NGO手里,不仅仅要得到健康而正派的应用,而且要起到引爆更多资源的效果。在几乎所有的时候,NGO都只是引爆器和导火索,而不是炸药包本身。
江苏海安县垃圾焚烧厂导致邻近居民的新生儿患上了脑瘫,这是一个典型的“社会共同困难”,无论对于海安县政府,还是天楹环保集团下属的那家垃圾焚烧厂,还是受害者,还是当地环保局,还是当地法院,还是北京大学医学部的环境健康医学专家,还是环保组织和关注这个问题的所有人士,大家都在极力探讨这个在中国“颇有新意”的难题的解决之道。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此事件显然把企业、环保局、当地政府、当地司法部门难住了,他们显示出了最传统的冷漠、蛮横和拖延的基本状态——法律虽然给出了举证责任倒置的出路,但法院居然不采用这套办法,显然证明这些政府部门尚未有正视难题的勇气,更没有积极高潮解决困难的勇气,而是只知道一味地把困难增大后返还给受害者的家庭,让其遭受一重又一重的痛苦,持续陷入绝望中。
同时,这个难题确实也把医学专家难住了,要证明一个儿童生病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向来是世界的难题,但好在也提醒了环境健康医学的专家,得开始积极正视这类问题,因为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污染,已经让太多的人遭受了生理和心灵的重创。这时候,环保组织持续地把这个困难给传播出来,带动场面上的各聪明头脑一起运转考虑,带动社会资源来注流和暖化,也许就有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解决方案。
困难不要自己扛。准确发现困难,尤其是准确“定位自己该负担的困难”,很是考验着NGO的智商和情商。该收编的如数收编,该转让的坚决转让,该合作的积极合作,该找婆家的给找到最合适的婆家。有一些人会在工作中迷失,有些人会忙于推卸困难而让自己成为行尸走肉,有些人会过度勇敢地不该闯入的困难阵而欣喜不已——却在久战之后发现徒劳无功。
无论NGO是“接应困难”还是“转移困难”,“持续参与,咬住不放”是最基本的工作态度。只要持续而积极地发现困难和干预困难,偶然的判断失误或者行动失当,并不会影响整体的价值,甚至正是这些可笑和幼稚的失误带给了NGO更深层的活力。NGO所有的工作成果都是脆弱的,虽然可能很值得欢喜,但接下来永远有新困难在跳跃起伏,吸引你去追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