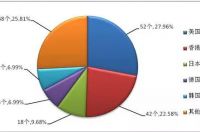纽时记者纪思道和伍洁芳夫妇在过去的25年里孜孜以求,追寻着人类的各种暴力。从一场诱发苏东阵营爆发“天鹅绒革命”的运动到南苏丹达富尔地区的种族冲突,他们先后获得两次普利策奖。不过,他们最新的著作《天空的另一半》,却展现了另一种形态的暴力,全世界范围内针对妇女的暴力,其范围之普遍、偏见之深、漠视之甚,都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这些针对妇女的暴力,从强迫卖淫到强奸、割礼、教育歧视、孕产妇死亡和贫困,在第三世界国家普遍存在着,构成了一幅21世纪的奴隶制图景。因为这些暴力形式的存在,无论割礼还是强奸或者教育歧视,都维系和再生产着社会的暴力,而非仅仅是针对个别女性或特定女性群体的,例如印度低种姓女性普遍的强奸威胁,一方面维系着种姓制度的不平等,强奸成为统治的工具;另一方面,表面上受到尊重的中产阶级女性,从这一暴力关系中获得安全感,却也被迫更加依附财产关系的婚姻制度。而在巴基斯坦,对女性的轮奸甚至可能是部族领袖发出的指令。结果,是整个部族的女性,或者女性作为一个阶级,沦为男性的奴隶,不论她是属于单个男性还是属于男性主导的社会,没有例外。
这一真相,恐怕大大超出我们的想象。即使在21世纪,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针对女性的暴力,仍然是统治的方式,甚至统治技艺的核心,却又受到如此严重的忽视。人们似乎更关心那些国家的公民权利、政治参与和经济繁荣,鲜有人将这种赤裸裸的身体政治与威权的持续或者民主发展的障碍相联系。
(一名佩戴面纱的巴基斯坦女性)
如果与印度、巴基斯坦、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女性的状况表面上似乎好得太多,不需要过多担心被强奸、被割礼,女童就学、产妇保健、经济自主、女性就业等指标要比这些昔日的第三世界同盟进步许多。但是,针对女性的暴力是否有着实质性改善,或者以其他更隐蔽的方式存在呢?因为,针对女性暴力的研究表明,对女性的偏见往往是导致暴力的原因,而各种偏见的普遍性则决定了暴力形态的普遍性和隐蔽性。例如,在非洲,割礼是如此普遍,反对割礼的组织甚至受到母亲们的强烈抵制,原因无他,她们担心拒绝割礼的女儿可能在未来的婚姻市场上被排斥,嫁不出去。在偏见的驱动下,这些母亲们自己充当了暴力的代理人,一代一代再生产着对女性的暴力。
类似的,几乎肉眼可见、习以为常的女性歧视背后,也都隐藏着各种形式的暴力,包括着三个层次:语言暴力,这一最为根本的象征性暴力;伴侣、家庭关系中的暴力;和以父爱名义滥用的国家暴力。这种划分可以揭示现实生活中无所不在的各种暴力形态,从职场的潜规则、饭桌上的荤段子,从就业和高考时赤裸裸的女性歧视,从婚姻市场上剩女的歧视,到李阳的家庭暴力,到招远麦当劳杀人案,到针对性工作者的收容教育制度,再到整个以暴力为中心的洗脑、专政体制,都存在逻辑的关联和一致性。
而这一逻辑,按照齐泽克对暴力的溯源,可以类比种族间的暴力原因,因为理性(reason)和种族(race)两个词都有着相同的拉丁词源——ratio,计算或逻各斯,意味着基于差异的对立关系及其背反产生着所谓纯粹理性,由此贯穿着古希腊以来文明对野蛮、基督教对异教徒、反犹太人、白人对黑人、富人对穷人、乃至男性对女性的征服和战争。当前述一切对立差异都被暴力本身、政治正确或者文化主义所化解,如詹姆斯·希恩所观察的暴力的衰落,那么在后现代社会仅存的也是最古老的差异,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差异便成为暴力的核心。
男女间差异及其对立关系,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男女的性别分工,狩猎与采摘。狩猎需要的是暴力、合作以及长跑,也发展出以消灭生命为威胁的暴力组织,直到今天,这仍然是人类社会暴力尤其是国家暴力的终极本质。作为哺乳动物中最能长跑的物种,长跑帮助人类不断进化,发展出褪去覆毛的体表降温系统,地形记忆和长期能力加强,大脑增大。在此基础上,狩猎所需的集体行动,也就是组织方式,一开始就朝着暴力组织方向发展,并且随着长跑能力的增强而迁徙、征服其他部落。但是,只有女性主导的采摘和种植才可能弥补两次狩猎间歇带来的热量与蛋白质缺乏,保证人类组织的存续,实现定居,人类的文明因而能够通过定居在更长期的时段内得以延续。
因此,男女间暴力-迁徙和种植-定居的差异,相当程度上能够解释人类性别对暴力的不同态度。但是,随着定居文明特别是城市共同体的发展,暴力随之趋向定居化,愈加内向化。即使蒙古人,如杉山正明所总结的,在进行世界征服大业的同时,也随之将粮草后勤基地规划为“大都”,按照阶级和分工来分配居住空间,形成蒙古式的城市模式。而且,这种围绕着暴力-权力中心的需要而规划空间的居住模式,而非欧洲自由市在教权或王权庇护下自由人的自然集中,不仅为明朝-清朝所继承,在今天仍然继续统治着中国的城市空间,并且其暴力指向从语言到家庭关系到国家暴力,从未间断。有趣的是,最近一些年轻学者从明朝继承北京提出明王朝胸怀草原的帝国理念,罔顾蒙古化都市形态本身切合明朝专制统治的内在一致性。
所谓语言的暴力,也许最好表明了暴力的任意性,可以轻易地利用知识的垄断和表达工具的控制,将任何人类差异对立化,形成社会关系的暴力,而无须诉诸死亡威胁。反之,如齐泽克所说,反抗暴力的捷径,或者抗议本身,就是寻求语言的暴力,从中获得解放。这大概最好解释了无能者的力量,口号可能是无能者唯一的反抗,无论嘲讽还是反对。
但是,对中国女性来说,首当其冲的是男性霸权的语言无所不在,无时不刻地在生产男女的不平等。例如,各种以女性为对象的三字经、黄段子在几乎任何人口中、任何场合都无顾忌地使用,包括女性自身在内在日常谈话或称谓中大量使用小姐、剩女、美女等,鲜有人反省其中包含的男性霸权。与此对应,各种对女性的歧视,从教育到就业,从工资待遇到待人接物,从男女厕所空间到精英流动,无不充满男权中心的权力统治关系,而这些不平等关系在过去三十年来,并未因为市场经济或社会改革而缓解,反而持续强化与巩固。
女性的身体在这种语言暴力下被物化,乃至婚姻制度,如同欧洲19世纪初资产阶级社会形成之际女性被迫服从于财产主导的婚姻关系,愈益成为财产的附庸,而女性在离婚后根本难以获得充分平等的权益保障,从子女抚养权到财产分割。特别是“包二奶”风气,和法国持续到二战的中产阶级蓄养年轻情人的风气,或者纪思道和伍洁芳笔下非洲大叔们蓄养年轻女孩的风气并无多少差别。在许多中国NGO内部,也充斥着强烈的男权气息,女性主义并未进入他们的政治正确辞典,一些著名公益组织甚至拒绝考虑资助女权组织,担心与其主流价值“冲突”。
这些语言暴力,最终都将转化为对女性身体、心灵和自由的剥夺,包括强奸、性侵和各种支配、控制。即使在美国,据FBI的统计,近年来每年平均有1500起丈夫和男友对女性的谋杀;而司法统计局较早的数据,仅1992年一年就发生了380万起性侵、50万起强奸案,而其中75%都是来自亲密关系的伤害。在中国,虽然无从查得确切的每年强奸案和性侵次数,但是大概很少有人会怀疑实际强奸案的发案率被严重低估,性侵次数更被到处弥漫的“职场潜规则”所掩盖,只有更为悲催的另一面:不时见诸报端的留守女童被性侵,以及趋向最为极端的暴力趋势——世界最高的妇女自杀率。
有文献表明,中国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3倍,每年自杀人数平均28.7万。而1990年以来,中国妇女的自杀率从十万分之十三稳步上升到十万分之三十左右,妇女的自杀率超过男性25%,这一现象世界仅有,而且中国妇女每年自杀人数占世界每年自杀妇女总和的56.6%。(1999年)其中,农村妇女的自杀率又是城市妇女自杀率的三倍。无论是否可用严重的相对剥夺感来解释女性的受压迫状况,导致自杀这一最极端的自我暴力的主因,农村妇女的高自杀率本身很大程度上都可自我解释为来自家人和亲戚等血缘关系的压力。
不仅如此,现实生活中,熟人、同事与上下级关系等非亲密关系,往往也习惯超越普通人际关系,侵入隐私空间,形成各种形式的人身依附,而所谓“潜规则”不过是其一面而已。结果,来自亲密关系对女性行为和自由的限制极其普遍,典型如婚姻关系中男方和几乎所有亲人对女性自由的限制、大龄女性面对的严重“剩女”焦虑。特别是婚内强奸问题,至今得不到中国法律的正式承认,仅有的一件立案把婚内强奸苛刻地限于离婚协商期间的强奸行为。如果考虑到按自杀年龄分组,过去二十年上升最快的居然是4-15岁组女性,与近年来激增的校园屠童案、留守女童性侵案、甚至与“父母即祸害”、“春节返乡恐惧族”等等豆瓣小组互参后,那么,传统的亲密关系,甚至爱,因为女性地位的不平等,最后都沦落为暴力的领域。
进而,当我们把性关系理解为正常亲密关系中的交往行为,那么,身体与金钱的交换,便可以理解为对这种亲密关系的扭曲、或者悖反,即所谓理性。沿着亲密关系暴力的进路,嫖妓便也可能解释为齐泽克意义上暴力的本质——对爱的领域的占领。也就是说,任何性交易对女性来说都是某种形式的暴力。如果追溯到女性从事性工作的初衷,也许不过是介于几种暴力形态之间相权取其轻,所谓自由性交易的真相。早在20年前1995年的北京世妇大会上,美国的法雷博士,公布了一个研究结果:在被调查妓女中,57%曾经在孩童时期受过性侵犯,49%受过暴力伤害;在卖淫生涯中,高达82%比例的妓女遭受过身体伤害,83%被武器威胁过,68%被强奸,84%曾经或者正处于无家可归。也就是说,与自杀类似,性工作可能同样是性暴力的结果。
即使在市场自由条件下,许多女性“自愿”选择性工作,也是亲密关系的剥削结果:基于为亲人筹措生病、上学费用,甚至婚娶费用等,为之做出牺牲,包括放弃教育机会、缺乏劳动市场上的足够竞争力等。而大部分性工作者,特别是底层性工作者,根据亚促会的调查,约60%在接客过程中因为男性顾客的需要而不能坚持使用安全套。男性强加的身体暴力在所谓自由性交易中再次显露。而中国现存大约300万左右狭义上提供插入服务的职业性工作者,如果考虑到更广义上从事足按、全身按摩、色情表演等一切引起性欢娱的服务业者,规模可能高达数千万,再考虑到前述每一个自杀女性的数字背后通常还对应着10到20位自杀未遂者,也即每年300到600万自杀未遂女性,不难想见如此巨大规模的亲密关系和暴力关系在市场中的相互替代,展现了女性作为一个整体或者阶级,如何超出想象地处于被压迫和剥削的地位。
但是,更重要的,无论对这些被迫从事性工作的还是所有女性,暴力不仅来自性侵经历、亲密关系的压迫和性交过程中的安全威胁,还来自制度化的暴力,即警察暴力或者国家暴力。如果留守儿童性侵、家庭暴力、招远麦当劳杀人案、专挑性工作者下手的犯罪等暴力形式,仍然无法让冷漠看客逼近暴力与女性的关联,那么国家暴力对暴力的垄断性运用并加诸女性身体,或许可以揭示中国女性承受的来自亲密关系和国家的双重暴力。
只不过,国家暴力对女性的压迫,要比市场的呈现更为隐蔽,往往以非制度化的方式进化着,却更有效。这个漫长的历史,可追溯到五四运动以来的妇女解放,对传统封建伦理的颠覆,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未发展出有力的女性理论,尽管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颇能解释革命之后的反动,如斯大林对革命的否定,妇女被革命动员之后的命运同样是被否定:领导人行列里再也没有向警予、蔡畅之类的女性领袖;曾经创造“妇女能顶半边天”神话的中国妇女运动,趋于官僚化、体制化,高高在上脱离了女性,成为男性统治阶级的附庸;60多年没有建立一个妇女或家庭部,负责女性权益和福利;消灭肉体的阶级斗争虽然休止,但是却诞生了一个新的与女性为敌的计划生育委员会,在改革开放的宽松气氛下,通过强制推行节育措施,动员基层行政力量和卫生手段侵入每一位成年妇女的阴道、子宫和输卵管结扎、上环,监视她们的生理周期,强行堕胎,并以取消福利、职位、工作和高额罚款等手段威胁、惩罚,人们日益龟缩在家庭的脆弱生命联系中,社会价值观逐渐保守化。
当然,这些都不算最严重的。继“严打”、“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后,1987年开始的“扫黄”运动延续至今,成为1949年后延续时间最长的国家动员,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严打运动。但是,这一运动的主要对象却是所谓卖淫妇女,并开始了大规模地对卖淫妇女实行收容教育,一种变相的妇女集中营,不能不让人回想到1620年率先在汉堡开设的惩戒所、1657年路易十三设立的国家收容总署,以及1697年英国布里斯托建立的第一座贫民习艺所。遗憾的是,这些福柯意义上带有中世纪残余的对流浪汉和贫民的收容、惩戒手段,却在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进程中死灰复燃,甚至在2013年为人诟病半个多世纪的劳教制度废除后仍然延续,而且专门针对妇女,特别是底层妇女,限制她们的公民人身自由。从1987年至今,估计有近50万妇女遭受过收教,每年约2.8万人被收教,收教期从半年到两年不等。
这一情景,另一半天空的阴霾,纪思道和伍洁芳恐怕也没有发现。再对照他们笔下的第三世界妇女竞赛的各种暴力,从强奸到割礼,似乎显得是那么原生态了。甚至纪思道或者安吉丽娜·朱莉等大力推动、以国际NGO和联合国人权机制和消歧公约的方式来改善的手段,也显得苍白无力,因为他们能否真正面对一个系统性的体制暴力对妇女的伤害,实在多少有些可疑。何况,俄、中以及美国里根时代的保守右翼最近共同鼓吹回归保守价值,俨然将对妇女的暴力的价值观升华为全球战略同盟的高度。
(安吉丽娜·朱莉出席反对性暴力活动与非洲妇女相拥。)
一些鼓吹儒家价值的团体兴起,组织“女德班”全国巡回培训,最近还进入了北京社区,专门教导女性如何顺从,与鼓吹“缠脚”、割礼并无本质不同,再次超出了我们的想象。那意味着,只要体制暴力还在继续,每天生活中,世界的未来,针对妇女的暴力就不会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