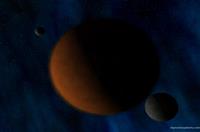2007年春节前,恩玖信息咨询中心的会议室聚集了不同领域的NGO代表,讨论的话题是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NGO注册难问题。有所不同的是,这一次面临即将到来的2007年两会,NGO决定策划一次推动两会提案的行。提案小组的第一次会议很快在各个NGO的发言中形成了统一的初期行动计划:由NGO提出呼吁书,邀请代表或委员撰写提案,媒体方面的配合造势。
几周后,几位NGO代表再次聚到恩玖,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徐永光等人被特邀参加了第二次会议。针对第一次总结的行动方案,与会人员就具体实施的步骤和方式进行了进一步讨论。
徐永光认为呼吁书的环节并无必要,媒体的配合也不一定会起到积极作用。关键在于,泛泛地提议改变NGO注册制度,对于民政部来说没有可操作性,NGO的注册还涉及到减免税等其他部门的职能,民政部也有它的局限性,可能最后还是不了了之。徐永光等人建议,在NGO几个领域各选一个有代表性的组织,比如星星雨、红枫、农家女、自然之友,这些组织历史比较长,成绩也被认可,却始终没有解决注册问题。徐认为,建议民政部用这4个代表不同领域的NGO做试点,由民政部协调相关部门,例如促成农家女在妇联注册,由民政部出面来召集相应的对话,尝试各类机构适合的方法。
提案的撰写最终由徐永光主动承担下来,在到会的人看来,这次的方案将会带给NGO人更多的喜悦和希望。
今年的两会上,徐永光递交了《关于解决民间组织登记难的建议》的提案,之后恰逢胡锦涛参加徐所在的分组讨论,徐更是夺到话筒仔细讲解。然而,自三月中旬,两会闭幕,关于NGO注册问题的反馈却再难听到下文,盲目而漫长的等待,似乎又一次预示着NGO人的失望。
在中国政治生活中,两会是如同“庙会”一样热闹的大事件,今年的两会“民生”问题突出,吸引了媒体与公众的关注度。然而在这一中国民主呼声最集中的时段里,却难以寻觅代表公民社会的NGO组织的声音。
是NGO不关注两会,是NGO始终无法取得与政府沟通的平等话语权力,还是NGO对两会之后的漫长甚至无望的行政回应失去信心?带着多重而复杂的疑惑,笔者采访了多家NGO的代表,从结果看,现状不容乐观,未来或可期待。
微弱的两会NGO声音
NGO与政府的复杂关系,贯穿在NGO从成立、开展工作到实现组织目标、推动公民社会建立等每个环节的工作中,是中国民间组织发展面临的最重要的瓶颈问题之一。在采访中,大部分被访者都意识到,NGO与政府之间的沟通,是打破社会桎梏、实施变革的有效途径,两会是重要的沟通途径。陕西省防止虐待与忽视儿童协会会长焦富勇相信:“通过两会上的讨论可以使更多的人了解到民间组织,关注民间组织的现状和困境,以及发展前景。”
但是也许期望越高,失望也越深。面对以往沟通的经验和结果,大部分NGO被访者使用率最高的形容词就是“失望”。从NGO的角度看,NGO与普通公众一样,处于政务信息接受的被动、弱势地位,公盟的许志永指出,“很多人不知道代表、委员的联络方式”,农家女的吴青也反映,“不知道谁(代表、委员)可能给NGO提议案”。
NGO与两会代表委员之间的信息不通畅,使得NGO的声音找不到代言人进行传达,NGO从根本上就很难抓住两会的机会表达观点。许志永认为这是因为“无论人大代表还是政协委员,与自己选区的沟通还是比较少。信息的透明度不够。”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所长田惠平也认为“现有立法机制,对相关利益群体的开放程度很不够。即使公众有参与的热情,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参与进去。”自然之友创办人梁从诫先生更是从自身做政协委员的经验总结:“我就是政协委员,在两会上有过多次的发言,但政府也不听我的。”
在另一个角度上,两会的众多代表、委员中,本身从事或曾经从事NGO工作或对NGO问题表示出明确关注的两会代表、委员确实屈指可数。仅以困扰NGO最深最久的双重管理体制问题为例,在2007年两会上,5000多名代表的几千份提案中仅有3份相关正式提案提交给全国政协。提案人分别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徐永光,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名,全国政协常委、苏州市副市长、“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永新。
欠缺的沟通现实
尽管现状不乐观,但NGO与政府部门的沟通有待加强确是公认的方向。NGO与政府部门的沟通,不仅是出于NGO生存发展的必需,也是NGO本身的“倡导”功能要求的。“服务”与“倡导”,本是国际上比较常见的对NGO类型或者功能的基本概括,如同NGO的两足,缺一不可。虽说在中国民间组织发展的法律框架和法制环境中,“公民社会”始终还是书本上的名词,但是草根组织顽强地集腋成裘,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争取到了“公民社会”观念的合法性。NGO要促成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不可能依靠恩赐。NGO表现出自下而上的积极参政议政的态度,是沟通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民间精英的政府游说、推动立法,是当下主要的沟通方式。公盟的许志永曾经说,“我们正在做的工作是:向部分北京市人大代表写信,并打电话争取面谈的机会,向他们表达对于现有法律的看法,提出新的立法建议,希望影响部分代表促使部分代表提出立法议案,最终修订现有法律,然后严格执法。”虽然许志永同时表示,与政府部门的沟通“并不理想”,结果往往是失望的。但他不愿轻易放弃,“我想,通过游说人大代表来改变不合理的法律是一种最理性的维护权利的方式,是一种建设性的推动社会进步的方式,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现代政治文明的生活方式。”梁从诫也提到另外一种沟通渠道,就是利用政协的渠道给有关部门写涉及民意的提议。
但更广泛的草根民间组织因为仍然处于微势状态而难有作为,大部分草根NGO的声音“没有进入当权者的视野”,深圳当代观察研究所的刘开明认为,这是因此大多数NGO已经习惯了对两会不寄希望。
对于大多数的民间组织来说,农家女的做法具有可借鉴性。吴青说,农家女是在NGO“自身规范、合法”的前提下,游说政府部门,“让他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比如农家女在1996年做扫盲时,邀请教育部来参观,听总结报告。“这事的本身就是在支持政府工作”,因此沟通取得了格外好的效果,在北京四县办的“农家女实用技能培训学校”还得到了市教育局等政府部门的支持,相关政府部门2004年给农家女拨款100万,2006年又追加110万。
河北绿色知音会长张忠民则从换位思考的角度提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面临本职工作和社会工作太过繁忙,专业知识不足的困惑。“他们有社会影响力,但是也需要提案的线索,专业性较强的民间组织,应该能受到代表、委员的欢迎。”
然而,面对目前全局性的NGO与政府沟通瓶颈,纵有破除坚冰的意愿,中国民间组织的思路,尚未能与政府部门找到更多的利益融和点。星星雨的田惠平以自己的经历总结:“我们的活动会发邀请函到政府,来不来都会发。目前是NGO有愿望和政府沟通,但是政府有没有耐心、有没有诚意来听NGO?这个主要问题在政府方面。我们NGO希望沟通的意愿是很强烈的。”
乐观着持续努力
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所有NGO都曾经或正在面对着自身能力稚嫩、公众信任度低、国家政策束缚等受限因素。NGO呼吁的问题,的确很少能成功进入政府体制改革日程表前列。而民间组织实际工作中的政府缺席,更是绝大多数时候的现实。
但接受笔者采访的大多数NGO人对于未来前景始终持有乐观的态度。在NGO人将现状形容为“失望”的同时,不断出现、频率极高的未来期许依然是“很乐观”。
刘开明比较清晰地阐释了持乐观态度的缘由:“1978年以来改革加速很快。……就这个思路来看,社会变革,会促使相匹配的改革出台,政府必须让出以往完全掌控的社会空间,必然要回归公共服务层面,才能可持续地稳定地发展。”
虽然大多数受访者只是模糊地认为,发展必然是越来越好的,但有一个观念相对明确,就是NGO必须通过行动去获得力量,通过沟通去推动政策改变,才是有效的方法。
梁从诫幽默的总结说,当下的沟通现状就是“说了也白说,不说白不说,白说也得说”。这似乎最为写实地勾勒出中国的NGO在与政府力量悬殊的制衡和沟通中,尚显稚嫩、矛盾、势微,却不轻言放弃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