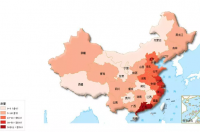志愿者是个大词,带着那么一点浪漫,理想主义,甚至一点崇高的意味。但如果用朴素的态度去看,它其实只是一种生活方式。
当你厌倦了城市,想去乡村,当你烦透了白领的生活节奏,想换个活法,甚至是你失恋了,想转变一下心情,可以考虑一下,做一次志愿者。
这段经历会让你难忘,因为伸出双手去温暖别人时,你会有同样的温暖;这种选择也不会有什么门槛,只需要你下定决心,去体验一种新的人生。
所以这期的封面专题,我们勾勒的是一幅志愿者的众生相,他们的动机各异,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他们甚至对跳蚤缺乏心理准备,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有快乐也有烦恼。
广义的角度看,志愿者的人群,其实也包括项目的策划者、投资人、捐款者、甚至是这些组织里的职业经理人,例如茅于轼先生和他的富平学校项目,尝试用经济制度来实现大规模的“帮助”,当然也是他作为经济学者,热爱的一种生活方式。
志愿者,不一定是远行,它也是一种生活心态,如果你有帮助的心愿,不妨从身边做起,你也会有快乐的收获。
只是有时,帮助别人却不一定会得到对方的回应,甚至可能会发现“凡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而这时你会不会被挫伤,从而动摇了“帮助”的决心?
(一)
司机老王开车已经20几年,但他的枣红色桑塔纳在弯道上还是吓人地弹跳了几下,雨水掩盖了路面上被重车压出的裂痕。
这里是云南省峨山彝族自治县。
汽车在离开连接玉溪和元江的高速公路不久,边远云南的贫困一面开始显露。盘山路上的破洞不时可见,拖拉机上插甘蔗般塞满了赶场的男女,放学回家的孩子在路上要随时留意不守规矩的汽车。
我们的向导是2006年从云南师范大学毕业的郭锐。郭面色黝黑,是中国-丹麦合办的云南发展培训学院成立5年来,招到的首位玉溪籍学员。
这是中国大陆惟一培养国际志愿者的学院。学员须为11个月的培训支付8000元学费,此间要在云南的贫困山村待5个月,学习如何为穷人做事。毕业后,他们可申请去非洲或印度做义工。
学员们喜欢称学院为YID。这是Yunnan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的缩写。学员们叫Development Instructor,英文缩写DI,意为发展指导员或发展志愿者。
车过亚尼,一处已被撤销的乡场。郭锐下车,从行李厢中取出一袋生鸡蛋、几个西红柿、一袋米还有一份《春城晚报》,托过路司机带给海味村的志愿者。司机们对“志愿者”这词显然不陌生,说,晓得了。这里5天才能有一次赶场,买菜很不容易,不管谁从学院下来,都会被要求带些生活用品,20来天不见的报纸和新鲜蔬菜是最受欢迎的东西。
大西村是DI们比较集中的地方,也是我们的目的地。
建在海拔2250米坡地上的村委会大院,是大西村最为醒目的建筑。大门左侧的标语很醒目:天下山苏第一村。
山苏人,是大西一带住民的自称。第三次人口普查时,被官方划为彝族的一支。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字,语言与彝语也不相同。大部分40岁以上的山苏人不懂汉话,也不知怎样和其他彝族人交流,不少人一辈子连峨山县城也未曾去过。
这里的村民主食为玉米、荞麦和金豆(类似于黄豆的一种豆子)。菜以土豆、辣椒、南瓜为主,殊少吃肉。虽然政府投资,修建了水库,引来了自来水,但大多数人还保持原来的生活习惯,人畜混居,喝生水,不洗手。
院子左侧是两层水泥楼房,楼下是政府投建的党员活动室,人造革的椅子正对党旗,成排立在会议桌旁。咖啡色的椭圆形会议桌估计是当地最具时髦特色的装置。
李艳的脸轮廓清晰,一身野外打扮,登山鞋细心地洗过,很干净。
她是3月份入学的DI,已在村委会后面卫生所隔壁的一个单间内住了二十来天。床很整洁,地上布满黄泥染成的脚印,墙角是登山包和睡袋。
拧开水龙头,李艳等黄色的浑水流变淡,把锅装满,端到厨房的电炉上。
这是清晨7时,她得抓紧备好早饭。5个6月份新来的同伴今天要到邻村查看项目的进展?D当地投建的几个卫生厕所快要完成了。
而8个月前,还在昆明外企工作的李艳不需这样早起。她的上班时间是上午9点到下午5点,不用为早点动手,也不需为等待清水多花时间。
她做了6年的行政主管,天天9点上班,5点回家。很想“换一下生活”。
“上山下乡”是YID最重要的培训内容。背景、国籍各异的DI们要花5个月时间住在乡村,在当地推动一些发展项目。
面条煮好了。桌子中间的海碗里,红色的辣子散发诱人的气味。身形瘦削的Andrea伸着懒腰第一个出现在桌子旁。他模仿中国同伴,舀一瓢调料浇在面条上,他用筷子还不熟练,尽管在他家乡?D意大利南部的一座小岛,面条也是他的每日饮食。“它们的味道不一样,”他咧着嘴回忆自己的手艺。
柳州来的邹明娟大学毕业不久,和Andrea是同批的学员,手舞足蹈一番,坐了下来,“我也要辣椒”。
邹以前学旅游,在公司做市场,来YID是想学英文、长见识。
尚禹秀原在深圳做保险,过去常为业务大量饮酒,一场大病后,信佛吃素,滴酒不沾。
南京的张丽很想做NGO,曾去一些机构面试,未获通过。
杭州来的刘金山医学背景,去过西藏、新疆、贵州很多地方。
菲律宾的Jumilo,学过农学,换过几个工作,YID学习结束后,留下任辅导员。
领队的李艳语则是YID的老学员,刚从非洲回来,现在YID临时任辅导员。
窗外绿野上,已有放牧人的影子。村头最显眼的,是那些涂成白色、类似碉楼的建筑?D这是大部分家庭必备的烤烟房,眼下正是收烟的季节。忙碌的村里人没时间观察新来的这批年轻人和以往的有什么不同。
这给刚下乡的学员们带来一些难题。他们办的学前班希望与家长们有些交流,但这些天很难聚齐。
李艳细心地让软檐帽遮挡住刺眼的阳光,然后步行半小时,到半山村头的学前班教室工地去观察进度。这座教室是学院投建的项目,大约二十来平方米的房子正在粉刷外墙。背后望去,她的行者打扮,和当地女性截然不同。
给当地学龄前儿童提供必需训练,推动学前班教育是YID的传统项目。在大西村,孩子们外出读书的最大障碍是语言。因不懂汉语,他们往往到三年级才能和老师同学对话。很难弥补的差距,迫使孩子们常辍学逃避。每年开学前,动员家长让孩子坚持念书是当地村干部们的一项工作。但至今,这里只出过一个大专生。
在学前班,孩子们要学普通话,写一些简单汉字。除了认字朗诵,他们还在这里学习怎样刷牙、怎样用香皂洗手。
当然,改变的不仅是当地孩子。这些外来的年轻人也得适应和城市完全不同的生活。一天两顿饭,菜单只有辣椒、罗卜和土豆。这里的跳蚤很厉害,甚至能钻进睡袋进攻。
在昆明时的李艳有洁癖,她回家一定会换衣服、洗手,不同意别人动她的床或东西,认为“那会很脏”。
现在,洁癖消失了。即使在汤里发现了苍蝇,她也会平静地把那些昆虫弄掉,接着再吃。
(二)
下午4点,又下雨了。
村口以西5公里,有拜火传统的山苏人刚修好一座硕大的取火圣坛。几天前的火把节,四处村寨赶来的人们把这里变成了狂欢场。人群散去,食品包装纸、塑料袋、烟头、破碗扔了一地。
26岁的李艳语领着Andrea和他的同伴们冒雨收集这些颜色各异的废弃物。不远处,站着一个放牛的小男孩。他看了半天,好奇地问:你们又来捡脏东西啊?
这让成都姑娘李艳语有些丧气,他们本希望自己的行动,能影响更多的当地人养成爱护环境的习惯。但看来不是短期可以达到的目标。
年轻人在山坡上的行为,在大西村惟一的大专生、村支书祝学勇看来,不是最好的办法:“过两天还有一个活动,那时花钱请人打扫一下就好了嘛。”
回到村委会,李艳语试图说服村干部加入他们清理垃圾的行动。一位干部笑嘻嘻地说,你们干就是了。
这些对话,从菲律宾来的Jumilo根本听不懂。他只能应付一些简单问答。他和Andrea一样,都是在互联网上看到发展学院的招生广告才到了这里。Jumilo是渔民的后代,曾跨海到台湾的工厂打工。为来玉溪学习“怎样帮助别人”,他费了不少口舌说服父母。这位长得酷似泰格?伍兹的年轻人希望自己能在中国多干一段时间,以便将来能有一份像样的简历,去找到更好的工作。
Jumilo现在关心的是那些盖厕所需要的砖瓦何时运到。乡村的慢节奏,很难让事情跟着计划走。
“我的家乡很像这里。”
Jumilo偶尔会用手机和在家乡的女友短信联络,或避开众人,打很长时间的电话。
晚8点,15瓦白炽灯下,一碗炒土豆和一碗煮萝卜摆在看不出颜色的方桌上。四口人端着碗,眼睛都盯着墙角14寸黑白电视,不时用山苏话议论两句。峨山县电视台放的武侠肥皂剧到了高潮。这家的儿子新荣留着谢霆锋式的发型,许久未打理,戳在领子上。新荣是村里的学前班教师。他对摄影师突然造访拍他家晚饭有些不快。“人家会不高兴我。”他的普通话没有轻重之分,咬字很使劲。
新荣家是大西村传统院落模式。房顶用泥土夯实,房屋紧挨着牲畜围栏,那里也是主人的厕所。堂屋地面挖有火坑。出门没有公厕,街道就是扔垃圾的地方。YID计划帮他家改造厕所,建材已在路上。
正在大西村推广的是和沼气池搭配的新式厕所,试图改善当地的卫生问题。厕所由云南一家环保机构设计,塑料蹲坑结构特别,能把尿液和粪便分开,既可产生沼气,又可消除臭味。
Andrea承认,刚来大西,上厕所对他来说是一个挑战:“我习惯用抽水马桶,不熟悉在一个洞上排泄。当然,现在没问题了。”
八千公里外的丹麦,二百年前也面临农村问题。那时的丹麦农夫很少受过良好教育,因为他们从孩提时起,就在地里干繁重的农活,而不是去上学获得知识。
18世纪丹麦神学家Grundtvig设计了一种农村合作体系,为乡村居民提供教育机会。这种教育不是让农民们在教室里通过各种考试,而是让他们无论强弱,集中起来,相互学习新的生活技能。越来越多的农夫聚在这里,学习阉割、挤奶或干燥玉米。这一合作运动改变了丹麦农村。贫穷的农夫们通过与人打交道,发现了通往新生活的途径。
这段历史,对YID的创办人、20年前从哥本哈根Metropolitan 学院教育系毕业的Lotte影响至深。
当然,对发展学院的学生们来说,在乡村的5个月,并不是带着户外装备的度假。
改变一个乡村社区的面貌,远比想象的复杂。而相应的,那些准志愿者们在这里尝试的改良也种类繁多:教村民怎样维护沼气池,帮当地妇女把她们的刺绣引进市场,教孩子们养成说“你好”“谢谢”的习惯,用笔记本电脑和投影仪给孩子放电影,鼓励孩子们学会用垃圾桶等等。
甚至还包括,提醒父母留意孩子们的保暖。在天气变化迅速的大西,很多孩子因感冒久拖不治引发中耳炎,导致轻度耳聋。
回大西的路上,路过海拔稍低的海味村。村中心YID也有一个点。院里只剩下3月份入学的扬州大学生物系毕业生石磊。石磊的头发很短,穿着背心,“我原来想象NGO应特纯洁、特高尚,没想到繁琐的事情这样多。而且,看不到结果在哪里。”
毕业后尚未就业的石磊推测,至少这段经历对将来去国际NGO求职会有帮助。
(三)
晚上8点30分,村里的公共活动室架起电脑和投影仪,光柱射到白色的墙面上?D?DDI们为村上的孩子准备了一部功夫片《霍元甲》。这部片子被DI们带到很多村民组放过。
看着李连杰扮演的霍元甲痛殴一名白人拳师,Andrea耸耸肩说,“我看了很多遍,但是不懂。”
26岁的Andrea家在意大利南部小岛上的一座小镇。两年前,他刚从大学毕业,想在亚洲寻找一份志愿者的工作,结果无意间找到了这座特殊学院的招生信息。为来中国,Andrea特地在家乡的酒吧做了一年侍者,直到攒足路费和学费。
他的本科专业是东南亚政治,覆盖地域有越南、柬埔寨和老挝。“云南有意思,离东南亚很近。”他说,“中国太复杂了,有香港这样的城市,也有这里,还保存中世纪一样平静的生活。”
中国同伴们用汉语交谈时,Andrea总是笑呵呵不说话,他的中文仅停留在问候水平。他也要在村子里待上5个月,每日奔走于不同村庄之间,查看那些厕所修建项目的进度。
语言不通,笑容成了最好的工具。闲暇时,Andrea会摸出一张纸念念有词,那是他为YID和玉溪当地联办的文艺晚会准备的一首意大利歌曲。
“中国和书上写的完全不同,”Andrea说。“将来我希望去湄公河看看?D那条河穿过很多国家。”
2005年7月入学的李艳语之前在深圳的富士康公司从事产品设计。5个月前,她离开非洲回到中国。现在,她已被发展学院位于丹麦的总部选中,即将去挪威工作5年。
“我从小到大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学校,”李艳语说。她来玉溪的目的之一,是因为听说这里结业后可以去非洲做义工。“我很向往非洲。”
赞比亚给她留下的第一个记忆是机场通往首都卢萨卡的道路,两边一无所有,长满了荒草。
尽管有大西村做项目的经历,非洲的贫穷仍然超出她的想象。没有电,每次要步行两个多小时才能找到水。
李的工作之一是帮当地村民挖井。志愿者网络负责提供所需的管子和材料,请当地精壮劳力协助开挖。和中国不同,非洲的居民居住分散,即使在村子中心打井,离井口远的人家也要走一两个小时才能赶到。
旱季的赞比亚没什么农活。每天中午1点开始第一餐饭,红色的塑料盘子装着一些包菜放在桌上供一家10口分享。男主人可以坐距离这盘主菜最近的地方吃他的玉米饼,女主人和孩子则拿着玉米面团,坐到在屋外的树荫下。那道主菜,可能只是一个中国人的食量。雨季青黄不接时,一天则只吃一顿。
孩子们普遍营养不良,腹部鼓起。
赞比亚,比艾滋病更危险的敌人是无所不在的疟疾。两个月后的一天,她骑自行车从项目地来回跑了60公里,突然高烧、发冷,后来只能裹在被子里,望着铁皮天花板发抖。两天后,非洲的上司Musonda把染了疟疾的李艳语接到镇上,让妻子照顾这个中国女孩。
从非洲回到玉溪农村,李艳语一路上不断遇到熟人,以前的DI留在当地的白色的小狗,见到她也立刻迎上来摇尾巴。
门外,刚从大西村回来的Andrea和他的中国同学约着去一位成都同学的住处吃饭。Andrea准备了意大利面条、西红柿和香肠,很快便熬了一锅地道的调料。尚禹秀则用在大西买的蘑菇做了地道的川菜。
大西村一如既往地运转。村上的小卖部甚至因为忙碌的收烟而早早关门。放假了孩子们在街上追逐,见到陌生的外乡人,会一起大声说:“你好!”
喜欢笑的Jumilo是他们追逐的新对象。又一批修厕所的空心砖到了,他要去清点接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