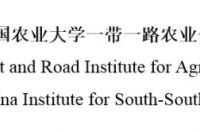
作者| 马俊乐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
徐秀丽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 IDT发起人
社会性别在国际发展领域是个关键议题,众多的国际发展机构都将其作为机构工作的核心支柱,这一方面源于发展中社会性别主流化工作的逐步推进,另一方面,也由此导致了当前国际发展架构呈现出“社会性别化”的重要特征,比如在许多国际发展报告中都需要凸显社会性别章节,在项目的规划、执行、监测评估中都需要体现社会性别要素,由此,大量的社会性别专家孕育而生,大量的社会性别分析工具和规划工具被开发出来。这也是当前我们进行国际发展合作对话无法避开的重要现实。
然而,在我国的对外援助中,经常被国际发展专家评论为“社会性别视角盲视”,即在当前“社会性别化”了的国际发展视角来看,无论是中国对外援助的历史经验、还是目前的政策实践,对社会性别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足的、甚至是缺失的,进而遮蔽了许多知识和话语,影响了合作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这一观点不无争议,另一些学者认为,社会性别是西方国际发展的产物,是后殖民主义知识体系的一部分,中国看似没有性别敏感的发展合作项目设计和项目执行事实上通过经济增长、生计提升、能力建设等方式为当地的社会性别问题缓解带来另一种途径,从而避免发展合作锁入“社会性别霸权”。
争议尽管存在,本文认为,既有的国际发展合作现实需要得到重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在我国的国际发展合作政策制定和实践中仍然值得采纳。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发展合作作为一种社会对话沟通的桥梁,本身需要开放性地关注现有的国内外实践经验,关注引入社会性别视角对我国国际发展合作的积极含义,至于如何具体落实,仍有待细察。本文以社会性别对于国际发展合作的三重贡献为例,抛砖引玉,期待推动该领域更深的探索。
一、有助于构建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理论框架
理论的构建不仅关系到合法性,也影响着话语权和发展空间。如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获得全球范围内的领导权,就离不开自身强大的发展知识生产体系[1]。然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虽然近年来迅速崛起,并且南南合作也发展了近60多年,但更多地呈现出的是碎片化的数据和经验,或者不干涉内政、互利共赢等原则,在理论建构上是远远落后的。在当前国际发展合作框架里,主流的发展理论基本上都来自西方,是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延伸。在这种理论建构中,能够清晰地看到中心和边缘的不平等结构,是基于对发展中国家想象的建构,[2]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主体性、实践经验都被严重遮蔽了。
而社会性别也面临着同样的遭遇,虽然女性运动开展了近两百多年,女性主义理论也不断创新,但基本上是“北方中心主义”,南方主体的理论和概念生产被忽视和边缘化了[3]。而事实上,南方国家的社会性别运动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亚非拉民族解放、反帝反殖民主义运动、再到国家建设发展,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北方国家的女性发展路径[4]。这种共同的历史遭遇让南南合作和社会性别是天然密不可分的,两者都是从“边缘”解读“中心”,都是对单一霸权的批判,都追求平等、多元的秩序和发展路径,因而本质关怀上是一致的。而且,近年来,以瑞文.康奈尔为代表的学者纷纷呼吁南方的性别理论,并积累了很多成果。所以,引入社会性别视角,可以帮助我国更多地借鉴全球发展的思路和方法,构建基于自身实践经验的、以中国为主体的、关怀全球发展伦理和公共产品的国际发展合作理论。而且性别平等基本上成为全球的共识,没有太多的争议,也是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理论搭建可资利用的良好资产。
图片来自网络
二、有助于完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政策制定
长期以来,中国对外援助政策从规划、实施、监督到评估,在社会性别上并不做细致的考究,由此导致对受援国的治理架构认知不全面、对他们真正的需求可能出现识别不精准、对项目的监督评估不全面等问题。例如对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评估时,在一些案例中忽略了当地既有的有比较健全的妇女发展网络的影响。许多示范中心基本上是在中心大院内组织培训班和现场示范,并没有有意识地去和当地的社会性别组织网络对接,但是部分女性在接受示范中心的技术培训后,主动通过其所在的女性组织网络向其他成员扩散,由此导致了项目的实际受益人数大大远远超过中心工作人员和项目评估人员所认知的,这就影响了项目评估的准确性,也将影响下一步的政策制定。换而言之,由于在评估中缺乏社会性别视角,许多中国援外项目其实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对于当地社会发展所作的贡献,其影响力反而被大大低估。
事实上,受国际、非洲区域和各国妇女运动的推动,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开启了国际社会促进性别平等的新纪元,[5]女性在非洲发展秩序中发挥的作用愈发重要。一方面非洲国家从国会议员到内阁成员、再到各级地方官员,女性的比例在全世界排名都比较靠前。如2017年,全世界下议院女议员比例超30%的国家,非洲有15个,占世界的31.9%,卢旺达女议员比例甚至高达61.3%[6]。而最新一届的坦桑尼亚内阁,女性就占据了副总统1名,国务部长1名,正部长3名,副部长8名。另一方面,非洲拥有大量的社会组织和网络关注女性赋权,并且从非洲区域层面的2063年议程,到各国的发展战略规划,都纷纷将女性发展放在重要位置。这些现实都形塑着非洲特有的治理架构和发展议程,也要求着中国国际发展合作政策制定时需要关注社会性别视角,才能更好地对接当地发展秩序,提升合作效率。
三、有助于提升中国国际发展合作实践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中国对外援助在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做了大量的实践探索,如对非洲的农业援助形式不断变革,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成套援建农场、农业技术试验站和推广站,到20世纪八十年代注重技术交流、人员培训,再到新世纪以来提出了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援非百名高级农业专家项目等新形式,[7]但大都随着中方专家撤出而无法持续。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对非农业援助基本上是以男性为主导的,尤其是中方专家几乎没有女性。男性主导的机制就很容易忽视社会性别视阈下的需求,尤其是在广大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农业生产基本上以女性为主,[8]他们对土地、技术、信息、金融等方面的服务需求是与男性不一样的。
那么这就要求未来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要在内容形式、援外人员配备上打破男性主导的局面。女性具备天然的亲和力,而且在可持续发展中有着当仁不让的先锋作用,[9]也有助于中国国际发展合作政策的落地和可持续。此外,笔者观察到,中国国内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对国际发展合作感兴趣、并且有志于从事相关工作,无论是笔者所在的国际发展专业、以及参与的国内与国际发展合作相关的会议、讲座等活动,女性都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而且随着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发展,传统的对女性全球流动的限制壁垒正在逐渐消失。从这个层面上讲,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也需要引入社会性别视角,充分发挥女性在国际合作政策和实践中的角色与作用。
参考文献:
[1]李小云:全球格局变化与新发展知识的兴起[J].学术前沿,2016(4).
[2]李小云:想象的建构与经验的平行分享[N].IDT,2015.
[3]瑞文.康奈尔:来自南方的性别反思[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
[4]黄平:性别研究的几个“陷阱”[N].中国社会科学网,2014.
[5]杜洁:国际有关社会性别主流化的理论观点述评——基于《超越社会性别主流化》专辑的讨论[J].妇女研究论丛,2013(11).
[6]和建花:非洲妇女参政是如何崛起的?[J].性别研究视界,2017年4月.
[7]齐顾波,罗江月:中国与非洲国家农业合作的历史与启示[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
[8]SOFA Team, Cheryl Doss: The role of women in agriculture. FAO working paper No.11-02,2011.
[9]李丹:论女性在环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与功效[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