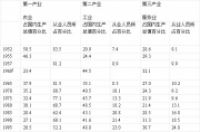社会化的抚养没有短期利益可图,现存制度也不愿意采用社会化的方式来保证人类的繁衍和教育,将生育、抚养、教育的责任更多推给了家庭。即便政府愿意为生育者派发津贴,在大部分情况下,这种津贴也远不足以补偿生育者的付出。
近日,一篇名为《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的文章在网络上疯传,文章提出应当设立生育基金制度,尽量实现二孩生育补贴的自我运转。“可规定40岁以下公民不论男女,每年必须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并进入个人账户。家庭在生育第二胎及以上时,可申请取出生育基金并领取生育补贴,用于补偿妇女及其家庭在生育期中断劳动而造成的短期收入损失。”
的确,我国的老龄化趋势日益严重,生育率却不断下降。但是,生育基金的设立真的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或者说,女性在生育期中断劳动所造成的短期收入损失真的是生育意愿不断降低的核心原因吗?
智联招聘2016年曾发布《2016年职场妈妈生存状况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中国职场女性生育意愿偏低,抚养费用高和精力不够是主要原因。除此之外,职场女性对于生育对职业发展的影响非常在意,几乎所有的职场女性都认为生育会对职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如岗位被取代、影响晋升等。同时,大部分雇主都很难对职场妈妈的福利待遇进行保障,让职场妈妈很难兼顾家庭和工作。
在传统的社会分工中,女性通常是主要的育婴人力,留职停薪的平均时间是7.1个月,女性的请假时间会较男性更长,因此造就了女性在求职期间就被迫要被询问是否有育儿打算的额外门槛,也造成进入职场的女性不敢离开工作生育的情况。上述报告就指出,通过对比生育前的工作时长、工作安排、职场待遇、职场地位,认同生育后工作职责和薪资待遇会出现降幅的人数要明显高过涨幅。
在女性看来,最担心的生育期间会发生的职场变化是“职位被别人顶替”,除此之外,女性会担心的职场变化还包括:“升职加薪难”、“再生育后难复出职场”等等。表面来看,女性是因为不愿意丧失工作机会而放弃了生育。但北欧五国自1990年以来,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基本维持在55%以上,而生育率总体上由1990年的1.8成长至将近1.9。这充分说明,并非女性拥有工作权一定导致生育率持续下降,而是因为育婴对女性的影响远大于男性,对职业生涯的阻碍更大。
事实上,2010年,我国六次人口普查指出,失业率的性别差异随着年龄增加而扩大,到35-39岁达到最大,为1.8%,40岁以后性别差异才逐渐减小,而2015年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女性》报告也同样证实了这一点。
据报告显示,25-34岁的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快速下降且远高于男性,反映出育儿妇女被迫从职场退出的状况,同时,智联招聘的报告显示,由于社会对母职的要求与女性独自承担家务与育儿工作的现状,有近八成的女性在成为母亲之后有过跳槽的打算,在生育后,女性对于职场的诉求主要会发生改变,女性生育后职场需求排名第一是“可自由支配的工作时间”,这导致许多女性被迫以从事非典型工作的方式重回职场,从而进一步使女性不敢或不愿意生育。
同时,抚养成本过高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抚养成本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个是生存型成本,或者说是生存型支出。这包括孕产妇怀孕、检测、生育成本以及抚养成本等;另一个是发展型成本或者发展型支出。这包括孩子的教育、医疗成本,甚至包括学区房的间接成本等,即让孩子高质量成长的成本。而与过去相比,抚养成本在结构上发生了很大变化,生存型成本的占比逐步下降,发展型成本占比不断提高,并且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家庭的生育决策。
▲ 从出生到大学,育儿成本最高可达百万。 © 金融界
根据Polanyi的说法,只要商品的交易越依赖货币,则商品化的程度就越高,而反映出的结果就是,消费者愈发依赖其个人的财力来决定能否获得某项服务。从上述的定义中,可以发现,相比大多数的基础教育,幼托市场呈现出极度的商品化趋势,平价、优质的公托服务少之又少。
以现金给付式发放的生育津贴不仅不能遏制这一局面,反而更支持消费者以货币取得服务、促成更多私人服务的兴起,从而愈发依赖消费者自身的财力来决定其是否能够获得幼托的服务,从而造就了价格高、质量低的幼托局面,大量的适龄儿童被排斥在托育系统之外,从而反过来阻止了照顾者回到职场。而幼托之后的公共服务也远远不足,使得照顾者要付出大量精力与时间来独自照顾儿童,从而进一步降低了生育欲望。
简单来说,现存制度不愿意采用社会化的方式来保证人类的繁衍和教育,将生育、抚养、教育的责任更多推给了家庭。社会化的抚养没有短期利益可图。即便政府愿意为生育者派发津贴,在大部分情况下,这种津贴也远不足以补偿生育者的付出。这才是生育率下降的核心原因。
不考虑生育的人,并非将生育看待成“改变现状”的期待,而是将其视为“降低生活质量与状态”的噩梦,对生育的负面印象,是一种全面社会性的排斥。“这个社会并不适合生孩子”,人很本能地会选择回避对自己不利的事情。更何况,在这个工时不断延长、生活成本不断提高、薪资不断下降、劳动环境日益弹性化的社会中,养活自己早已成为难题,成家更是遥不可及的奢望,遑论抚育下一代呢?
俄罗斯的经验表明,增加奖金或奖励对提高生育率没有帮助,生育率问题更多是和社会条件有关,和金钱鼓励的关系不大。近期对人口的比较研究得出了有趣的第二种生育趋势:社会的进一步现代化发展,将有助于生育率再次提高。女性不应该被视为生育过程中唯一的参与者,男性也应该参与其中。当男性与女性一样,透过陪产假、育儿假等方式参与到生育过程中时,不仅女性可以尽早回到职场,同时也使得女性为生育所付出的时间与精力大大降低,更降低女性进入职场和重返职场的所付出的成本。在男女平等社会结构趋向稳定后,生育率将再次上升并稳定在较高的水平。
同时,如人类学者蔡丁丁所言,当国家与资本联手提高成家门坎(如买不起、养不起),家的公共性意义如今已一变再变,成为普罗大众逃遁资本与暴政的情感依归,也成为社会边缘者退无可退的最后立锥地。家庭不应该,此时也无力承担各种幼儿、卧病、成长的照顾需求。国家不能再自我满足于残补式(residual)的社福体系、现金给付式的简单补贴,而应该主动提供更多平价、优质且非现金给付式的生育相关公共服务,切实降低家庭负担。而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再放任低薪过劳的劳动环境继续存在,只有一个自己活的下去且生活质量高的社会中,人们才会、也才敢有抚育下一代的想法。
生育,意味着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与成长。也因此,生育问题绝不仅仅是关于家庭与性的问题,它也关乎于工时、社会环境、教育体系等等许多问题。它就像我们这个社会的缩影,反映着我们的社会,是否友善到有资格也有能力迎接新生命的诞生。生育基金解决不了问题,抓不住核心问题,却胡乱开药,只能误国误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