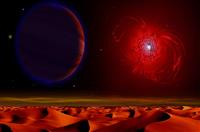这两天看到博文:钱学森给吴仲华的报奖成果做鉴定
俺当时评论道:这说明钱学森不是合适的评阅人,大同行。王虹宇老师回复到:钱总是一直鄙视这种基于数值的计算吧,倒也不算不合适。
在我去google吴的1950在NACA的报告后,更加坚定不移地认为俺的观点是合适的,有依据的。
Wu, C.-H., 1952. A General Theory of Three-Dimensional Flow in Subsonic and Supersonic Turbomachines of Axial-, Radial-, and Mixed-Flow Types. NACA Report TN-2604, NASA, Cleveland.
这篇文章迄今还在被引用,已经是774次了
吴仲华的(可能是求解上文某个方程的数值计算)工作最终获得了二等奖,先前的投票表决是三等奖,后来有了组织方面的干预;见“中科院科学奖励制度的建立与首次评奖”。
那么为什么钱学森没有建议一等奖呢?原因真的或许是王老师给出的答案:钱总是一直鄙视这种基于数值的计算(可能王老师读了钱的许多信件和讲话而得出结论)。不过俺觉得还不止于此,应该换一种更“合适”的说法。这就是学院派和企业阵营的分歧。钱作为CIT的冠名教授,他追求的是宽泛的、解析的 (gengeral, analytic) 、数学上美丽的结果;将“能全面地领导燃气轮机的发展”的工作“列为技术科学研究之最高成就”,这就是学术界的“道”。而吴的工作与方法则来自于解决实际问题的需求,他之所以取得当时的结果,没有达到钱眼里的“最高要求”,也是实际问题所限。
例如俺最近的工作就是一个合适的例子,现在还在应用的霍曼转移(地月、地火转移轨道)最优性的解析证明,以及空间飞行器的拦截问题。前者一旦提出 formulate 合适的数学问题,可以给出严格的解析证明,而后者在尽可能解析以后(给出变分条件),它的诸多性质也只好求助于数值技术了。
俺从根本上认为,一个未说出口的原因或许是问题的难度。学院派理所当然地强调,解决“人所不能”的问题才彰显一个人的“学术品质”(这或许包括像俺在霍曼转移工作那样,指出“你们都错了”)。很多时候的第一在于“闻所未闻、前所未做”,第一个“吃螃蟹”那些人,需要的是机遇和勇气,而不在于他们的天赋。张三能第一个吃螃蟹,往往李四有了机遇,也是敢于第一个吃螃蟹。所谓天赋就是无论别人怎么努力,包括去吃“狗屎”,也达不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学术品质”,按照数学家哈尔莫斯的说法,它包括“天赋”和“学术训练”;有“吃狗屎”的勇气,显然是后天的磨练,否则是狗就不是人了。天赋大概包括自己找到机遇的能力,而不是“老天爷”给“机遇”;抓住机遇的能力,后天的训练可以达到。学术给予了一个人展现“天赋”的战场;而你的战利品帮助人们,鉴别你的天赋。
吴仲华的工作,还在被引用和使用;依据文献的引用,俺猜测(而且故意这样说)它是作为一种方法的。(这一点,专业人士应该反驳,如果俺说的不对)
HFDT is a Siemens standard through flow analysis code that computes the performance of the multistage compressor as an axisymmetric model. HFDT is essentially a two-dimensional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code based on the streamline curvature method, as reported by Wu [22].
这一段英文来自于英国的一篇文章,它的发表时间是 9 December 2020,[22]就是吴的1950年的报告。显然,吴的工作还在支撑工业界的技术,它基于吴报告的方法。既然加了定冠词,那么它指的不是唯一的方法,而是特指吴贡献的方法,而不像"the sun, the earth"。
科学研究的成果(或者俺再加上“方法”)是要“过时”的,如韦伯在《以学术为志业》中所言。钱学森作为学院派的代表,他追求的是一劳永逸,直白地说,是永恒的东西,是不“过时”的成果和方法。如果他还活着,在看了俺的今后不会被过时的霍曼转移最优性证明以后,一定会非常高兴地修改他1950-60年代的讲义“星际航行概论”相应部分。
唉,俺写博文的风格,还是一如既往、坚定不移地吹牛,特别是被降为“四级教授”以后。
那些比较对社会的直接的,包括政治上、经济上贡献的地方,不是展现一个人“天赋”的好场所,而国际数学上的奖项,包括很少的一部分诺奖,能够衡量天赋。天赋是人之初,反映了一个人的 originality。
假入流水能回头,那一年的中科院一等奖,非吴莫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