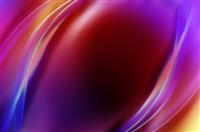
看上去《美丽与哀愁》的作者做了一件很容易的事,他把23位世界大战亲历者的书信、传记、回忆录以及其他资料中的细节,放在一起,按照年月日重新排列组成了一本书:告诉我们1914年8月穆齐尔在柏林看到了慷慨激昂的人民,卡夫卡在布拉格看到马拉着加农炮走过,而帕尔·凯莱门穿着轻骑兵制服,乘出租车到了火车站……
但如果你认真地读完这本书,就会发现作者其实做了一件非常神奇的事:通过他仿佛仅仅握着剪刀和胶水的手,在这本书中再现了一个世界。那个一百年前已经远去了的世界,不是作为地图上用颜色代表的国家,不是条约上的签字和火漆印章,也不是旗帜、统计数字、部队番号或条约上的文字条款; 而是作为活生生的人出现在我们面前。他们怎样在那个夏天听到两个陌生的词“宣战”和“动员”,怎样离开家,怎样在高奏的爱国歌曲和国歌声中,在亲人的哭泣和陌生人挥动的双手中登上列车。在营房、列车和原野上试着面对这一切,不是演习、不是旅行也不是开玩笑,在成群的难民、燃烧的村庄、倒闭的牲畜中穿行,被炮弹轰击,被枪弹扫射,然后在恐惧和震惊的瞬间,第一次意识到,这是“战争”!
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严肃的读者”有时会陷入困惑:怀疑自己究竟在读什么,“历史”还是“小说”?和人们习以为常的严肃历史相比,这本书实在太文学了:燃烧的甲板、震耳欲聋的枪声、赤日炎炎中在巴勒斯坦干燥的土地上行军,这一切都显得太生动。但和小说比起来,它又太真实,雷马克、阿诺德·茨威格、巴比赛的小说对我们都不陌生,那些书读起来是沉重的,放下时却很轻松:因为无论读到什么,我们都可以安慰自己这是一本小说,潜台词就是这一切都是虚构的。而《美丽与哀愁》刚好相反,阅读时轻松愉快,放下时异常沉重,书里的一切都是真实的,这些活生生的人,在生活在观察,更多地在战斗,在经历那些写在纸上被我们看到的事。
无论我们有多少种理由去阅读一本书,却总有个理由可以一票否决我们去读它,那就是“它好看么”。对这个问题,我觉得最正确的回答是:你完全不需要特意抽出时间去阅读它,因为《美丽与哀愁》格外有趣,你可以在任何时间读它,随着它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世界。
这本书有23个主人公,其中很多人今天已经无人不晓,比如在本书描写的时代,越来越无法掩盖自己敏感和焦虑的弗兰茨·卡夫卡,那时他是布拉格社会保险的一名犹太职员。
此外,还有图书馆管理员罗伯特·穆齐尔,在本书所描述的这四年中,像他有生之年的大部分时光一样默默无闻,他的书到二战后才突然被德语文学界发现,然后成为二十世纪最著名的作家之一。在本书开头的1913年,穆齐尔用“重度神经衰弱伤及心肺功能”的医生诊断书向维也纳综合理工大学请长假,在柏林对市民中爆发的战争热情冷嘲热讽,但几个星期后,他就回到故乡维也纳报名参了军,用他自己的话说战争像疾病一样向他袭来,比发烧还厉害。在战争的这些年中,他在阿尔卑斯山前线战斗,但表现得很不好,当上连长又被撤职,家人因此而深感耻辱,但他自己找到了一个淳朴的农家女孩,对职位的升降处之泰然。战争末期穆齐尔回到维也纳,成了战时通讯社的军官,坐在巨大的办公室的角落——自己的办公桌边,显得微不足道,作者在这里向我们指出,穆齐尔的作品《没有个性的人》此时已经渐渐浮出水面了。
如果说这个新大陆冒险家就像一个冒失鬼闯入了奥斯曼帝国的最后岁月,那么帕尔·凯莱门,则是奥匈帝国最后时刻最好的见证者。他来自布达佩斯的一个体面家庭,是位喜欢小提琴的英俊的轻骑兵军官,本书中他的段落颇为引人注目:穿着轻骑兵华丽的刺绣上衣,在人流中登上列车,然后就被卷入战争。
在全书末尾,凯莱门在列车上看见了布达佩斯的灯光,然后乘坐一辆顺路的马车回到了阔别四年多的家,而在1918年匈牙利脱离奥匈帝国的革命中,为了回到此时正在急剧左转的布达佩斯,他还得小心地遮好自己的军衔和勋章,战后的岁月在他踏进家门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当他在自家的厨房里倒头睡去的时候,一个漫长的故事结束了,四个辉煌的帝国和它们的王朝的历史也在这些入睡者的鼾声中终结了。没有人站起来唱1914年到处高奏的国歌,没有人挥动送他们离去时的鲜花。这是一个世界的终结,但在之前的战争中已经有太多的世界终结了。那些在战场上丧生永远不能再回到亲人身边的人,每一个都是一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