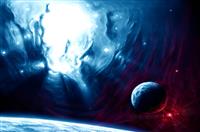
一个满心烂漫而又美丽的女人嫁给了一个老实愚钝的男人,悲剧就这样产生了。
夏尔单调、麻木,空有一片仁心,却无知无趣无感。爱玛的思想无法与他诉说,他们生活上越接近,心理上的距离反倒越远了。
“他以为她快乐,不知道他怨恨的,正是这种雷打不动的稳定,心平气和的迟钝。”
她不满于琐碎无趣的日常,她不喜无聊无能的丈夫,她甚至怨念他对她卑微全情的好—她觉得目前的生活配不上她。
她也曾如春天的清晨般美好,只是曾经对爱情的幻想破灭,好似深陷牢狱,她的生机和灵气渐渐消失。爱玛的问题在于,她不满于现在的生活,又不知道或没有能力做出改变,于是只能误入歧途。
她先后经历了两个情夫,渐渐的沉迷声色和物质享受,为此欺骗夏尔,债台高筑,她以为追寻到了自己想要的爱情。可是她越陷越深,幻想得到更多的幸福,却把所剩无几的幸福挥霍得一干二净了。
“新奇的魅力,渐渐地像件衣裳那般滑脱,裸露出情爱永恒的单调,始终是同样的模式,同样的腔调。”爱玛的梦想破灭了。
爱玛的行为不值得提倡,但我却很同情她。夏尔的愚钝令人厌恶,但他的仁厚也令人无可指摘。也许一开始她就嫁错了人,嫁错了之后又不懂得欣赏和感恩这个平凡医生的种种好处。
大部分悲剧中都闪烁着哲学的光辉。每个人身上其实都藏着一个包法利夫人,也有可能要面对一个包法利。这世上少有天生的贞洁烈女,同样也少见荡妇,人们只是在摇摆中,在挣扎中,稍稍前进了一步,或稍稍退后了一步,便被打上不同的标签。爱玛的悲剧在于,她首先对自己没有准确的定位(很大程度上自视过高),其次并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就盲目地去追求。最重要的,她没有立身于世界的工作和人生目标的支撑,于是混混沌沌,被欲望、虚荣心和不知所起的愤怒裹挟着走向自我灭亡的道路。
说到底,是一个人如何把握和平衡现实和理想的关系。即便不满现实也要尊重现实,即便拥有理想也要警惕那是否只是错误的幻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