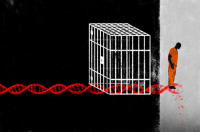
冤案是什么?就是没有罪而被当作有罪判决或受处罚的案件。
基因鉴定技术是一项生物学检测技术,人体细胞有总数约为30亿个碱基对的DNA,每个人的DNA都不完全相同,人与人之间不同的碱基对数目达几百万之多,因此通过分子生物学方法显示的DNA图谱也因人而异,由此可以识别不同的人。
近一个世纪以来,指纹技术给侦破工作带来很大方便。但罪犯越来越狡猾,许多作案现场没有留下指纹。现在有了DNA指纹鉴定技术,只要罪犯在案发现场留下任何与身体有关的东西,例如血迹和毛发,警方就可以根据这些蛛丝马迹将其擒获,准确率非常高。DNA鉴定技术在破获强奸和暴力犯罪时特别有效,因为在此类案件中,罪犯很容易留下包含DNA信息的罪证。
根据DNA指纹破案虽然准确率高,但也有出错的可能,因为两个人的DNA指纹在测试的区域内有完全吻合的可能。因此在2000年英国将DNA指纹测试扩展到10个区域,使偶然吻合的危险几率降到十亿分之一。即使这样,出错的可能性仍未排除。
自从DNA检测技术1987年首次在美国法庭中发挥作用以来,便一直在寻求公正的过程中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
图中为无罪释放后的陈龙綺(左二),台湾冤案平反协会主席(左一),格雷格·汉比基安,以及陈龙綺的妻子。
据报道,如果你看过《犯罪现场调查》这类的犯罪类剧集,就会知道DNA证据往往是审清案件的关键因素。如果嫌疑人的DNA与犯罪现场的DNA相符,就足以给他们定罪。但问题是,情况并非永远这么简单。大多数人认为DNA检测不可能出错,但检测分很多种类,还有很多解读方式。在犯罪现场收集证据和在实验室中分析证据的过程中,有时便会出错。
对陈龙綺而言,一次糟糕的DNA测试改变了他一生的轨迹。
2009年5月25日清晨,陈龙綺正在他租来的一家台湾零售店外和朋友们喝酒。凌晨3时左右,两名女性加入了他们。据陈龙綺和他的律师称,陈龙綺不久便离开了这伙人,去接妻子下班。在凌晨4点至6点间的某个时段,两名女子遭到强奸。虽然受害人并未指控陈龙綺,也没人指认陈龙綺在罪案发生时在场,但他最终却被判决有罪,判处四年有期徒刑。是DNA证据将他与罪案联系在了一起。
五年后,第二次DNA测验显示,陈龙綺的DNA与犯罪现场根本不相符,于是他被宣告无罪。在他被控强奸的几年间,他失去了他的妻子、事业和大部分人生。他拒绝服刑,宁愿作为逃犯,孤单地生活在抑郁和羞耻的阴影中。
陈龙綺的这种情况被称作巧合配对(coincidental match)。调查人员一开始测试了犯罪现场找到的几人DNA混合物中Y染色体上的17个基因标记物,结果陈龙綺的DNA吻合。但增加标记物数量之后,结果就不吻合了。因此陈龙綺的DNA并不是犯罪的证据,而是一种做DNA测试时极少考虑的统计异常现象,即所谓的假阳性。
“所有DNA(证据)都各不相同,很难解释,”协助解除陈龙綺罪名的美国博伊西州立大学教授、爱达荷无罪项目主管格雷格·汉比基安(Greg Hampikian)指出,“就连专家也不能保证每次都理解正确。”
自从DNA检测技术1987年首次在美国法庭中发挥作用以来,便一直在寻求公正的过程中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光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DNA数据库就涵盖了1200万份数据,每年可为数万名调查人员提供帮助。仅在美国境内,可当作犯罪证据的DNA测试就有许多中。DNA标准测试为STR 检测,出现巧合配对的可能性仅有十亿分之一。但在某些情况下,其它测试可能效率更高、更具性价比。调查人员选择进行哪种测试、以及解读的方式,都会大大影响案件结果。
因此,虽然法庭很少怀疑DNA证据,但越来越多的学术界人士呼吁调查在犯罪调查中采用DNA证据的方式。陈龙綺的经历更是令汉比基安等人支持以更审慎的态度利用DNA证据。
DNA证据最不容置疑的一点,便是人们对它的绝对信任。2005年的一次调查显示,85%的美国人认为DNA证据“非常、或完全可靠”。另一项于2008年发表的研究显示,陪审员认为DNA证据的准确度约为95%。澳大利亚近期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存在DNA证据的性侵案件发展到庭审的几率比一般的要高一倍,最终定罪的几率更高达无DNA证据的33倍;谋杀罪发展到庭审的几率为14倍,定罪几率为23倍。该领域科学家有时将人们对DNA证据的偏爱称为“CSI效应(即美剧《犯罪现场调查》)。
DNA并不是无可辩驳的犯罪证据,也不是无罪证据。但在陈龙綺的案子中,错误指控他与罪案相关的DNA证据的重量远比证明其无罪的证词重得多。
要明白这是怎么发生的,首先要理解实验室进行DNA样本配对的原理。法庭分析专家不会对嫌疑人的整个基因组进行分析,而是选择几个通常差异较大的关键部位,即”标记“。在审理陈龙綺的案件时,实验室分析了17个不停的Y染色体标记。然而,这种Y染色体检测法并不如最常采用的短纵列重复序列检测法(即STR)那么具有针对性。两种测试法分析的都是所谓短纵列重复序列,即基因组上包含几处重复DNA片段的部位。不同人基因组上不同部位的重复序列数量可能有很大差别。但Y染色体检测法只分析了一条染色体上的17个部位,13标记检测法分析的则是多条染色体上的13个部位,大大降低了出现巧合配对的概率。除同卵双胞胎外,STR测试中13处标记全部吻合的概率约为十亿分之一。
汉比基安指出,许多犯罪实验室仍在使用导致陈龙綺蒙冤入狱的检测方法,不过也有一些实验室正逐渐开始采用为其洗清罪名的23标记Y染色体检测法。
在另一例显示了DNA证据强大力量的案例中,汉比基安利用DNA证据帮克里斯托弗·塔普(Christopher Tapp)洗脱了罪名。1998年,尽管DNA与犯罪现场的样本并不温和,他仍因谋杀罪被判25年有期徒刑,直到今年春天才出狱。当警察于2015年重新审理这桩谋杀案时,DNA测试结果险些使另一个无辜的人蒙冤。警方对DNA记录进行了筛查,寻找与犯罪现场DNA近似的人,最终锁定了一位名叫迈克尔·尤斯利(Michael Usry)的男子。在35个标记中,他有34个标记与杀手吻合。就像陈龙綺的案件一样,调查人员只分析了Y染色体,只不过这次他们分析的标记为35个,而不是标准的17或23个。
当分析人员只考察Y染色体短纵列重复序列时,他们基本上要查看整个Y染色体。Y染色体的基因信息名叫单倍型(haplotype),父子的Y染色体单倍型完全一致,因此一个种族中可能有许多Y染色体完全相同的男性。如果采用更加标准的测试,尤斯利便会成为巧合配对,被判有罪。但警方决定在他的亲戚中寻找完全配对者,最终从尤斯利的儿子身上提取到了样本。标准的Y染色体STR检测法可能会使他蒙冤入狱,但采用35标记法,他的儿子最终也得以脱身。DNA测验出错不仅会使无辜者蒙受牢狱之灾,还会导致应当受到法律制裁的人逍遥法外。
陈龙綺的案例突出了汉比基安等人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混合DNA。
在陈龙綺的案子中,之所以采用DNA检测,是因为两名受害人喝醉了,无法认出袭击者。陈龙綺的两名朋友均承认与两名女子发生了性关系,但声称是对方同意的。此外,陈龙綺的妻子告诉警方,陈龙綺接她下班的时间在早上4点左右,她下班时盖的章也证实了这一点。陈龙綺称自己4点左右离开零售店,他的朋友之一确认了他的证词。
调查人员决定对其中一名受害人内裤上的精液进行DNA检测后,他们决定让三名男性的DNA均接受测验。内裤上的DNA混在了一起,无法辨别哪些DNA片段属于哪个人。但由于混合物中的DNA来自不止一人,很可能会有某一名嫌疑人与17处标记全部吻合,因为能够与之吻合的标记组合不止一种。
“这就像把我的名字和你的名字拆开来,再用这些字母组合成上百个名字。”汉比基安说道,“这使得测试结果格外具有迷惑性。”
汉比基安和他的团队后来所做的计算显示,陈龙綺符合上述DNA的几率为741分之一,这意味着在一座2300万人的城市中,有几千人可能与这条内裤上的DNA吻合。做测试的实验室总结道,陈龙綺“或其直系亲属不能从嫌疑人中排除”。依照这一证据,陈龙綺被判参与轮奸,并于2012年被叛入狱。另外两人也与结果吻合,因此亦被定罪。
陈龙綺拒绝服刑,对律师表示他不愿“为自己没做过的事自愿进监狱”。他还联系了台湾冤狱平反协会,该协会在陈龙綺的判决中看到了明显漏洞,立即动手准备上诉。他们要求重新检测DNA,将标记数量从17增加为23。在新增加的6个标记中,陈龙綺只有4个吻合。这项新证据说明他不可能是混合DNA样本中的DNA来源。此外,样本中的全部基因标记都可用被定罪的另外两人的DNA解释。据此证据,法庭同意重新庭审,推翻了对他的判决。
美国莱特州立大学DNA证据专家丹·科伦(Dan Krane)指出,在他看来,陈龙綺的案件中一开始就不该采用DNA证据,因为该DNA样本属于混合物。
“混合后的Y染色体STR测验不应被纳入考虑范围,”他说道,“一旦发现这是混合的,就该放弃这一样本。这样就能直接解决问题。”
美国国家标准技术所的法庭科学家迈克尔·科伯(Michael Coble)认为,进一步检测也许本能帮助台湾的法庭科学家判断DNA混合物是否主要来自一名嫌疑人,否则从中收集的信息便存在很大局限。
“DNA证据决定判决结果时,最关键的其实是对证据的解读方式。”
在2013年由国家标准技术所开展的一项调查中,该机构要求108所实验室对一份包含四个人的、伪造的DNA样本进行分析。他们还提供了一份并不在该样本中的、编造出的嫌疑人DNA信息。结果70%的实验室都认为这名伪造的嫌疑人DNA与样本吻合。
联邦调查局表示,虽然他们也将DNA混合物视作证据,但只有当实验室能确定样本中的DNA主要来源于某个人时,他们才会这样做。(FBI还证实,他们仍在采用导致陈龙綺被定罪的17标记Y染色体STR检测法)。在一项针对陈龙綺案件的新研究中,汉比基安指出,此类证据只能用来排除嫌疑人,而不能为他们定罪。科伦则认为应彻底弃用这种检测方法。
“DNA信息应当非黑即白,”科伦说道,“不存在灰色地带,尤其是当牵涉到某人性命的时候。”
“我觉得理解这一点的专家也许有一百人,不理解的则有成百上千。”科伦指出,“还有一些不愿去理解的公诉人。此外,还有很多一听到DNA就两眼放光的辩护律师。很难在课堂上教会他们这一点。”
弹道分析、指纹和纵火痕迹一度被视作无可辩驳的科学依据,可排除调查中的人为误差。但今天已经广为人知,这些调查方法的结果并不一定可靠。在法庭科学中,DNA证据正逐步引起人们的怀疑,使人们对采集和分析DNA的条件提出严格要求。在2008年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称“DNA证据往往笼罩着一层神秘的、确定无疑的光环。”但DNA证据并非“生而平等”。不错,它们可以为案件板上钉钉,但前提是DNA样本采集合理、测试得当。
汉比基安指出,DNA对公众想象的神秘掌控力应当使所有人感到不适。
他表示,陈龙綺是令他这样的专家对DNA测试的真伪产生关注的少数案件之一。
“我们必须时常审视自己对各种测试方法的依赖情绪,”他说道,“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犯错,并且要过很久才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