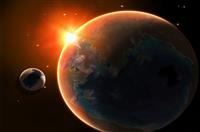这样的声音并未掀起波澜。
直到2021年11月,网红主播雪梨偷税漏税被罚6000万,一个月后,另一大体量主播薇娅同样因偷税漏税被罚13亿。
坐镇杭州的两大头部主播接连因事故停播,仿佛点燃了导火索。今年年初,外界对杭州直播电商的“担忧之情”更盛。
2022年1月,“杭州网”发文称直播电商行业野蛮生长时代终结,取而代之的是行业洗牌和规范发展。杭州能否在广州、上海等同样发力直播电商的城市中继续保持先发优势,仍需时间的检验。
3月,“电商头条”的一篇名为《一大批直播电商倒闭!原因和薇娅有关》的文章提到近期多位直播公司的老板不约而同地发布转租直播场地、转手直播器材、转让旗下主播的合同等信息,表示杭州正有一大批直播电商公司倒下。
4月,“新婉儿”的《直播电商抛弃杭州》中,更将杭州比喻为一座需反思的围城。在杭州倒下的直播电商公司也有了更直观的占比,文章列举微博粉丝百万以上的财经博主等用户的内容,显示“杭州直播工作室倒闭90%”“杭州直播电商已不适合个人创业”。
一边是直播基地的热火朝天,一边是多方的持续担忧,到底哪一面才是杭州直播电商的真实现状?
“倒闭90%是真的,但身边没有”
2019年来杭州创业的赵恺,如今是一家MCN机构的负责人。他公司合作的红人中,不乏张纪中夫妇、曹颖等明星。
当小巴提及杭州直播电商公司倒闭的事件,他表示并未感到危机:“没有感到不好,我们和我们身边的MCN机构,没有倒闭或者做不下去的情况,大家都活得很好。”
停顿了几秒,他笑笑继续补充:“我们都属于行业中腰部甚至是头部机构,如果连我们都不好了,这个行业也不行了对吧?当然网传近90%的小型直播电商公司倒闭也是真的,这个行业的二八定律很明显,做直播电商多少需要有些底子。”
2019年,在疫情推动下,直播电商迅速爆火,结合产品、物流发达的产业经济带、杭州优惠政策,越来越多网红主播、机构、品牌及平台入驻杭州。
当直播电商正值风口,MCN机构的底子是红人IP带来的流量。
但随着头部主播频繁出现事故,令平台及品牌方意识到依赖巨额流量的风险,开始重新思考直播电商的合理路径。由此,直播电商机构进入了“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不断增加自己的“重量”,以期不被激流冲走。
赵恺的思路是加强对直播电商全链路的把控能力。他投资了一家女装类直播电商公司,全年直播销售额15亿元。他又建立了一个短视频直播机构联盟,会员涵盖粉丝量一亿以上的MCN机构、单场直播观看人数上千万的红人以及有带货需求的企业家。
“MCN机构+机构联盟+直播电商公司”的模式,贯穿前期产生流量,中期供应链需求对接,后期流量变现整个运作流程,这或许就是赵恺及身边同类机构活得很好的原因。
再看引爆本轮担忧的谦寻,在薇娅风波后,开始了更广阔的业务线路布局。我们从薇娅团队前员工胡迪处了解到,偷税漏税事件后,团队工作量减少,停摆一段时间后重新调整业务模型,扶持其他主播开辟新市场。与此同时,也在布局供应链、店播、主播培训等相关业务。“直播带货已经成为营销的重要环节,它不会消失。所谓消失的公司,只是优胜劣汰的产物。”胡迪说道。
今年2月,浙江省电子商务促进会发布《浙江省2021年度直播电商发展报告》,报告数据显示,2021年1—10月,浙江全省直播电商交易额6092.1亿元,占全国总额的28.4%,位居全国第一;而杭州直播电商交易额达5024.8亿元,占全省直播电商交易总额的82.5%,规模居全省第一,同比增长128.4%。
也就是说,杭州在交易体量上,仍可称之为直播电商第一城。那么,倒下的90%究竟是谁?
尴尬的代播公司
在最初引发担忧的那张截图中,倒掉的实际上是“杭州直播带货的服务商”。
直播电商服务商大致可分为三类:如赵恺般手握红人IP的MCN机构、淘宝联盟这类整合供应链,链接商家和MCN机构&KOL的供应链服务商以及代理品牌直播电商业务的代运营服务商。
此次杭州直播电商的“重灾区”,便是最后这一类服务商。
直播电商代运营服务,以代播为主。麦子告诉小巴,这类公司在业内被称为代播公司,即为品牌直播时提供运营、主播、场地等服务的直播服务商。在直播三要素:人、货、场中,代播公司负责人和场。
2019年,淘宝将淘宝直播变为独立App,为摆脱头部主播影响,对于淘宝店铺有了直播要求,尤其是大的品牌商家,必须保证一天6小时以上的开播时长。
由此,淘宝将直播电商推入2.0时代。据淘宝数据显示,2019年淘宝直播中90%的直播来自商家,10%的直播来自主播/网红。70%的交易额由商家直播贡献,30%是来自主播/网红带货。
对品牌方来说,场地费、人员投入以及效果在开播之初都无法预估,代播公司应运而生。据“电商在线”报道,自2019年“618”大促过后,淘宝直播上的代播服务机构从0增加到了200多家。
若单从服务业务来看,代播公司似乎与MCN机构类似,品牌方提供产品,服务商进行直播带货。但实际上,二者却有着巨大的差异。首先,是主播的可替代性。
无论是日前因健身直播成为顶流的主播刘畊宏,还是已销声匿迹的薇娅、雪梨,他们在各平台直播所使用的账号,均为MCN机构所有的“个人账号”,商家选择与其合作,也是看中了机构红人主播的个人影响力。
而据麦子介绍,绝大多数代播公司直播所用的账号,均为品牌方账号,主播更像是品牌方通过代播公司雇佣的导购,个人影响力几乎为零,可替代性强。
由此,便带来了第二个差异:收入。
手握粉丝流量的MCN机构多以主播“坑位费+佣金”的方式进行收费。
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主播的坑位费在几万到十几万不等,佣金分成比例一般在20%—30%,像罗永浩在抖音的首场带货直播中,坑位费高达60万元/件。
反观代播公司,大多以“服务费+时薪”作为其收费模式,即几万元的服务费+直播每小时几百到一两千元不等的费用。“之前待过的一家代播公司为了争一个大品牌,时薪报到300块,简直不要命了。”麦子说道。与动辄上万元的坑位费相比,代播公司几百的时薪,显得如此“亲民”。令其成为品牌方试水直播电商的首选,但也使其陷入尴尬境地。
“如果直播效果好,品牌可以跟代播公司签长期合作,一年就有几百万。”麦子停顿了几秒补充道,“但是真的做起来了,品牌方干嘛不自己接手?杭州直播电商从业者这么多,主播又不是网红,团队很好组的。”
通常代播公司与品牌方签订的直播协议,最短周期为1个月,直播效果欠佳,一个月后终止合作撤出的品牌方也不在少数。
而薇娅事件,成为压死代播公司的最后一根稻草。
“比如我昨天播的护肤品,投流假设一万,但其实卖货最多也卖一万的样子。为了拿到佣金,有些代播公司会跟品牌承诺销量,没到的就得自己刷单。如果每天有十个直播间在播,那就都得砸钱。”麦子表示只有极少数品牌方会自己承担投流费用,至于刷单,则是业内公开的秘密。
然而,刷单的销售额,是会显示在公司流水上的,因此,在计算税费时,这笔虚假订单也会算在其中。自薇娅事件后,浙江针对直播电商偷税漏税打击力度加大,以前依靠皮包公司避税的方式行不通了,补税令本就收入少支出大的代播公司雪上加霜。
据企查查数据显示,2020年杭州市“直播服务”相关企业注销量为341家,2021年注销吊销量近600家。而截至2022年至今,杭州相关企业注销吊销量已达去年全年的一半。
事实上,代播公司为品牌方直播提供场地及专业“导购”,收取劳务费的商业模式,正符合如今直播电商回归职业化、流程化的趋势。据艾瑞咨询预测,2023年企业自播占比将接近50%。
庞大的市场需求正在赶来,但这也注定了代播不是一门“一夜暴富”的生意,作为店播过渡期的产物,代播公司的生存路径始终未走通。
癫狂过后
逃离北上广的年轻人,找到一座新城。
罗永浩的“交个朋友”、歌手胡海泉旗下的MCN聚匠星辰、抖音顶流网红“大狼狗郑建鹏&言真夫妇”“多余和毛毛姐”等红人机构先后入驻杭州,政府、平台、品牌、网红、打工人的“卖力宣传”,让越来越多人相信,杭州就是继北上广之后的又一座梦想之城。
据公众号“泽平宏观”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2020年,杭州人才中来自上海和北京的合计占比15.8%,大批资源、人才“逃离”北上广,涌入杭州。
彼时的杭州直播电商,或许同样适用于电影学者大卫·波德维尔对香港电影的评价:“尽皆过火,尽是癫狂。”
“直播公司都是被我们主播割韭菜的。”麦子从业3年,据她表示,自己合作过的杭州直播电商公司不下十家 ,底薪也从八千涨到了近三万。
薪资涨幅大、从业者稳定性差,似乎成为直播电商行业通识。“杭州电商人才确实鱼龙混杂,主要是有钱人太多了,大家都想用钱解决时间成本问题。”赵恺说道,“直播电商在杭州做起来之后,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老板来杭州开公司,大厂培养出来的直播人才跳槽出去薪资就翻倍。”
有半年经验的主播,底薪就可达1万,场控、中控的底薪也普遍在6K左右,至于运营,赵恺表示,其联盟机构曾面试过的一个抖音直播电商运营,底薪要求5万元。
水涨船高的人力成本,直播所需大面积场地带来的高昂租金,一直是直播电商公司身上的重担,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其中一部分如今被压垮的局面。当风渐止,被欲望、梦想吹到杭州的人才,终将落回地面。
与麦子相识于一年前,彼时她的女儿刚出生。原以为她会换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方便照顾孩子。但再次见面时,她只是换了新的直播公司,嗓子也更加沙哑:“底薪涨到3万就没再往上了,现在直播公司也冷静,不过有能力的主播还算赚钱的,养孩子开销太大。新主播看着高薪想入局,就难了。”
麦子更卖力直播来争取每晚8点到12点的黄金时间,这样至少每天有一个时间段她和女儿没有时差,可以多陪陪孩子。
5月7日,薇娅助理琦儿以主播身份在抖音开启直播带货。无论是此前的“蜜蜂惊喜社”还是如今的琦儿,失去薇娅的谦寻,虽然少了头部IP的光环,但仍有完善的供应链和运营团队可用。
狂热过后,直播电商或许迎来了当下最好的结局,变成了一门常规、需要稳扎稳打的普通生意。
注:麦子、赵恺、胡迪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