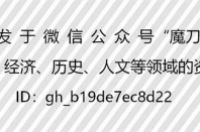
公元前336年,大思想家孟子来到魏国,面见当时的梁惠王。梁惠王久仰孟子大名,他原以为对方会和他讲一番如何富国强兵的道理,就像今天政府聘请的那些战略顾问那样。
“先生远道而来,有什么利于我们国家的建议吗?”梁惠王问。
没想到,孟子非但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还反驳了梁惠王,“王何必曰利?”孟子说到,“我这里只有仁义而已,如果国君天天想着什么对我国家有利,那么士大夫和老百姓也会跟你一样想,如果人人都只为自己考虑,国家可就危险了!”
这是《孟子》第一章里的经典对话,每个中学生都读过。换到你做梁惠王,你会对孟子的回答满意吗?我相信不会,你大老远请人家过来,不是为了听这些大道理。别忘了,那可是群雄纷争的时代。如果我是梁惠王,我一定会反问孟子:“您叫我仁义当然可以,但如果别人拿刀架在我脖子上,我能劝人家对我仁义一点吗?”
1/5 义利之辨与囚徒困境
这便是我第一次读到《孟子·梁惠王上》的感觉,当时孟子给我的印象,就是个满嘴跑火车的道学先生。而他与梁惠王的这番对话,则开启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义利之辨”的序幕。
以前我总觉得孟子很迂腐,他周游列国,一生不得志,其政治主张始终不被诸侯们接受,这和孔子的经历非常相似。但仔细想想,在战争岁月,让大伙抛开切身利益,空谈仁义道德,谁会听你的呢?
但今天回过头来再读这段对话,我有了新的发现,不得不承认,孟子有他的伟大之处。
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如果每个人只为自己着想,那到头来每个人都过不好。无论在国家内部还是国与国之间,类似的悲剧都会发生。
设想你现在生活在一个部落里,你的部落要去征服其他部落。打仗需要士兵,士兵得从部落的所有成年男性中挑选,你也是其中的一员。请问你的最优策略是什么?
倘若你是个“聪明人”,最好的办法是打断自己一条腿,这样就不必上战场了。等军队凯旋归来,你再分享战利品。别人做出牺牲,你摘现成的桃子。这在经济学上叫做“搭便车”。
问题是,假如人人都“搭便车”,整个部落就没人当兵了,一旦别的部落打过来,你们就只能束手就擒。所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就实行了征兵制,每家至少出一位壮丁,以组成常备军与外国作战。个别国家甚至规定,有的家庭必须世代为国家提供兵源,未经允许,不得随便转业。
除了“搭便车”以外,还有个普遍的治理难题叫“公地的悲剧”,它是在1968年由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提出的,哈丁想象了这样一个场景:有一座牧场,上面水草丰美,你是周边的牧民之一,牧场的面积有限,但每个牧民都想上去放羊,结果会怎样呢?可以想象,用不了过久,牧场上的草就被吃光了。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乱局,也可视作“公地的悲剧”的另类版本。各国之所以兵戈不息,是因为大家都想争夺公共资源,这些资源包括山林湖泊,农田矿山,甚至还有优秀的人才。从各国自身的角度出发,最优策略是把所有资源都抢到手。但每个国家都这么想,天下就永无宁日,公共资源也得不到有效利用。为什么呢?因为你今年抢了一块地,明年就可能被人夺走,你还会在上面苦心经营吗?你只会竭泽而渔,反正这个便宜不能让别人占了。
以上这两个故事告诉我们,在社会中,自利行为对个体是最优的,可对于整个群体却是毁灭性的。最终甚至会造成“人人为己,人人遭殃”的结局,这就是著名的“囚徒困境”。
2/5 对自利行为的制约
因为“囚徒困境”的存在,儒家思想对自利行为持批判态度。在古人看来,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始终存在无法调和的冲突,到了某个临界点,两者就会陷入此消彼长的关系,这个社会离天下大乱也就不远了。
对此,儒家的解决方案有两种,一种是“克己复礼”,借助自我修养与道德约束来压制个人欲望。还有一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希望通过强有力的政府来维持社会秩序。
不止中国的儒家,在西方世界,曾经也盛行着对欲望和自利行为的敌视。典型代表就是对待商人的态度。不错,除了中国,西方人也有歧视商人的传统。在古希腊,经商被视为不光彩的事情,贵族以做生意为耻,手工业者和商人连公民资格都没有,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奴隶没什么两样。
到了中世纪,这种倾向就更为明显,神学家奥古斯丁认为,对金钱与财富的贪婪是堕落的标志。他将物质欲、权力欲和性欲视为人类的三大罪恶。很多人都知道《圣经》里的那句名言:“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天堂还容易。”形象地说明了基督教对商人的态度。
儒家认为,若社会放任个人追逐私利,整个社会就会分崩离析。古今中外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以古希腊为例,希腊人曾为他们的民主政治和自由主义而自豪,但自由的反面就是放纵,希腊耗尽了自然资源,道德开始败坏,政治秩序也日渐混乱,最终被比他们更具集体主义精神的罗马人给打败。
与儒家持类似观点的,是英国哲学家霍布斯,霍布斯假想了一种“自然状态”,在自然状态下,人摆脱了社会约束,就会像野兽那样陷入自相残杀,从而导致“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为了避免这种状况发生,就需要一个集权国家来垄断暴力机器,霍布斯称之为“利维坦”,霍布斯认为,一个强大的第三方是遏制个人欲望泛滥的前提条件,这个第三方只能由政府承担。
从中国儒家、中世纪基督教到近代的霍布斯,他们对人性都持比较悲观的态度,要解决个人与社会间的矛盾,要么诉诸道德与宗教,要么求助于集体主义或强制管理。在这些思想家的语境里,欲望即便谈不上罪恶,至少也是有损社会利益的,一个社会无论如何都不能鼓励逐利行为。往小处说,这会腐蚀淳朴的民风。往大处说,这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
然而,仅仅依靠压制,并不能彻底消灭欲望,因为那是我们的生存本能。再往前想一步,即便我们的确把个人欲望给压制了,社会真会变得更好吗?很遗憾,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人类始终没找到让两者实现共赢的最优解。
3/5 找到破局点
1776年,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出版了他的《国富论》。如今,《国富论》被视为经济学的里程碑著作,但很多人忽略了这本书对人性的解读,从某种意义上,这才是斯密最最了不起的地方。
提起《国富论》,大家马上会想到“看不见的手”,斯密有句话被大家反复提及:“我们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商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这句话的特别之处在于,斯密首次肯定了自利的价值。不仅如此,斯密还说,我们平时所得的一切,都是别人“自私”的产物,对他人如此,对自己也一样。没有金钱的激励,就没有大规模的物质交换,我们绝大部分人只能过自给自足的生活。社会得以有效运行,靠的不是大家的无私奉献,而恰恰是每个人的利己之心。
《国富论》不再将个人利益置于社会利益的对立面,它开始替利己主义正名。更重要的是,亚当·斯密已经在个人利益与社会繁荣之间找到了破局点。
斯密的学说打开了个人欲望——这个道德家眼中的“潘多拉魔盒”,还提出了一个关键假设:如果人类利己心不被刻意压制,而是充分释放,只要我们能把它引到一个正确的轨道上,每个人就会比原先活得更好,整个社会都会因此而进步!
而这个正确的轨道,就是自由市场主导下的商品经济。
其实在早些时候,另一位英国哲学家曼德维尔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曼德维尔写了一本书,名叫《蜜蜂的寓言》,在书中,曼德维尔就大胆地提出,自私自利与公共利益并不矛盾,不仅不矛盾,还有助于公共利益的改善,增进全社会的福祉。
《蜜蜂的寓言》的出版时间比《国富论》早了半个多世纪,在当时,曼德维尔的观点不受待见,遭到了欧洲学术界的不断抨击,也许这就是思想先驱需付出的代价。
放到今天,你会肯定觉得这些思想稀松平常,这不就是我们生活的常态吗?市场经济不就是这回事吗?那我们不妨再问一句,如果这个道理如此显而易见,为何过去的哲学家没有想到?难道他们都蠢吗?
所以,背后的事实没有这么简单,《国富论》首次提出了市场的价值,但斯密没有告诉我们的是,“市场”本身并非天生就存在于人类社会。换句话说,所谓“互惠互利”的市场经济,不是人们自古以来就拥有的,它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
4/5 市场秩序的建立
为了理解这一点,让我们回到亚当·斯密之前的年代,看看人类过去的经济活动是怎样展开的,以及为何我们的传统思想总是排斥个人利益。
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提出了近代市场经济诞生前的三种经济形态。第一种是互惠型,比如原始社会的物物交换,不同的部落结成一个政治同盟,定期将贵重物资赠送给对方,中国古代的朝贡体系与此非常类似。不过请注意,这种互惠关系不同于今天的市场经济,因为它的主要目的是建立稳固的政治合作,无论是交易的规模还是频次,都无法与近代市场经济相提并论。
第二种形态是再分配,这在世界各国的古老帝国中都很普遍。所谓再分配,就是拿出国民收入中的一部分给另一部分人使用或消费。比如在中国,古代政府会建立粮仓,以便在灾年救济民众。当然,再分配最大的受益者是特权阶层,比如到了明朝后期,社会上存在大量的皇族后裔,他们被分封在小小的土地上,不事生产,专食皇粮,成为社会的寄生虫。
第三种形态就是自给自足,早期人类文明都经历过这一阶段。中国的小农经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领主,都是这种经济模式的代表。自给自足最显著的标志,是只为使用而生产,我用多少,我就做多少。自给自足环境下不可能有精细的分工,家庭成员往往身兼多职,生产效率极度低下。
以上这三种经济形态,都曾长期存在于人类社会,它们是在生产能力低下,市场规模较小的背景下产生的。因此,它们都受制于社会的存量,一旦对存量的消耗大于存量的增长,整个经济体入不敷出,社会就会濒于崩溃。
从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到中国历朝历代的兴衰,从根本上都遵循着这一规律,社会初期,生产力蓬勃发展,国家欣欣向荣,可到了中后期,随着人口增长与特权阶层的膨胀,对存量的消耗渐渐增加,如果再遇到天灾或者外族入侵,政府财政吃紧,久而久之就会形成恶性循环,很多大帝国就是因此而灭亡的。
在近代市场经济出现以前,人类文明无法走出这个困境,因为长距离的贸易网络尚未建立,国与国之间无法通过大规模的商业交换发挥比较优势,在各自的文明圈里,大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
在严重依赖存量的经济体中,就会出现一种批判私欲,抵制享乐的文化。我们不难看到,全世界很多古老的宗教,都是奉行禁欲主义的。因为有限的存量经不起过多消费,当一个社会的上层出现奢靡之风时,往往以蚕食或掠夺大部分人的收入为代价。所以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才会说:“一个国家生于禁欲,死于享乐。”物质匮乏的年代,利己主义就是洪水猛兽。
5/5 企业家与市场经济
那什么是市场经济呢?前面已经说过,仅仅有了交换,不足以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市场。市场是一种特殊的制度设计,不过,它既非统治者自上而下的安排,也不是全靠人们自发地形成。确切来说,它是两者结合的产物。
卡尔·波兰尼认为,市场经济的物理前提是大范围的远距离贸易。只有市场足够大,经济互利才能触达到每一个人,而不是少部分人。
但光有这个前提还不够,为何近代欧洲能够崛起?很多人会想到大航海时代的殖民掠夺。的确,远洋贸易帮助欧洲国家建立了全球性的贸易体系,但这个体系不是免费的,它需要高昂的成本,从过去的西班牙和英国,到今天的美利坚,这些海上霸主都是通过军事实力来维持世界秩序。因此,所谓的全球市场,并不是大家心平气和坐下来商量就能搞定的,它其实是霸权的衍生品。
还有一个因素不容忽视,那就是金本位。这涉及到金融史的话题,本文不做赘述。简单来说,金本位能够将不同的货币放在统一的尺度下衡量并兑换,这使得跨地区的贸易大大方便了。设想一下,在物物交换的年代,人们根本无法准确衡量物资交换的具体价值,统一标准的出现,不仅意味着交易成本的降低,更有助于凝聚商业共识,金本位是市场经济得以运行的制度保障。
市场经济是经济与权力运行的共同结果。它以价格为杠杆,增进了资源的流通,使人类打破了过去的存量限制,将区域间的存量给盘活,使每个人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激发出来。你想获得更多的财富,可以不靠偷,不靠抢,不靠特权的庇荫,而是正大光明地给别人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你为社会创造了多大的价值,社会就会给予你多大的回报。
当然,除了经济回报,市场经济也离不开竞争。为了让资源更有效地聚集和流通,市场就需要企业家。市场的规模越大,企业家作为调配生产要素的枢纽才显得越重要。只有当分工产生的专业化水平越高,企业家的创新才会更有价值。
这也是为什么,人类一直到19世纪末,当西方的全球贸易与大规模工业化初见雏形,我们的思想家才开始赞颂商人,崇拜企业家,从马克斯·韦伯到熊彼特,商人不再是自私自利的吸血鬼,而是成了勤勉、克制、责任感乃至创新精神的代言人。
一个社会推崇什么,反对什么,往往是由它的生存模式所决定的。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看清历史对我们的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