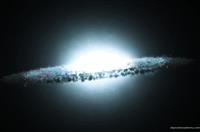吴:《读书》这几期,上海的朋友相继提出了人文精神的失落和遮蔽等问题。今天,我们江苏几个学人聚谈,看看能否将其中一些问题深化一下。我总觉得,失落也好,遮蔽也好,这些只是描绘了人文精神在中国的现状,但追问一下,这里面也暴露出我们过去的人文精神理解上的问题。换一种思维方式也可说,正因为我们过去追求的人文精神有问题,所以今天失落了,这样我们今天面临的就是建设新的人文精神这一空前难题。
另外我注意到,中国儒家的人文关怀和西方近代的人文话语有个特点,那就是她们都成为过社会的主流话语,在本文化系统内占据主流。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抛弃了儒家的一套人文关怀,所需要建立的人文价值是否也应该力争主流化才可能?反过来,本世纪西方的人文意识之所以在中国总是处在边缘位置,被排斥,在实践中又很难完成对儒家传统的否定,是否也说明既定的西方人文话语并不完全适应中国?
干:我觉得人文精神在当代,主要体现为知识分子的一种生存和思维状态。人文精神的危机说到底还是知识分子的生存危机。具体地说,多年来我们人文工作者始终是以“参照”作为生存依据的。“五四”时期,鲁迅、李大钊、陈独秀这些新文化的先驱,对儒家传统采取了激烈的批判,所参照的西方人文价值体系是非常明显的。民主、自由、博爱这些价值规范,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冲突当然是很尖锐的。后来由于种种特殊情况,五四的这种西方人文传统被中断了——这个“中断”也许已经说明了一些问题。直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又想恢复五四的这种人文传统,但是现实又非常残酷,崔护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忽然成了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写照。原来中国知识分子千呼万唤的那套西方人文传统,在西方也面临了危机,面临许多不能解决的问题,说白了,就是西方人文价值传统在崩溃。作为以“参照”为生存方式的中国知识分子,当然也会感到陷入一种迷茫的困境。而现实的问题,现实的困境,又在加剧着我们这种迷惘。于是我们便一下子找不到了自己的生存状态。简单地说发扬中国传统人文精神,或者对西方已有的人文精神认同,恐怕都不能解决我们的困境。“寻找新状态”才是九十年代中国人文科学工作者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一个很迫切、很重要的话题。
费: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太重现实功利,太重集体原则,太容易媾和认同,缺乏形而上的批判与否定精神。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很难找到自己的个人位置和独立话语,这样,也就谈不上对人文精神有自觉清醒的建构意识。
回顾中国历史中人文精神的发生发展过程,不论儒家朴素的人道主义思想,还是道家对个人生命的重视,从中都不难发现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轨迹。但悲剧在于:本来人文精神应该是与统治阶级的政治话语相对立的,可一旦统治阶级将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纳入其集团政治话语时,无论儒家型知识分子,还是道家型知识分子,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统治阶级公开的或潜在的“合作者”,人文精神也就在这个时候被阉割、被遗置了。所谓“儒在庙堂”,就是儒家人文精神被同化的一种说明。当年孔子周游列国时那种“仁爱”理想,有着明显的反对国君暴虐政治的人道倾向,但到了汉代“独尊儒术”,儒学被请进“庙堂”,成为统治阶级的主流话语以后,这种“仁爱”理想的性质就完全变了;而“道在江湖山林”,虽说表面上站在与“庙堂”相对的位置上,可究其实,人的个性自由对现实政治的超越作用,已不复存在,“山林”更多成为“庙堂”的补充,历代许多自认为老庄之徒的文人,“身在江湖,心在魏阙”,就是证明。这不仅是历史,也是近代的现实。从五四以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虽说曾激烈地抵制过,拒绝过,但最终还是没有逃脱传统知识分子同样的悲剧,因为他们从根本上说并没有越过儒与道的历史思路。事实提醒我们,人文精神只有与世俗的社会功利需求相对抗,才能得到彰显和阐扬。要在这个意义上,强调知识分子对于承担人文精神的责任;也要在这个意义上强调知识分子的生存选择和价值立场。
彬:统治阶级需要儒家经世致用的一面来维系社会,却不需要凌驾于统治阶级之上的、能检验合理与否、正义与否的“道”,或者对这个“道”进行符合自己统治目的的解释,这种阉割和被解释的东西,可能便是人文精神。明代朱元璋号称“以孝治天下”,但他将《孟子》中的“君视臣为草芥,臣视君如仇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删掉,且声称如孟子在世,一定诛之,就是一例。反过来,有气节的知识分子又始终是在抗争的。明清之际的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就极力张扬一种可以检验制约君权的尺度,极力寻找一种以道统对抗的合理性。如果说中国也曾有人文精神的话,那么这是否就是了?
至于儒家的人文关怀为什么会被统治阶级阉割,我想这是否与儒家哲学缺少西方意义上的超验价值有关。我们重建人文精神,当然不会与西方人文精神完全相同,但也必然与西方人文精神有相同之处。各个文化和民族虽然有自己的人文阐释,但似乎也应该有一种“家族相似性”。
吴:我总觉得汉末儒学崩溃,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神学”受到知识分子的普遍怀疑,是第一次文化大发展的好机会。可惜这个机会中国文人没有利用好,才导致隋唐之后,宋明理学(新儒学)又成为社会政治的主流话语。比如:东汉末年的范滂,已经对儒家的善恶观提出了“谁汝为善?谁汝为恶?”的质疑,但这种质疑的结果,依然没有摆脱东汉郭泰不隐不仕的矛盾,心灵上落得个“遂散发绝世,欲投迹深林”(《后汉书》卷四十五《袁宏传》)的空茫境地,最后走不出何晏、王弼的“道本儒末”的思维模式,以及阮籍、刘伶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生活模式。也因此,道教意义上的自然性生命和无为而不为的人格,能否真正构成对儒家的否定,一直是可疑的。后来郭象建立“三教互补”,二程朱熹建立宋明理学,只不过是用事实证明了中国知识分子以道反儒的失败罢了。
我还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魏晋以后我们对印度佛学的汲取,很相似五四以后我们对西方话语的汲取;佛学后来虽然以禅宗的形象在中国站稳了脚跟,但是它和道教一样,最后还是被统一于儒家的思想模式里了。这个悲剧同样是一百年来我们讲西方人文话语的悲剧。在找不到对儒家更好的否定方式之前,儒家可能只能不断地被后人重新解释。这大概就是“新儒学”也成为历史的缘故。
干:上面几位提到的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在文化传统、文化系统的意义上,是可以成立的,但我总觉得这种人文精神更多的还是体现了一种文人精神。比如方孝儒那种不怕灭九族的气节,与统治阶级不合作的大无畏气概,体现的是一种文人精神,与我们所渴望的人文精神,不是完全等值的。几千年来,文人精神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生存依据,作为一种捍卫知识分子人格和尊严的武器,确实有过非常积极的一面。但是它也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始终具有“代言”、“依附”、“工具”的身份。不是代圣人言,就是代自然言,不是依附这个阶级阶层,就是依附那个集团和体系,知识分子在社会中始终没有独立存在过,找到过真正的自我。儒家哲学为什么会被统治阶级利用?原因之一恐怕也在于此。道家讲的人格独立和生命自由,与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角色去独立地思考,恐怕也不是一回事。
另外应该提醒的是,由于我们今天处于一种半工业半农业的社会历史转型期,因此我们应着眼于当代来谈新的人文精神状态的建立。今天的知识分子普遍丧失了“代言”的身份,也许正是寻找新的叙事可能、叙事权利的契机,如果知识分子没有话语权,没有独立生存的价值,人文精神的再生,搞不好还会是文人精神的回归。我甚至想,今天谈人文精神的建立,不大可能再会是一个普遍性原则,不可能成为人人信服的宗教,也不太可能成为社会新的经世致用的哲学与价值体系。某种意义上,今天所需要的人文精神,可能只是知识分子话语的一个执著的世界,一个与当权者无关甚至在目前也可能是与民众没有多大关系的独立存在。
费:今天知识分子的状态,无论是生存状态还是思想状态,都不比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好多少,更不必比五四那批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知识分子了。我们比什么时候都更加虚弱,更感到危机。重建人文精神,从最切近的目的上说,是今天知识分子的自救之道,是寻求再生之道。因此,人文精神在今天的“可能性”,不仅仅是学理上的“可能性”,更主要是指“实践”的“可能性”。我这里指的实践性主要是指话语操作上的,与《读书》第三期王晓明他们所说的“个人的实践性”还不完全一样。比如魏晋玄学对儒学的反动,明代个人性情对世俗生活的解放,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用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抨击传统文化,都有很强的操作性。今天谈重建人文精神,我们应该操持一套怎样的话语,话语标准和对象又应该是什么,……这些都是很具体的实践问题,困难之处也就在这儿。根据刚才我们所谈,好像回到被五四抛弃了的中国文化传统,到中国传统文化人格和学术生活中去寻找再生力,似乎很可疑。而回到五四的思路上,把现代西方人文哲学那套话语拿来用,也可能有一个久虚的人,你越补越虚的问题。存在主义也好,海德格尔也好,即便是好药,能治西方的病却不见得能治中国的病。再加上我们自己,一方面自命要负起当代人文精神重建的使命,另一方面又无法克服那种来自历史深处的“合作者”心理障碍……这就使我们今天的人文话语对象,要比预想的复杂得多。
彬:“新儒学”和我们刚才所说的中国传统里固有人文精神,其实不是一回事。强调这一点很有必要。新儒学最大的问题,可能还是在“心性本体论”方面,和传统儒学没有什么差异,还是一种“内圣外王”的思维模式。我们今天谈人文精神的失落、遮蔽、重建,必须明确一个前提:传统中有无人文精神?如果在中国文化传统里根本找不到今天我们所需要的人文精神,那么只能说传统中没有真正的人文精神,也就谈不上失落或遮蔽。但如此一来,重建又以什么为依据为参照呢?全盘西化式的人文精神在中国又行不通,最后可能我们还是必须从传统中寻找人文精神的原素。比如,儒家虽有人文精神但却始终不够昂扬,原因在于儒家思想是一种过于世俗的思想,儒家始终强调知识分子要实现自己的价值就必须从政,将“治国齐家平天下”作为理想,这就极大地限制了人文精神的发展。中国始终没有“上帝的事情归上帝管,凯撒的事情归凯撒管”这样一种西方传统,没有超验和绝对神圣的价值依据,所以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往往很脆弱,经不起冲击。但是要今天的中国人接受西方式的绝对神圣的宗教精神,可能也很难。但我们能否考虑在现实和入世的层次上设计一种绝对的价值坐标呢?在“入世”的“入”上做一点文章呢?
吴:我觉得既是反思过去人文精神的问题,可能还有必要回顾一下近百年对西方人文精神的理解与追求。我是这样理解的:每种民族都会有人文关怀的冲动,但不同时代,这种关怀的结果是不同的。西方近代人道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差异正在这里。我们所处时代的特殊性,也决定了我们不可能挪用西方特定时期人文关怀的“结果”。比如西方的基督教精神,绅士风度,淑女风范,我以为都不适合今天中国的人文风范。西方近代所讲的人格尊严、个性解放,也都是对人的普遍内容的关注,在今天我们这个无序和茫然的社会环境下,也可能失去了应有的意义而显得陈旧。特别是人格和个性这些范畴,很容易被刚才所讲的中国“文人精神”所同化,被道家的人格和性情所同化。就像“理解”这个词,在西方现代哲学中本有她特定的前提和内涵,但我们一挪用,就成了“原谅、慰藉、同情和妥协”的代名词。即便西方现代哲学所说的生命的痛苦体验,我觉得在我们的表述中,已经混杂了生存性挣扎、民族存亡的成份,甚至和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某种原欲性文化,可以直接沟通起来。“生命”于是便成了一个很含混的概念。
干:人文精神在今天何以成为可能,主要表现为知识分子叙事的可能和必要。“人”,主要体现在知识分子的精神上;“文”,主要体现为知识分子叙事的可能性上。作为人,他的再生与我们整个社会知识分子力量的存在有很大关系。人文精神主要就体现为知识分子独立叙事的程度、独立叙事的力度,
看它能否和物欲横流的社会划开界限。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感到一种困境,就在于没法和这个世界划开界限,于是也就找不到自己的状态。知识分子在叙事时必然会混淆于其他社会角色,被其他的社会声音所淹没。知识分子独立叙事这样一种存在是人文精神得以存在的先决条件,否则人文精神的重振就是一句空话。知识分子也必然会重新依附到某种价值规范中去,某种既有的权力机构当中。
另外应该强调的是:知识分子作为一种叙事人预设人文价值有一个重要特点:即它是否定性的、批判性的。人文精神不是指导性的,它是无实施性的。如果把人文精神变成一种可以实施的蓝图或章程,那么人文精神就贬值了。为什么儒家学说在中国衰落了?因为它后来变成了一种经世致用的规范、一种章程,所以人文精神就死亡了。就像知识分子一样,一方面在科学领域中对社会有工具性的作用。但在人文精神领域,知识分子必然应作为社会的否定力量存在。
吴:我由此想到《读书》第三期上,上海的朋友们提出的人文精神的普遍性和个人实践性问题,我觉得通过对“否定”的强调,似乎可以将两者统一起来。如果我们将人的诞生理解为人是在对自然物的否定中成为可能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显然又面临着一个否定人所创造的物的境况。人文精神丧失的时候,也就是最需要这种否定的时候。这种否定有一个特点,就是其结果必然是一个个体性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把人类的诞生理解为宇宙中的一个个体,不同的文化文明理解为这种否定的结果(个体)。所谓人文精神的普遍性,就是指不同的文化和民族,其实都暗含着类意义上的否定性,所谓个别性,就是指这种否定的结晶,肯定又是一个殊类。我觉得强调这种否定,对我们今天反对西方文化霸权(或东方文化霸权)是有意义的,对我们将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型态,可能也是有意义的。进一步说,知识分子能否找到自己独立的存在,每个人是否能在普遍的生活方式(如下海,如以吃喝玩乐作为生活方式)中找到自己独特的体验性内容,是否都应与这种否定意识有关?
再一个,应该补充的是:每一种文化在成熟的时期,都容易丧失这种否定,中国文化在宋明理学时期(或许更早)就丧失了,西方文化在今天也可能丧失。可否说,之所以整个人类有人文危机,是否可以认为人类历史今天已经达到了一个成熟的状态呢?我觉得日裔美籍学者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个人》,在这一点上是能给人启发的。
费: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在儒学那里也好,在庄玄那里也好,都有很浓重的世俗化成份。后来的佛学虽说是宗教,但一到中国就被充分世俗化了。由于有这种局限,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的价值位置的选择从来就很被动,总是在世俗的文化中周游循环。我们现在讲知识分子要主动回到“本位”,可这“本位”在哪儿?他能否超越世俗世界中某种集体的代言人和附庸者的角色,成为一种形而上精神的勇敢发言者?我感到困扰似乎很大。
现在,确有不少学者从“庙堂”等处撤下来,回到书斋从事纯学术活动,但在“书斋”里是否就没有了失去“本位”的茫然感了呢?我总觉得,这还是一种儒家和道家交替互补的文化循环。庙堂与广场,总是与经世致用相关,而书斋,则与山林一样,是道家退身韬晦的又一种策略。清代乾嘉学人们的学术道路,就是如此。当然,“乾嘉学派”以及在中国所有的书斋文人,在学术上的作为自有其个人价值,对人文历史也有不可抹杀的贡献。但“学术”在成为个人生存方式和理由的另一面,有可能消解知识分子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以及由这种关怀产生的对现实的否定与批判。单纯回到书斋的可疑性就在这里,至少在今天的时代环境下是如此。因此,讲知识分子个人的学术活动在什么样的层面上才能构成知识分子的“本位”,可能更为重要,否则,一个人什么也不关心,就关心他的书本,他大概只能成为一种人文知识的留存者,而不是人类的关怀者,人类情怀对现代知识分子来说,应该大于学术。
彬:说到这里,我想到了宗教问题。人类历史上,对人类社会、对尘世、对人自身最坚决、最深刻、最彻底的批判与否定,往往是来自宗教精神。人文精神不一定就体现为宗教精神,人文价值不一定就体现为宗教价值,这在中国尤其不可能。但这二者之间绝对是有联系的。人文精神如果理解为批判性与否定性,那么人文学者、知识分子则必然站在现实的对立面上,而若站在现实对立面上,则必然要有一个价值立脚点。这立脚点不能是世俗的、经验的,它必须具有神圣和超验的性质,而这只能是一种具有宗教性的东西。所以,人文精神要重建,要昂扬,与其说回到“岗位”,不如说回到“天国”。你要否定和批判尘世的东西,就必须有一种源自天国的尺度。
近几年,中国文化界人文精神低落,但偶尔也有一两句声音很振奋人心。在作家里面,张承志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文化现象。他的散文,是近几年最具有批判性与否定性的一种声音,也是最真诚而正义的一种声音。他为什么如此,就因为他已找到一种宗教尺度,一种超验价值。
吴:大家不约而同地强调了“否定与批判”,作为对今天我们所需要的人文精神的理解,我想对“否定”是否还应该有一个属于我们的界定?因为本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在用西方人文观念来“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似乎中国学者从来不缺少否定。但事实证明,这种用一种现成的东西来否定另一种现成的东西,只属于黑格尔的方法性否定。这种否定搞来搞去,最后仍然不会诞生属于我们自己的存在。因此,我们所讲的否定,应该是一种能诞生我们自己存在的“本体性”否定。通俗点说,由于我们现在还没有自己的存在,所以我们要有一种一切现存的观念和行为,都不能表现我们自己存在的意识;而在现阶段,我们也只能依据这还未诞生的存在作为标准,去批判和否定一切现成的东西。对大的现实而言,这个“存在”具有超验性,对具体的现实而言,这个“存在”又具有未来性(尚未实现的现实),因此这种“否定性”是可以无处不在的,在世俗层面和超验层面都可以有所体现。对我们学者而言,强调这种本体性否定,意味着我们从此将有意识地探寻自己的思想,自己对世界的理解、自己的话语、自己的体验方式与内容,不再追随和认同他人——尽管这些暂时还未实现,但是由于我们都有一种“我的存在在那里”的意识,我们就有资格和权力依据这意识、这体验去批判和否定一切现实,并且依据这种精神去造就一种“人之初”意义上的人文氛围。我想,有了这种精神,有了这种氛围,有了这种体验,中国文化的转型,知识分子的独立,个体的存在,就至少有了一种正确的方位,再考虑具体的操作方法,或许就容易得多。
潘青松、朱洁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