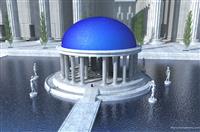在1930年代的“现代派”诗人中,卞之琳的诗所具有的某种独特的古典韵味很早就引起了评家的注意,废名在其《谈新诗》讲义中曾言:“卞之琳的新诗好比是古风,他的格调最新,他的风趣却最古了”,1将其与温庭筠词、李商隐诗作比,这开了卞之琳诗歌研究一个先河,尽管“大凡‘古’便解释不出”,2然而对于卞之琳诗与古典诗歌美学之间关联的讨论在此之后不绝如缕,卞之琳晚年大量的回忆、序跋文字中就新诗如何借鉴古诗的论述也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佐证。这些,连同对他诗艺中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观念影响的研究,使得他成为我们认识1930年代“现代派”诗潮乃至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具有典范性的诗人之一,在新诗与“传统”关系问题上,也已成为一个显著的例证,以表明新诗在借鉴或“继承”传统上的成功实践。
卞之琳晚年自述其写作观念:“我写白话新体诗,要说是‘欧化’,那么也未尝不‘古化’。……就我自己论,问题是看写诗能否‘化古’、‘化欧’。”3在新诗如何汲取古典诗词的文学资源方面,卞之琳抗战前的诗歌实践表现尤为突出,这与他在写作意识上的自觉有极大关系。本文试图考察的,则是卞之琳这种“化古”观念的内涵,它在理解、诠释新诗与古典诗“传统”之间关系方面的特征,及其形成的文化、历史语境,也试图探讨这一观念在其晚年大量有关新诗的论述中所显示出来的变异,和这种变异就新诗史而言所具有的复杂意味。
第一节 卞之琳1930年代的“传统”认知
卞之琳在1930年代的写作以诗与文学翻译为主,少有与诗有关的论述。李健吾曾在赞许的意义上谈到一些“不止模仿”而“企图创造”的新诗人:“然而真正的成绩,却在几个努力写作,绝不发表主张的青年。”4这其中即应包括卞之琳等“汉园”三诗人。
而他在这一时期所发表的仅有的零星论述中,就表现出对于新诗与旧诗关系的关切。1932年,他从英国著名文学评传作家哈罗德?尼柯孙(Harold Nicolson)所著《魏尔伦》一书中选取一章译出,以《魏尔伦与象征主义》为题发表,在这篇译文的“译者识”中他写到:
魏尔伦底名字在中国文艺界已经有相当的熟悉了,他底几首有名的短诗已经由许多人一再翻译过。象征主义呢,仿佛也有人提倡过。魏尔伦底诗为什么特别合中国人底口味?象征派作诗是不是只要堆砌一些抽象的名词?这种问题在这篇文章里可以找出一点儿解答,虽然这篇文章并非为我们写的。(说也奇怪,记得有一次看到我们一位大约自命为象征派的名家,把魏尔伦一首诗译得莫名其妙,在读者看来也许要以为不足怪,晦涩难解是象征派底不二法门,实在呢,译者不但并未看懂原诗底主意,连字句也不曾理清楚!这位名家听说尝“自承认是魏尔伦底徒弟”。)其实尼柯孙这篇文章里的论调,搬到中国来,应当是并不新鲜,亲切与暗示,还不是旧诗词的长处吗?可是这种长处大概快要——或早已——被当代一般新诗人忘掉了。5
这段话表明,对包括魏尔伦在内的法国象征派诗歌的接受引起了卞之琳对旧诗词的美学关注,使他产生了观念上的自觉,即他在文末所暗示的,有意在新诗中实现此种“亲切与暗示”的长处。卞之琳从一个“新月”诗派的学徒诗人超越出来,成为“现代派”的“前线诗人”,法国象征派诗人,尤其是魏尔伦起到关键的影响作用,6就此而言,可以说他的现代主义诗歌实践从一开始就与对中国古典诗学的思考联系在一起,魏尔伦的影响乃是“结合着中国古典诗学一起对卞之琳发生作用的”。7
如果说,就卞之琳自身的写作历程而言,对法国象征派诗与中国旧诗词之美学契合的体认,其意义更多在于帮助他辨识出自己的诗歌禀赋、气质,初步形成其写作趣向,那么他在这一时期另一重要的译介活动,对艾略特著名论文《传统与个人的才能》的翻译,则深刻地影响了他在写作上“化古”观念的成型。此文是他应叶公超之嘱而译,发表于1934年5月《学文》创刊号,在卞之琳日后的回忆中,这篇译文对其1930年代的写作具有标志性的影响作用,8而这里试图通过分析表明,卞之琳的“传统”认知与艾略特的论述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他对后者的接受有着特定语境下的“误读”性质,最终体现为两种不同的文学史观。
如前文所述,卞之琳在1930年代极少论诗文字,但如考察他直至建国前的著作活动,仍可发现他对文学传统、文化传统的一些论述。如在1944年为于绍方译亨利?詹姆士小说《诗人的信件》作序时他曾就这部小说的内容发挥到:
传统是必要的,传统是一个民族的存在价值,我们现在都知道,保持传统却并非迷恋死骨。拜伦时代和拜伦时代的世界已成陈迹了,要合乎传统,也并不是为了投机取巧,随波逐流,就应当学拜伦时代人对于当代的反映而反映我们的时代。传统的持续,并不以不变的形式,……9
在他稍早的长篇小说《山山水水》中,卞之琳借以他自身为原型的主人公梅纶年之口也发表了这样的意见:
我们现在正处在过渡期中,也自由,也无所依傍,所以大家解放了,又回过头来追求了传统。一个民族在世界上的存在价值也就是自己的传统。我们的传统自然不就是画上的这些笔法,也许就是“姿”。人会死,不死的是“姿”。庞德“译”中国旧诗有时候能得其神也许就在得其“姿”。纯姿也许反容易超出国界。10
尽管并非直接就新诗或新文学而言,但这些文字仍为我们把握他的“传统”意识的内涵提供了一定的线索,而它与艾略特意义上的“传统”体现出几个重要的不同之点。其一,在艾略特那里,“传统”的涵义主要是指在文学实践的意义上一种不断变动的秩序:“现存的艺术经典本身就构成一个理想的秩序,这个秩序由于新的(真正新的)作品被介绍进来而发生变化。这个已成的秩序在新作品出现以前本是完整的,加入新花样以后要继续保持完整,整个的秩序就必须改变一下,即使改变得很小;因此每件艺术作品对于整体的关系、比例和价值就重新调整了;这就是新与旧的适应。”11在此意义上,“传统是具有广泛得多的意义的东西。它不是继承得到的”。而卞之琳使用这一概念时明显具有一种实体化的内涵,这很大程度上缘于英文tradition与中文“传统”在译介时发生的变异,卞之琳只是沿袭了它,12即将它视为是在时间上属于“现代”之前的文化及其价值,因而在艾略特那里所表述的“新”与“旧”的解释学关系在这里被转化成了“古典”与“现代”的辩证。
其二,艾略特将诗人/作家与tradition应具的关系概括为一种“历史意识”的获得,即“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也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13“要感到从荷马以来欧洲整个的文学及其本国整个的文学有一个同时的存在,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是这一意识“使一个作家最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自己和当代的关系”,也就是说,在时间的维度上,他强调的是文学实践由此历史意识而具备的当代敏感,在tradition之秩序与个人才能之间指向的是后者,是“真正新的”作品的生成,而在卞之琳这里,则更注重“传统”之于现代的价值。14
其三,卞之琳对“传统”价值的强调是将之置放在民族/世界的论述框架中,这是艾略特在欧洲文学的范畴之内而带有普遍主义意味的表述中所没有的。这实际上延伸了周作人在“五四”时期就表达过的观点:“我仍然不愿取消世界民的态度,但觉得因此更须感到地方民的资格,因为这二者本是相关的,正因为我们是个人,所以是‘人类一分子’(Homaraus)一般。……我相信强烈的地方趣味也正是“世界的”文学的一个重大成分。具有多方面的趣味,而不相冲突,合能和谐的全体,这是‘世界的’文学的价值,否则是‘拔起了树木’,不但不能排到大林中去,不久还将枯槁了。”15
卞之琳不曾就艾略特此文发表过具体的见解,但他在前引文字中表露出来的“传统”观不可能不带有后者所影响的痕迹,如以他在题为《尺八夜》的随笔中结尾一句话两相对照即可看出这一点:“呜呼,历史的意识虽然不必是死骨的迷恋,不过能只看前方的人是有福了。”16事实上,卞之琳恰恰以此表明了他的“历史意识”与艾略特的分野所在,即虽然反对一味地崇古,然而,正如《尺八夜》一诗所体现的故国式微之思一样,在卞之琳的“历史意识”中,有着艾略特文中所无的民族现实境遇的沉重内容,身处大敌临境的“边城”北平,巨大的危亡感使他并非从文学史秩序的抽象层面去领悟“历史意识”,而是自觉融入了对民族文化命运的思考。17
应当说上述“传统”认识框架并非卞之琳所独有,然而就其诗歌实践以及日后的有关论述来看,他仍然显示出某种代表性。首先他很少孤立地去看待新诗实践中这一问题,而对这一问题所蕴含的西方现代文学的诠释中介具有充分的自觉,在如何“融会中国传统和世界现代感应性”问题上,18后者乃是基础,如他论及梁宗岱时所言:“由于对西方诗‘深一层’的认识,有所观照,进一步了解旧诗、旧词对于新诗应具的继承价值,一般新诗写作有了他所谓‘惊人的发展’,超出了最初倡导者与后起的‘权威’评论家当时的接受能力与容忍程度。”19在此意义上返观他于新时期的开端在《<雕虫纪历>自序》中提出的所谓“欧化”、“化欧”和“古化”、“化古”的说法,亦可察觉他以后者为其时仍为主流意识形态所戒备的欧美现代主义文学流脉张本的小心翼翼的意图。20
其次,在卞之琳这里,“传统”所具有的内涵以及在此基础上生发的“化古”意识,在新诗与旧诗关系上,承续了1920年代闻一多对“地方色彩”的呼吁和周作人的“融化”论,就写作而言也是对它们更为全面和成功的实践,很大程度上可以说,闻一多曾经召唤的所谓“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是在卞之琳等“现代派”诗人这里真正得以成为现实,21这也是李健吾在后者这里所兴奋地发现的:“他们属于传统,却又那样新奇,全然超出你平素的修养,你不禁把他们逐出正统的文学。……所以最初,胡适先生反对旧诗,苦于摆脱不开旧诗;现在,一群年轻诗人不反对旧诗,却轻轻松松甩开旧诗。”22而在终于“甩开旧诗”的同时,也意味着新诗与旧诗及其美学“传统”之间一种迥异于五四话语的认知方式开始被普遍接受,即新诗对于“传统”的“继承”。这种“回过头来追求传统”的认知方式正是在1930年代,尤其是在北平学院文人的氛围中获得有力的生长。同时,旧诗的“传统”被更充分地对象化,与同时期的诗人废名、林庚(尤其是后者)“以旧诗为方法”的诗观相比较,卞之琳的方式可以说是“以旧诗为对象”的,在前者那里,古今并无严格的区分,旧诗的某些概念体系(尽管已经经过了现代文学观念的中介)如“质”与“文”等仍然能够作为一种活跃的诠释力量参与到新诗的理论与实践之中,而在卞之琳这里,“传统”(“古”)已是诠释和“化”的宾体。23
第二节 卞之琳晚年的“化古”论述及其内涵
接下来我想从一个较少为人注意的角度来继续考察卞之琳对于新诗与旧诗“传统”关系的论述,并将问题延伸到新诗史研究的层面。青年时代“绝不发表主张”的卞之琳,其有关新诗的论述多数都撰写发表于晚年,在以往对卞之琳和1930年代“现代派”诗的研究中,多把他晚年的新诗论述视为与他青年时代的相关表述具有等同内涵、同时在评价他早年诗歌时其权威性毋庸置疑的叙述,而对其间横亘的时间/话语作透明性的处理。然而,从1930年代到1980年代,这半个世纪之间所发生的政治、历史与文学思潮、观念的变化无疑是巨大的。对于理解这些论述的意义,两个时代各自的语境差异是否有必要考虑在内呢?
卞之琳是在《<雕虫纪历>自序》中首次提出“化古”这一说法的,这是他在新时期开始前后所发表的最早几篇文章之一,也是新诗史研究中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献。这篇序言既为卞之琳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线索,乃至奠定了新时期以来卞之琳研究的一些主要命题的基础,他对自己写作特征、艺术追求的一些概括,如“小处敏感,大处茫然”、“化欧”、“化古”,都已成为不刊之论,同时它对1930年代“现代派”诗歌的研究也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是这方面研究中被引用频次最高的文本之一。但它的话语构成的复杂之处却迄今尚未得到研究者的足够重视。24
《<雕虫纪历>自序》作于1978年12月,由于这一时期特定的“美学和意识形态的双重规约”,25此文在其发言方式上带着明显的当时流行的“语法”和“自我检讨”的特征,文章开头先后两次引用“主席语录”作为“通行证”,在谈及1930年代他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接受时也带着委婉的道歉式的口吻:“我自己思想感情上成长较慢,
最初读到20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还好像一见如故,有所写作不无共鸣”,26在此意义上,他对其1930年代诗歌写作特点的自我总结“小处敏感大处茫然”就不仅只是“自谦”之辞,而是具有特定语境下的内涵,而且,它也并非仅是出于意识形态规约之下被动作出的措辞,就卞之琳自身的思想和写作经历来看,其中也包含着他在“小”与“大”之间的主动选择。与他的诗友何其芳一样,卞之琳在抗战开始后有一个思想上逐渐左转的过程,只是过程更为复杂,27在新的政权建立之后,他也持较积极投入的态度,如他1980年代末一篇文章中还曾忆及在“文革”前的十七年中他“三度诚心配合当前形势,真诚(当时达到忘乎所以的程度)写几首诗”,并为它们在官方文坛所受到的冷落而颇觉不平。28这种思想意识上的变化当然也是经历了和建国后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的思想改造的结果;而落实在他晚年的有关论述中,则就可以看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关于文化艺术的意识形态权威话语所作用的痕迹。同样涉及到中国艺术的传统,卞之琳在1985年曾就昆曲发表过这样的意见:“复古不足为训;民族气派,却不容置诸脑后。……不保持与发扬我国优秀一方面的民族风格,我们决不可能跻身现代世界文艺前列。”29这里或可感到他在特定“套语”之下婉转表达的良苦用心,但其中“民族气派”的所指已未必全是他青年时代所究心的“姿”或“中国精神”这些说法的内涵。30这是第一重有必要加以留意的语境。
卞之琳在文革结束之后所写的、现在所可见及的第一篇文章是《分与合之间:关于西方现代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稍早于《<雕虫纪历>自序》的写作而均发表于1979年,31和他的学生袁可嘉一样,作为外国文学研究者的卞之琳从新时期开始就在为重新恢复现代主义文学的“合法身份”而努力,这种努力甚至一直持续到了1990年代初期。32这构成《<雕虫纪历>自序》写作、发表的另一重要背景。代表卞之琳诗歌主要成就的早期诗歌亦构成了《雕虫纪历》的主体部分,而它们的现代主义质地以及所受到的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滋养,在序言写作的时间显然存在着讲述与接受、意识形态与美学的双重困难。
此外,从这篇序言开始,晚年卞之琳除了在新诗诗律与译诗问题上专门撰写了多篇文章,通过序跋、回忆文字,也有意识地表述他对于新诗、新诗发展历史的各方面观点,正如他自己所说,“1939年,我一度完全不写诗,特别从50年代起,谈诗就多了一点。形势一转,我对师友,今已大多数作古的,不论相知深浅的前辈或侪辈,著述阅读生涯中实质上与诗有缘的,无论写有诗篇立有诗说与否,我为文针对他们或他们的产品,都以诗论处,讨论也好,追思也好,写序也好,评论也好,推举也好,借以自己立论也好,……所收各篇都不扮起一副学术性面孔,只是都贯穿了我自己既有坚持又有发展的见解。”33这一方面使得他的这些文章别具分量,如其中纪念闻一多、梁宗岱、叶公超、何其芳的长文,和为徐志摩、冯文炳(废名)、戴望舒等人诗集文集所作长序,都成为有关研究中的重要资料;也形成了这些文字独特的、有时略显繁赘的文体,就《<雕虫纪历>自序》而言,它的历史价值的获得恰恰是由于它完全脱出了一般的自序文体的规格惯例,在自述写作生涯的同时着意借此场合不厌其详地缕述他对新诗的认识,在这方面,可以说他是带着明确的“历史意识”的。不过,他在文中也说明,新诗格律问题和利用古洋资源问题,虽然是他“一贯探索”的,文中所谈却是“今日的看法”,34因此,在他晚年作为回忆者、作为诗论家和某种意义上的新诗史家的认识与表述,与他早年作为年青的“前线诗人”的诗歌观念之间,也存在着并非可以忽略的缝隙。
在此意义上,可以说《<雕虫纪历>自序》是一个“多褶层”的文本,它一方面似乎呼应了他在1930年代关于象征派与旧诗词气味相通的观点,一方面又是在所谓“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一论述框架下来展开他个人在“化古”、“化欧”方面的经验陈述,而在这些论述中,包含着三个层次:他以可以被接受的话语方式所表述的“今日的看法”;他在特定语境中所使用的修辞策略;在这些论述中所折射的他早年的实际写作观念。这些层次并不可能被完全分解,但却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体察它的内涵。
以这样的眼光再来重读这篇自序中的这段话:
我写白话新体诗,要说是“欧化”(其实写诗分行,就是从西方如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那么也未尝不“古化”。一则主要在外形上,影响容易看得出,一则完全在内涵上,影响不易着痕迹。一方面,文学具有民族风格才有世界意义。另一方面,欧洲中世纪以后的文学,已成世界的文学,现在这个“世界”当然也早已包括了中国。就我自己论,问题是看写诗能否“化古”、“化欧”。35
就可以看出其中为“欧化”(这是卞之琳作品在建国后常被批评的地方)、为新诗的“世界”性所作的辩解的努力。也就是说,在此文的场合,“化古”、“化欧”并非同等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前者起着为后者“保驾”、“引渡”的作用,以这样的修辞方式,卞之琳试图重新申张现代主义文学的观念与技巧。他接下来表示:“在我自己的白话新体诗里所表现的想法和写法上,古今中外颇有不少相通的地方”,36与他在1930年代谈象征派诗与旧诗词长处的相似,在内涵上已有所不同,后者是由西方诗而引发对中国文学的重新观照,并在后来的危亡感受中进一步发展为文化价值的认识,其重点在“古”,而前者则是在意识形态禁锢刚获松动时,对异质文学因素的辩护,其重点在“欧”。
我总喜欢表达我国旧说的“意境”或者西方所说“戏剧性处境”,也可以说是倾向于小说化、典型化、非个人化,甚至偶尔用出了戏拟。37
我写抒情诗,像我国多数旧诗一样,着重意境,就常通过西方的“戏剧性处境”而作“戏剧性台词”。38
迄今为止,只有极个别研究者对卞之琳这里所说的“意境”与“戏剧性处境”之间的相通表示了质疑,但主要是就其写作表现而言,认为他的作品更多前者的呈现,而在“戏剧化”上有所不足。39这已可引出一个问题:在“意境”和主要从艾略特那里得来的“戏剧化”技巧(它与袁可嘉1940年代主要从肯尼斯?伯克那里借来的“戏剧主义”诗学是需要区分开的两个概念)这两个相当不同的范畴之间,卞之琳将之牵连起来的交叉点在哪里?此处无法就此作出探讨,而是从修辞策略的角度,认为卞之琳的表述在二者间是有所轻重的,两处均是以前者过渡后者,略于前而详于后,重点都在后者,这在另一处相似的表述里可以看得更明显:
我在自己诗创作里常倾向于写戏剧性处境、作戏剧性独白或对话、甚至进行小说化,从西方诗里当然找得到较直接的启迪,从我国旧诗的“意境”说里也多少可以找得到较间接的领会,……40
这也就是前面曾经提到的,在“中国传统”和“世界现代感应性”之间,他所偏重的乃是后者。而综观卞之琳涉及“化古”的言论,也会发现,较之他分析、评价他和他的师友的写作中所受到的西方不同时期、不同风格诗人和不同流派诗学的影响时详尽细致的程度,他谈到他们“继承”中国诗“传统”的场合都是非常简略乃至语焉不详的,这种对比相当明显,如谈何其芳:
现在事实清楚,何其芳早期写诗,除继承中国古典诗传统或某些种传统以外,要说也受过西方诗影响,那么他首先直接、间接(通过《新月》诗派)受19世纪英国浪漫派及其嫡系后继人的影响,然后才直接、间接(通过《现代》诗风)受了19世纪后半期开始的法国象征派和后期象征派的影响。41
这当然与旧诗“影响不易着痕迹”因而难以指实有关,与他的关注点更多在于“新诗和西方诗”之关系有关,但也不尽然,在《<雕虫纪历>自序》中,他详细交代了波德莱尔、艾略特、叶芝、里尔克、瓦雷里、奥顿、阿拉贡等西方现代诗人在他写作的不同阶段以不同方式给他的启发,但谈到古典诗“影响”的一面时则是:
从消极方面讲,例如我在前期诗的一个阶段居然也出现过晚唐南宋诗词的末世之音,同时也有点近于西方“世纪末”诗歌的情调。42
例如,我前期诗作里好像也一度冒出过李商隐、姜白石诗词以至《花间》词风味的形迹。43
这些文字(尤其后一处)的口吻是耐人寻味的,一方面显得含混而作出了不少修饰性的限定,另一方面,它不像是经过汲取(“化”)古典诗词资源之后的作家的经验总结,倒近于旁观者置身其外的评鉴。作这样的“文本细读”,并不是要质疑卞之琳的古典文学修养,以及他的诗作中古典文学影响的存在,这方面已有了大量的研究,44而是想揭示出,同为1930年代的“现代派”诗人,有异于废名、林庚,卞之琳的写作直接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受益,他对于旧诗词的认知方式、态度也更接近于我们今天较普遍的那种宽泛和固定化的理解;与早期基于写作实践而发生的对旧诗词某些具体的艺术质素的观照体认不同,他晚年的有关论述更多是作为一个特殊的新诗史家的原则性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客观上正与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某种期待视野相叠合,由此,他的一系列具有独特历史意识的忆述相当深刻地参与了迄今为止对1930年代“现代派”诗歌的形象建构。
--------------------------------------------------------------------------------
注释:
1 废名:《论新诗及其他》,辽宁教育出版社,第154页。
2 同上。
3 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卞之琳文集》中卷,江弱水、青乔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59页。
4 李健吾:《新诗的演变》,《大公报?小公园》1935年7月20日第1740号。此文后被作者作为《<鱼目集>——卞之琳先生作》一文的第一节收入《咀华集》。
5 卞之琳:《<魏尔伦与象征主义>译者识》,《新月》1932年11月第4卷第4期。
6 参见江弱水《卞之琳诗艺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五章第一节的分析。
7 江弱水:《卞之琳诗艺研究》,第184页。卞之琳后来亦曾如此提及他走向现代主义诗风的开始:“我则在学了一年法文以后,写诗兴趣实已转到结合中国传统诗的一个路数,正好借鉴以法国为主的象征派诗了。”见《赤子心与自我戏剧化:追念叶公超》,《卞之琳文集》中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87页。
8 卞之琳晚年在多处谈到这篇译文在他写作生涯中的重要性,如《<西窗集>修订版译者引言》(1980): “我作为译者,即使在编纂这本译文集的当时,对于西方文学,个人兴趣也早从波德莱尔、玛拉美等转移到瓦雷里和里尔克等的晚期作品,从1932年翻译魏尔伦和象征主义转到1934年译T.S.艾略特论传统的文章,也可见其中的变化。”《卞之琳文集》下卷,第587页。《赤子心与自我戏剧化:追念叶公超》中忆及他早期译《魏尔伦》选章、波德莱尔诗和艾略特文章:“这些不仅多少影响了我自己在30年代的诗风,而且大致对三四十年代一部分较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新诗篇的产生起到过一定作用。”《卞之琳文集》中卷,第188页。
9 卞之琳:《亨利?詹姆士的<诗人的信件>——于绍方译本序》,《卞之琳文集》中卷,第49页。
10 卞之琳:《山山水水(小说片断)》,香港山边社,1983年,此处据《卞之琳文集》上卷,第365页。
11 艾略特:《传统与个人的才能》,卞之琳译,《学文》1934年5月第1卷第1期。以下不另出注。
12 本文无力对现代汉语中“传统”这一概念的历史进行追溯,但它显然是从日本“汉字”词语中“回归”的外来词之一,可参见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的附录D中相关条目。它在古代文言中的涵义与今天不同,多指帝业的世代相传,其所具有的“守成”的涵义或许影响了它在现代汉语中的使用。
13 卞之琳此处的翻译也许也构成其误读在细节上的体现,“现存性”在原文中为presence ( of the past ) , 艾略特所欲表达的“过去的在场”、过去与现在之存在的同时性这一极具哲学意味的时间观,一定程度上被这一译语削弱了(可试与[过去的]“现在性”相比较),而这很大程度上与对“传统”的实体化理解有关。
14 臧棣曾指出,艾略特对玄学派诗人的阐释(在中文语境中)常被泛泛地解读为对文学传统的重视,
所谓“回归传统”,这也许错失了他真正的用意,其批评的策略性所在,即回击他同时代的公众普遍认为现代诗歌沉溺于文学实验而陷入晦涩难懂的读者舆论,“艾略特几乎是诡辩式地运用人们对古已有之的依从心理”。这种误读在对艾略特此文的接受中也相当普遍。见其《现代性与新诗的评价》,《现代汉诗:反思与求索——1997年武夷山现代汉诗研讨会论文汇编》,作家出版社,1998年,第95页。
15 周作人:《<旧梦>序》,《自己的园地》,岳麓书社,1987,第117页。
16 卞之琳:《尺八夜》,《卞之琳文集》中卷,第12页。江弱水《卞之琳诗艺研究》亦点出此点,见其第192页。
17 张洁宇《荒原上的丁香——20世纪30年代北平“前线诗人”诗歌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一书中亦从创作心态的角度分析了卞之琳等诗人的写作意识、作品情调与1930年代北平的历史氛围之间的关联。
18 语出卞之琳《一条界线和另一方面:郭沫若诗人百年生辰纪念》一文,见《卞之琳文集》中卷,第143页。
19 卞之琳:《人事固多乖:纪念梁宗岱》,《卞之琳文集》中卷,第168页。
20 关于这一点下一节将有较详分析,亦可参见作者与此文同时稍早写成的《分与合之间:关于西方现代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中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辩护。
21 闻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18页。
22 李健吾:《<鱼目集>——卞之琳先生作》,《大公报?文艺》1936年4月12日第126期(误排为122期)“星期特刊”。
23 详见本人博士论文《新诗与“古典诗传统”:诠释性关系的建构——以1930年代北平现代主义诗坛为中心》中的有关分析,废名和林庚都是将新诗作为中国诗最近的一次变革来看待的,从而将新诗与旧诗的差异相对化,这与卞之琳的新诗立场完全不同;他们对于温李的兴趣也在于其中所具有的“新诗”的因素,而卞之琳则主要是在风格情调、所谓“末世之音”的意义上接受温李,其间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也就是说,在前者那里,旧诗仍是重要的文学资源,而在后者,多数时候只是美学资源。
24 姜涛《小大由之:谈卞之琳40年代的文体选择》是少数注意到这一文本中卞之琳的自我表述与特定的历史语境之间关联的论文,见《新诗评论》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25 同上,第28页。
26 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卞之琳文集》中卷,第446页。
27 姜涛在《小大由之:谈卞之琳40年代的文体选择》一文中非常细致地讨论了卞之琳在1940年代尝试小说创作的内在动因,事实上,他这一时期的各类写作尝试如《慰劳信集》和报告文学《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晋东南麦色青青》等都是朝向“大”的努力的一部分。《<雕虫纪历>自序》中对于他抗战后到1940年代末的思想与活动也做了简略的交代。
28 卞之琳:《人尚性灵,诗通神韵:追忆周煦良》,《卞之琳文集》中卷,第218页。卞之琳在建国后至“文革”结束这一期间的经历可参见张曼仪《卞之琳著译研究》(香港大学中文学系,1989年)一书。
29 卞之琳:《题王奉梅演唱<题曲>》,《卞之琳文集》中卷,第93页。
30 在小说《山山水水》中,卞之琳曾借一个人物之口,把中国艺术中所推崇的“以认真到近乎痴的努力来修养了功夫而表现出随兴的风度”这一特点视为“中国精神”的表现。见《卞之琳文集》上卷,第312页。
31 此文写于1978年11月,原载《外国文学集刊》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收入《卞之琳文集》中卷。
32 在1992年撰写的《重温<讲话>看现实主义问题》一文中,卞之琳借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的场合,以其中有关现实主义的观点为由头迂回地为现代主义辩护,原载《外国文学评论》1992年第3期,收入《卞之琳文集》中卷。
33 卞之琳:《<人与诗:忆旧说新>增订自序》,《卞之琳文集》中卷,第135-136页。
35 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卞之琳文集》中卷,第459页。
36 同上。
37 同上,第446页。
38 同注51。
39 陈旭光:《中西诗学的会通——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9页。
40 卞之琳:《完成与开端:纪念诗人闻一多八十生辰》,《卞之琳文集》中卷,第155页。
41 卞之琳:《何其芳晚年译诗》,《卞之琳文集》中卷,第293页。
42 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卞之琳文集》中卷,第459页。
43 同上,第460页。
44 江弱水在其《卞之琳诗艺研究》中对卞之琳所受古典文学、哲学影响作了专章分析,是目前这方面研究最详尽的。他在讨论这种影响时也指出:“由于现代汉语与文言形态上的差异,也由于现代诗艺与旧诗词形式与技巧的差异,所有对于古典传统的吸收和利用,更有赖于诗人创造性转化的才能,而转化也就意味着不再执着于外形的相似。而且,现代诗人对古典传统的援引往往趋同,很难再具体地辨识其为《诗经》的传统抑或《楚辞》的传统,究属韩孟的影响还是元白的影响。这种笼统的情况很普遍地存在于新诗与旧诗的关系中。”见此书第230页。但对于这种援引的趋同仍需要作出进一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