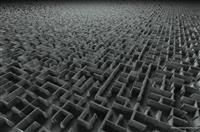一
注杜千家各苦辛,次公详解迈时伦。语熔经史偏知味,事用祖孙贵辨真。
断简抛残须获惜,丛书辑佚费精神。林君巨帙存遗烈,杜学重兴势喜人。
《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以下简称《辑校》)一书,本是山东大学研究生林继中君在萧涤非先生指导下完成于一九八六年的博士论文,我当时因参加此论文之答辩会曾获先睹之快,遂作此诗以赠林君,既述赵书的历史背景与学术价值,亦叹林君辑校的艰辛,喜杜学的后继有人。虽口吻近于老气横秋,而萧先生当时见了亦颇欣悦,曾赐书嘉勉。今林君此书终得上海古籍出版社领导之积极支持而问世,萧先生虽作古人,其平生酷爱杜诗,精研杜学之遗志亦可稍慰于地下。今与学太合作撰述评此书的文章而不能忘怀旧作,亦非无故也。
赵次公注是杜诗第一部较为准确、丰富、有一定深度的全注本。今存明抄本题名《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它诞生于北宋末、南宋初,正是杜诗受到空前重视的时代,人们读杜谈杜,学杜注杜,蔚成风气。不仅士大夫如此,其他阶层略有文化的人,也习染此风。《蔡宽夫诗话》说:“三十年来学诗者,非子美不道。虽武夫女子,皆知尊异之。李太白而下,殆莫与抗。”有的人,甚至嗜杜成癖,见人就开口谈杜诗,使人不敢近他,说:“怕老杜诗。”蔡宽夫又说:
老杜诗既为世所重,宿学旧儒,犹不肯深与之。尝有士大夫称杜诗用事广,傍有一经生忽愤然曰:“诸公安得为公论乎?且其诗云:‘浊醪谁造汝,一酌散千忧。’彼尚不知酒是杜康作,何得言用事广?”闻者无不绝倒。予为进士时,尝舍于汴中逆旅,数同行亦论杜诗。旁有一押粮运使臣,或顾之曰:“尝亦观乎?”曰:“平生好观,然多不解。”因举“白也诗无故,飘逸思不群”相问曰:“既言无敌,安得却似鲍照、庾信?”时坐中虽然之,然亦不能遽对,则似亦不可忽也。
它说明“杜甫热”还带有点全社会性。从这条记载中亦可见大多数读者在理解杜诗上还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只整理、编纂杜甫诗集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还要有注释本,以帮助读者扫清障碍。
北宋时期的士大夫已经认识到要读懂杜诗是有一定难度的。杜诗用典多,与时事、现实生活联系密切,这些又与杜甫个人的流离播迁息息相关。因此,王直方概括地说:“不行一万里,不读万卷书,不可看老杜诗也。”(辑录本《王直方诗话》)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于是代替读者“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注本便大量出现了。
读者的需要对书商来说是市场需求,因此,杜诗最早的一批注本带着浓重的商业色彩,这主要体现在出得快、出得多上。北宋中叶以后,杜诗开始风行,到了北宋末、南宋初,仅数十年间便有数十种杜诗注本、编年本的出现。较知名者如王得臣的《杜工部诗增注》,薛仓舒的《杜诗刊误》、《杜诗补遗》与《续注杜诗补遗》,郑卬的《杜少陵诗音义》,孙觌的《杜诗押韵》,蔡兴宗的《杜诗》与《杜诗正异》,杜田的《杜诗补遗正谬》与《续注杜诗》,鲍慎由的《注杜诗及文集》,薛梦符的《广注杜诗》,师古的《杜甫诗详说》,卞大享的《改注杜诗》,罗列的《注杜诗事类》,鲁詹的《杜诗传注》等等,从这些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书名,可以想到当时的“盛况”。这些编注者大多名不见经传,许多可能就是为书坊编著书籍赖以糊口的下层文人,文化水平不高,这点决定了此批杜诗注本的质量不会太高。此时还出现了书贾用以招徕顾客而故夸繁富的《十家集注杜诗》、《门类增广十家注杜诗》(尚存残本六卷)。为了促销获利,书贾还假托名人,欺骗顾客。如各种集注本中的“王洙注”、“黄庭坚注”,皆属此类。王洙根本没有注过杜诗;黄庭坚所谓“杜诗笺”可能也仅是庭坚读杜诗时随手笺于书上的数十条备忘文字而已,后被好事者编入《豫章黄先生别集》,遂为书贾剽窃,仿佛黄氏真有专著《杜诗笺》似的。最可恶者为托名苏轼所作《老杜事实》(或名《杜诗事实》、《东坡事实》、《东坡杜诗故事》等),此书在注杜时“随事造文,一一牵合,而皆不言所自出。且其辞气首末若出一口,盖妄人依托以欺乱流俗者,书坊辄抄入集注中,殊败人意”(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书中任意捏造出处,不负责任,在古书注解本中当推第一,又把文责推到苏轼身上,更是可恨。或云此书为闽人郑卬伪造。其三是编注粗糙,那些随口造文、伪造典事的《老杜事实》与师古的《杜甫诗详说》等可不具论,就一些严肃注本看,也多浅鄙可笑之论与常识性的谬误。王直方言:“近世有注杜诗者,注‘甫昔少年日’乃引贾谊少年,‘幽径恐多蹊’,乃引《李广传》‘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绝域三冬暮’,乃引东方朔‘三冬文学足用’,‘寂寂系舟双下泪’,乃引《贾谊传》‘不系之舟’,‘终日坎(土禀)缠其身’,乃引《孟子》‘少坎坷’,‘君不见古来盛名下’乃引《新唐书·房琯赞》云:‘盛名之下为难居。’真可发观者一笑。”(《王直方诗话》)对于有学问的读者是可“发观者一笑”,而对于那些要靠注本弄懂杜诗的读者真可使其一哭,因为王氏列举的那些注文还不在于它的正确与谬误,而是这些注文对弄懂杜诗毫无用处,注了等于没注。清代钱谦益谈到宋人杜诗注时说:“杜诗昔号千家注,虽不可尽见,亦略具于诸本中。大抵芜秽舛陋,如出一辙。”并总结了其八大罪状:伪托古人、伪托故事、附会前史、伪撰人名、改窜古书、颠倒事实(以前事为后事,以后事为前事)、强释文义、错乱地理。(见《注杜诗略例》)这些虽有言之过甚之处,大体上还是说中了宋注的缺点。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宋代最高水平的杜诗注本——赵次公注出现了。它的出现,杜诗才有了一个较为全面、较为正确的注释本,使一般读者对于杜诗有了较为准确的认识,这是杜诗学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
二
《杜诗赵次公先后解》的学术成就,在《辑校·前言》中作了充分的肯定。这里仅就赵氏注释与编年之风格作些补充评述。
赵氏注之风格是注释平实准确,编年细致深入。注释平实看似简单,实际不易。历来注释诗文,特别是注释有卓越成就的诗文作品无不喜欢在诗文夹缝中搜索微言大义,以表现自己发隐探赜之苦心,因此极易流于穿凿附会,求之愈深,离原义愈远。《诗经》、《楚辞》的许多注释本皆有这种倾向。杜诗是在宋代被人们广泛理解和重视的,但也是自宋代起被歪曲的。因为宋代有些读者认为杜诗都是表达“周情孔思”的,可与六经相提并论,杜甫是他们心目中的圣人,其一言一行必合于圣人的标准。然而杜甫是唐人,有唐代特有的自信与潇洒,而不是宋代圣人模具中的产品,这些皆一一反映在其诗中。于是宋代一些批评家在解释杜诗时便横加歪曲,使之就范于己。而赵次公注释的最大特点就是把杜甫还给杜甫,下面我们结合例证,作些说明。
杜甫是极度关心国事天下事的诗人,从他开始,忧国忧民便成为诗人的传统。杜甫的“忧”不是口头禅、门面语,更不是决心要教育读者而进行的表演。他这种“忧”发于内心,时有流露,决非处处标榜。另外杜甫也是普通人,是丈夫、父亲、朋友,因此他也有许多普通人的生活,他把在这些生活中的感受也写入诗中,所以我们才能在杜甫诗集中看到一个完整的杜甫。而宋代一些批评家把忧国忧民庸俗化、表面化,把它视为一种表演,而且要从朝廷、官场一直演到家。有时诗人明明是在与老妻稚子闲语,却被认为是在写君臣论道,有时诗人欣赏自然风光,却被认为是诉说诗人对政局的感受。注释者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时要兜好几个圈子,才能扣到这些大题目上,注者累,读者也累,更可气的是歪曲了作者。赵次公认为杜甫不会“打谜作诗”,因此注释者也不必去猜谜解诗。这种理解是极平实的,但又是许多注释者难以达到的。
赵次公注中多次提到“世有《东溪先生集》者,其中有释杜工部诗十六篇,每篇先拟《毛诗》之序,以撮其大要而判释之,自以为启杜诗之关钥”云云,这便是刻意求深、曲解杜诗的典型。“东溪先生”即高登,乃北宋末年与陈东齐名的学生运动领袖,颇以忠义自许。“四库”馆臣称其“每饭不忘君”。他自认为是老杜的知音,以解经的方法说杜,似乎在拔高杜诗的价值,实际上是在贬低杜诗的艺术。他选杜诗十六首,细加解剖,作为理解杜诗的钥匙。于是赵次公便以这位颇有影响的杜甫“知音”为靶子反复指出他的错误,以破除注杜中的穿凿附会之风。高氏解《北风》云:“《北风》悲燕寇衰弱王室,祸以加民。寇来自北,故况北风。”注“北风破南极”云:“寇自北来而破两京。”注“朱凤日威垂”云:“天子将出狩”也。注“洞庭秋欲雪”云:“安史之乱唯不及江南,秋非雪时,言及将乱也。”注“鸿雁将安归”云:“大曰鸿,小曰雁,大小皆无所附,与《诗》万民离散同意。”高氏洋洋洒洒解了一大篇,连此诗写作时间都没搞清楚。赵次公说:“此其不考公赋诗之年辰与处所,直误以安史之乱,故为此注。”此诗写于大历四年(769)潭州(今湖南长沙),距安史之乱被平定的广德元年(763)已有六年,因此,“悲燕寇衰弱王室”纯粹是想当然。赵氏批驳说:“然就其中误两京为南极,夫西京(指长安)天子所居,曰南极犹可,东京何预?亦可譬之南极乎?便自差排朱凤为天子,威垂为出狩,则何所据乎?洞庭自是荆湖路,亦何谓之江南乎?惟以鸿雁为民,则周诗美宣王之说,却与朱凤譬天子之无出处反自攻矣。以此集刊传,恐惑后学,故次公费辞辨之。”赵注中不仅揭示了高注中的自相矛盾及其缺乏依据之处,而且对全诗作出平实的解释。“北风”就是指北方吹来的风,“南极”指楚地,因为,“公在楚,故所见者北风破南极与洞庭秋欲雪也。”“朱凤”为南方之鸟,遇寒而“威垂”,“鸿雁过洞庭,洞庭欲雪而安归?皆言值时如此,于是乎失所也。”用此以“自叹其在风尘之际,方旅泊而未得归也”。赵氏完全从写实角度对此诗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高登在解释内涵较为丰富的寓言诗《朱凤行》、《白凫行》等篇章时则穿凿更甚,诗中所写的朱凤、黄鹄、白凫等动物情态皆有所喻,但这些属于寓言,取譬虽近,所指亦远,其所喻的应是某一类人或某一类社会现象。高氏在分析这些寓言诗时硬是把它们落实在某人某事上,看似确切,实际上是笨拙之极,而且使其神韵全无,变成了枯燥的历史记载。如说《朱凤行》是:“悯天子蒙尘,小大之臣,并罹祸难而恩泽下均也。”此诗开篇即写道:“君不见,潇湘之山衡山高,山巅朱凤声嗷嗷。”可知此诗写于大历五年(770)诗人在衡州之时。杜甫一生经历两次天子“蒙尘”,一是天宝十五载(755),因安史叛军破潼关,唐玄宗西逃入蜀避难;另一为广德元年(763),吐蕃攻长安,代宗东走陕州,以避其锋。两次皆与作诗时间不合,因之,不能将此诗坐实在任何一次“天子蒙尘”上。实际上此诗并不晦涩,诗中虽有寄兴,但却是:“感于物而兴焉也。公在衡州,则衡山眼前所见也,朱凤则山上之物也。因其物而有作,乃以为兴也。”赵氏认为这首诗是托兴朱凤,写君子无朋、怒视小人而悯及弱者。此解通达平稳,不哗众取宠而得其实。在阐释《白凫行》[注]诗旨时,似与高登相类,但在解释诗句上赵注从全诗意象出发,不作胶柱鼓瑟之论。他说:“鹄高五尺,宜高远引,乃推藏低徊,化作白凫之状,象老翁之伛偻,天寒岁暮,困于波涛之中,忍饥西东,无所投迹,此贤者失所之譬也。”“前六句盖公自况,末两句念及同志之人。”再比较一个高登的解释,他认为此诗是:“闵贤者降于黎庶,而不贤者冒名器也。”“黄鹄而化为白凫,贤者降在黎庶也。”然后分解诸句,认为“故畦”二句言“贤者无禄食”,“鳞介”二句言:“贤者不苟禄,而时乱不安其居也。”“鲁门”二句言:“以不贤者冒名器,蹭蹬宜也。”可见高登解说诗句指向太具体,因而破绽百出。赵氏反问道:“以黄鹄为君子,白凫为黎庶,此何所据,于义何取乎?”特别是结尾二句,诗人立意在同情“鶢鶋”,而高氏认为是指斥,并把它视作“不贤者”的象征。所以赵次公说:“所谓亦蹭蹬,义在亦字之悯同类也。”两相比较,高下自见。
传统论人,喜欢把人分作两极。宋代儒者更好谈论君子小人。杜甫在宋代是被视为抱道自守的儒者的,因此人们认为他的大多数作品是表彰君子、指斥小人的。而杜甫有许多描写自然风光与日常生活的作品难作此解,
他们便搬出比兴这个大题目,歪曲杜诗,使合己意。惠洪在《天厨禁脔》中论及比兴法时列举杜诗三联:“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野外》现称《江村》);“不分桃花红胜锦,生憎柳絮白于绵”(《送路六侍御入朝》);“不如醉里风吹尽,可忍醒时雨打稀”(《绝句》)。并言:“三诗皆子美作也。妻比臣,夫比君,棋局,直道也,针合直而敲曲之,言老臣以直道成帝业,而幼君坏其法。稚子比幼君也。锦、绵,色红白而适用,朝廷用直材,天下福也,而直材者忠正;小人谄谀似忠,诈讦似正。故为子美所不分而憎之也。小人之愚弄朝廷,贤人君子不见其成败则已,如眼见其败,亦不能不为之叹息耳。故曰‘可忍醒时雨打稀’。”这段妙论简直如痴人说,次公曾把它们引入自己的注释中,使读者见识一下这种怪论的可笑。
解诗不能抓住一句两句,胡乱发挥,应该从全篇出发,特别是涉及到诗中是否有寄托、是否运用比兴等问题,更要考虑到作品通篇之意。如《江村》一诗分明是写诗人在草堂夏日中悠闲生活,描绘出浣花溪畔,江流曲折的恬静幽雅之景象。惠洪真富于想象力,竟能从老妻想到君臣,从棋局、钓钩想到直道、曲道。赵氏批评惠洪的文字虽未流传下来,然而他对此诗的解释被“九家注”辑录了一部分。他说:“公闲居诗,每道实事。”“老妻”二句义为“妻为棋局以弈,儿作钓钩以钓”。他正是从《江村》的全篇出发,不承认惠洪所说的比兴。另外比兴也不能滥用,一般说什么物象象征什么都是有源流传统的,如果诗人要自出机杼,那是要在诗中说清楚的。赵氏在注《送路六侍御入朝》时批评惠洪说:“不知于桃花、柳絮何所据而便比谄谀奸讦之小人乎?”《绝句》一诗前二句为“楸木清香倚钓矶,斩新花蕊未曾飞”,赵氏指出楸木是真材美物,从其语气看也是对其赞美有加,而不可能用以譬喻“小人之愚弄朝廷”。其他如:“门外鸬鹚久不来,沙头忽见眼相猜。”惠洪解释为“言贪利小人畏君子讥其短”,将“会须上番看成竹,客至从嗔不出迎”,释为“惟守道为岁寒也”。一些注释者把杜甫许多描写大自然、揭示自然与人的和谐关系的诗句皆视为用以比喻社会伦理的作品,使得丰富多彩的杜诗艺术变得单调而枯燥,亦背离了作品本义。对于这些,赵氏除了在注释中随时纠谬外,还在《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诗题解中说:“近世学者于杜公诗,每以君子、小人分解其诗句。如‘市桥官柳细,江路野梅香’;又如‘麝香眠石竹,鹦鹉啄金桃’。皆以为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者。次公于丙帙成都《西郊》诗尝论之矣。”这段“论”一定很精彩,可惜未能流传下来。
赵注的平实准确不仅表现在廓清解杜中的穿凿附会上,而且其解释文字也不拖泥带水,语言通俗,多用当时口语,这些从我们上面所引文字即可看出。杜诗中有些极尖锐的诗句,或指摘皇帝,或怒斥当道,往往突破了温柔敦厚的诗教。这些是不符合儒家规范的。一些注者或为尊者讳或为了正面引导读者,往往要把话说得圆转一些。而赵注不是这样,他按照自己的理解,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如赵注《前出塞》、《后出塞》,皆直接写明“此讥好大喜功之主也”。后人或说“刺开边”,或说“遏人主喜功之心”,很少象赵氏说得如此直接明白。后世还有人将此改为“讥好大喜功之士”,不仅文不对题,亦可见琐屑文士为尊者讳之心态。其他如《麂》最后两句“衣冠兼盗贼,饕餮用斯须”,赵注云:“末句言衣冠之人,行如盗贼,惟知饕餮而已。故使人多害生物,用以充疱,止在斯须之间。然则公之仁心于物,乃不避忌讳矣。”我们再对比一下仇兆鳌注:“衣冠乃食肉者,盗贼乃捕兽者,徇口腹之欲,而戕命于斯须,则衣冠亦等于盗贼矣。此骂世语,亦醒世语。”另一首《东屯北崦》首句:“盗贼浮生困,诛求异俗贫。”赵云:“人之所以为盗贼者,以浮生之困也。《管子》曰衣食足而知荣辱。谚云:盗贼起于贫穷。观下句则所以招盗之因也。”浦起龙注云:“惟‘盗贼’故‘诛求’,惟‘诛求’故‘俗贫’,意相因也。惟因盗贼而我生转徙,且因转徙而见此俗贫,事相因也。‘盗贼’泛指。”除了思想上差距外,仇注浦注虽然也表述了他们的意见,但给读者的印象是语意含混,不够明确,似乎在躲躲闪闪。而次公注则痛快淋漓、直截了当,没有任何顾忌。因此,赵氏注本虽较原始,但后世注杜者并非在任何方面都超越了它。
三
关于杜诗的编年,宋人作了很多工作。今天我们能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杜诗准确地编排在杜甫一生中的各个阶段,其功劳主要属于宋人。钱谦益对此持否定态度,他说:“纪年系事,互相排缵,梁权道、黄鹤、鲁訔之徒,用以编次后先,年经月纬,若亲与子美游从而籍记其笔札者。其无可援据则穿凿其诗之片言只字,而曲为之说,其亦近于愚矣。”(《注杜诗略例》)“穿凿其诗之片言只字,而曲为之说”,当然是错误的,但如果说未能“亲与子美游从而籍记其笔札者”,就无法弄清杜甫诗歌的写作年代,那么还要考证作什么用呢?实际上杜甫诗歌中的绝大部分写作年代还是被考证出来了。在这方面赵次公作的工作尤多。赵注不仅细致地为杜诗编年,有些甚至精细到季度、月,而且还对杜甫生平经历有所订正。例如兖州省父一般皆定在开元二十五年(737),其根据就是《登兖州城楼》的“东郡趋庭日,南楼纵目初”。赵次公对“纵目初”作了新的解释:“纵目初,则追言儿童时耳。”其根据是其晚年在夔州《热》诗所写:“何似儿童岁,风凉出舞雩。”“舞雩乃是兖州,公未尝泛用事”,由此可知其省父当在儿时,开元二十五年所写《登兖州城楼》已经是再度至兖了。《杜诗话》言此诗是:“十五岁(开元十四年)作,时公父为兖州司马。”虽然对此诗写于何时有不同的意见,但都是认为甫父杜闲任兖州司马是在其少年期间。
对于杜诗编排作到“年经月纬”的是赵次公。赵注之前有《纪年编次》,又有卷首与诗题下系年及句解所征引之史实,这些为每首杜诗作了详细的编年,其细致深入,超过宋代诸家。杜甫自秦州以后,行踪清晰,每至一地皆有大量的诗作,而且在每一地停留时间皆不太长。赵氏先考证某诗作于某地,据地以定其年份,然后再据诗中所反映了物候定其季节月份,例如《滟滪》作于夔州自不待言,而且是作于初至夔州时,因为杜初到夔州居西阁,在白帝城下,每天都可以看到白帝城下江心的滟滪,此时为大历元年(766)。赵云:“此篇与下篇之《白帝》一首皆夏秋诗也,不合混在秋诗中。何以言之,郦道元《水经注》云:‘水门之西,江中有孤石为淫滪石,冬出水二十余丈,夏则没,亦有裁出矣。’此诗首句为:‘滟滪既没孤根深,西来水多愁太阴。’秋天水位渐退,不应有此景。”因之,此诗定于大历元年夏末或初秋作。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许多。
编年与解释诗意关系密切,只有对杜诗内涵作出正确的解释才能对该诗作出准确的编年;同样,只有在准确的编年的基础上才能对该诗作出正确的解释。高登以及宋代许多注家对杜诗荒谬的解释,其中有的就是未能对该诗作准确的编年。如《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旧编与仇注皆将其编在秦州诗内,作于乾元二年(759)。赵次公编于潭州(今长沙)诗内,写于大历四年(769)。从题目上看,作于秦州(两当县在秦州至同谷之间)较合理,可是详味诗中“借问持斧翁,几年长沙客?哀哀失木狖,矫矫避弓翮”,如写于秦州,当时距吴郁(吴十侍御)贬谪最多亦不过两年有余,与诗中感慨不合。另外“哀”二句形容吴之忧谗畏讥、为避祸谨慎小心情态,亦非未见吴郁的悬想之词。因之,赵之编年是较准确地把握了诗旨的。
四
赵次公注自南宋中叶以后逐渐亡佚,这可能因其卷帙太繁(赵注有罗嗦的毛病,有些注文屡屡重出),不适合市场需求,其后嗣又无高官显贵,未能重刊,日久遂湮没无闻。明末的钱谦益之饱学与藏书之富,竟说赵注“边幅单窘,少所发明,其失也短”(《注杜诗略例》),可见他也没有见过赵注。五十年代以来,大陆学者十分重视杜甫,但在八十年代以前,人们也很少关注宋代的杜诗研究,更无论赵注了。
自萧涤非先生于七十年代末领导杜甫全集校注以来,广泛考查了历代研究杜诗的成果,看到了杜甫草堂所藏清初所抄《赵次公杜诗先后解》之残帙,高度评价赵次公注。八十年代中当林继中同志成为他的博士生时,便指导他完成了《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使得赵次公对杜诗学的贡献大白天下,见为次公之功臣。
继中同志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一、力图恢复赵书的原貌。现存赵书两个残本,大体相同,皆从丁帙开始(我们认为是从丁帙下半部分开始),甲、乙、丙三帙全佚。虽然,郭知达所编《九家集注杜诗》中保留了较多的赵注,可是《九家注》是古今体诗分编本,与赵书残帙的编年体例不同,前三卷必须重新编次。于是继中同志考虑到《百家注》本后部分编年与赵书残帙大体相同,于是将“前三帙分卷参考《百家注》目录所标示之时地,兼及篇幅长短酌定”(见辑校本《凡例》)。有的篇目赵注中点明在某帙某卷,则依赵注。赵原本有的诗题目亦与《百家注》本不同,则依赵本。如丙帙卷十的《自阆州领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据丁帙卷五《寄董卿嘉荣十韵》题解说此诗原“在《归赋蜀山行》之下”。尽管这个题目没有《自阆州……》更符合诗意,但也遵照赵的意见将题目改为《归赋蜀山行》。前三帙的注文采自《九家注》中的赵注,并校以《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与《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分门集注杜工部诗》、《黄代补千家集杜工部诗史》等等书中的赵注。这是一个十分繁琐费力又很难见巨大成效的工作。其实“十家注”、“百家注”、“千家注”、“分门集注”,除“千家注”有黄希黄鹤父子之补注外,其他注文都是辗转相抄而来,而书贾为了欺骗读者,制造些小异,如将一长注割裂数段,分属多人,以增加注者数目,给人们“百家”或“千家”的假象。又如将注者次序颠倒,给读者以新鲜感,使人不易觉察其抄袭,这些都给校辑者带来许多困难。继中同志以细致和刻苦的工作,解决了这些问题,使得已佚的赵书甲乙丙三帙得以恢复其大部分原貌,产生了这部最接近赵书原编之旧的《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这是继中同志对杜诗学研究的最大贡献。
其次是《辑校》通过大量校语(萧涤非先生在《辑校》序中说八百余条,出版时有所删订)使读者了解到各种注本中赵氏注文之异同及赵注本身的不足与缺欠。搞杜诗研究工作的人们了解到赵注的重要后,想要弄懂弄清赵注还是十分困难的。清以前,特别是宋注本无不引“赵曰”或“赵叟曰”,繁多零乱,不知其异同,更难了解其来龙去脉。继中同志在整理赵注残本的同时,把众多集注本中的赵注作了比较,确定了孰先孰后,谁最接近原本,谁在引用时做了手脚,眉目清晰,读者使用十分方便。另外,还辑得《九家注》与《先后解》残帙所失载的赵注佚文,使之更为完善。
赵注并非十全十美,其不足也很明显,大要有三:一,很少深入细致分析杜诗的思想艺术;二,注文重复,如仅在丁戊己三帙中关于《桃花源记》的典故就引用了五六次之多;三,引用典事越常见越易出错,估计赵氏仅凭记忆未复核原书之故。前两点不足校辑者无能为力,在第三点上继中同志为之作了许多更正,并写入校记之中。如《赠李白》赵注“蔬食每不饱”引《孟子》:“虽蔬食菜羹,未尝不饱也。”林在校中指出《孟子》原句当作:“虽蔬食菜羹瓜祭,必齐如也。”这种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赵注的不足。至于残帙传抄过程中的谬误,《九家注》中所引赵注的讹夺衍倒,校辑者皆能细加剖析,予以纠正。许多较简单之处并未都写入校记。总之,《辑校》一书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恢复了赵书的原貌,而还提高了赵书的质量。
第三,《辑校》长篇前言也是杜诗学研究的一篇重要成果。该文长达两万字(在《中华文史论丛》发表时长达三万余字),文中不仅考证了赵次公其人和其书原貌以及刊刻流传的情况,而且研究了杜诗集在北宋与南宋之初刊刻流传和注释,并确定了赵次公注所用底本是与吴若本相近的注本(此本之注,次公常称之为“旧注”,《钱笺》所用底本也有“旧注”,而且两者相近),并将从王洙所编《杜工部集》到赵注、《九家注》、《十家注》、《百家注》、《分门集注》、《黄氏补注》等演变过程以图表形式固定下来,十分清楚。当然,关于这个“源流示意图”,还会有争议。但是继中同志是根据对各种集注本中所引赵氏注文的分析比较才确认了各种注本的演变轨迹,他的意见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前言》还确认蔡兴宗、蔡伯世为一人;杜田、杜修可、杜时可为一人。这些曾经注过杜诗的宋人,因为其名不见经传,常给研究宋代杜诗学者造成混乱,过去也有人怀疑他们本为一人,由于继中提供了确凿的证据才得以确定下来。这些可视为校辑者的副产品了。
注释:
全诗为:君不见黄鹄高于五尺童,化作白凫似老翁。故畦遗穗已荡尽,天寒岁暮波涛中。鳞介腥膻素不食,终日忍饥西复东。鲁门鶢鶋亦蹭蹬,闻道如今犹避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