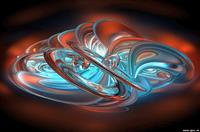“说唐”小说系列在民间流传是极其广泛的。这个故事中的主人公秦琼、程咬金、徐茂公等为人所熟知的程度,恐怕不在宋江、李逵、鲁智深、武松、吴用、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等人之下,因此,它对民众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从古至今最大的游民组织天地会,其建立所依据的三部通俗小说就是《小浒传》、《三国演义》与“说唐”小说系列。他们从这些作品汲取思想、获得反抗社会的勇气,这些书中所表现的行为理念则成为他们思考问题的价值模型。
1.“说唐”小说系列的构成及其早期作品
本文所说的“说唐”小说系列是指取材于隋末群雄并起,天下大乱,秦王李世民(唐太宗)削平群雄,建立唐帝国的历史通俗小说。隋末唐初是个“讲史”的好题材,隋炀帝的贪酷暴虐,古来少有;唐太宗的英武好贤、体恤下情也是十分罕见的。特别是他所建立的唐帝国是古代中国人民的骄傲,其创建过程中充满了传奇色彩,不仅唐代笔记和传奇对此有大量的描述,即使正史亦间有记载。这些都为群众所喜闻乐见,艺人也能够有根有据地进行发挥和艺术创造。
以隋唐之际历史为题材的平话很早就产生了。元代文人王恽有几首歌咏说书的词,如《鹧鸪天?赠驭说高秀英》“短短罗衫淡淡妆,拂开红袖便当场。掩翻歌扇珠成串,吹落淡霏玉有香。由汉魏,到隋唐。谁教若辈管兴亡。百年总是逢场戏,拍板门锤未易当。”另外《浣溪纱》中亦有云:“隋末唐初与汉亡,干戈此际最抢攘,一时人物尽鹰扬。褒、鄂有灵毛发动,曹、刘无敌简书光。争教含泣到分香。”“褒”公为段志玄,“鄂”公为尉迟敬德,均为李世民麾下的重要将领和功臣。从这两首小词可见隋唐之际的历史是平话艺人喜欢讲述的段子,而且他们在演播这段历史故事时是偏重刻划历史人物的,也就是说走的是英雄传奇的路子,这是从吸引听众出发的。但是从现在所存关于这段历史的小说系列来看,则有重历史事实和重英雄人物两条路子。一般说来,平话演说艺人注重人物形象的传奇性,他们据以演说的底本多虚构成分,多荒诞的情节,较为口语化;而文人的修订本则多采撷史籍,注重历史上的真人真事。
“说唐”系列就现存的小说来说大致包括《隋唐志传》(下简称《隋唐》)、《唐书志传》(下简称《志传》)、《大唐秦王词话》(下简称《词话》)、《隋唐志传通俗演义》(下简称《通俗》)、《隋史遗文》(下简称《遗文》)、《大隋志传》、《隋唐演义》(下简称《演义》)、《残唐五代史演义》、《说唐前传》(下简称《说唐》)、《说唐后传》、《说唐三传》、《瓦岗寨演义传》以及《五代残唐演义》,如果再加近代评书艺人演说的记录稿如《兴唐传》、《兴唐后传》、《忠义响马传》、《薛家将》、《薛刚反唐》、《罗通扫北》等等,可以说有数十种之多。这些通俗小说题材相同,但是其侧重点不同、主题有区别、人物形象塑造上也大有差别,其间的种种异同反映了作者的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取向。我们通过对这个系列故事的演变的比较,可以看出许多在中国通俗小说史上应予注意的问题:例如这类历史题材的小说可大体分作两个系统:编年讲史与英雄传奇——文人与游民知识分子对于历史事实认知与表现上的差异。
在诸多说唐故事的传本中,现在仍有明代刻本传世的是上述的前四种,即《隋唐》、《志传》、《词话》和《通俗》。最早的是嘉靖时清江堂刊本《唐书志传》,其它三种皆有万历刻本。这四种本子也表现出两种倾向,即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相背离倾向。《隋唐》与《词话》离历史较远,其中多荒诞不经之言。《隋唐志传》未见,但孙楷第的《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和柳存仁的《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中皆有所论证。夏志清在为《隋史遗文》台湾版写的序中也说“《隋唐两朝志传》第七十二回‘黑闼箭射罗士信’,正史里搀入了说书传统的材料,叙述较详。《词话》与此情节大体相似,因此,孙楷第认为《志传》出于《词话》。柳存仁虽然不同意这种意见,但这两书属于同一系统是不能否定的。
与《隋唐》、《词话》不同的是,《唐书志传》和《隋唐志传通俗演义》则竭力向史书靠拢。这两部书简直就是敷衍《资治通鉴》而成,有些段落直取《通鉴》原文,只是稍加变动而已。不仅如此,《志传》和《通俗》还在每卷之首注明此卷取某年至某年之事。如《通俗》第一卷便标明“自隋文帝仁寿四年改炀帝大业元年起,至大业十三年,迄于恭帝侑义宁二年,共十三年事”。第二卷“起隋恭帝侑义宁二年即唐高祖武德元年,止隋越王侗皇泰元年,首尾凡一年实事”。这种写法简直与史书一样。《志传》甚至还直录《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的评语和《纲鉴易知录》中的“纲目断云”。从中可见小说作者与浪迹江湖的游民知识分子不同,他们不太考虑小说的读者与听众面的广狭问题,不注重这类作品可接受性的问题,而是一味地向史书靠拢。因此孙楷第对这类作品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他说:“小儒沾沾,则颇泥史实,自矜博雅,耻为市言。然所阅者不过失子《纲目》,虽洓水《通鉴》亦未暇观。钩稽史书,既无其学力;演义生发,又愧此槃才。其结果为非史抄,非小说,非文学,非考定。”(《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
《隋唐》、《词话》则近于孙楷第所说是“市人揣摹”出的作品,也就是本文提出的是游民知识分子的创作。这些人“勇于变古,唯其有变古之勇气,故粗糙而尚不失为活泼”。《隋唐》未见,不能妄论。《词话》在叙事上已经偏离了《资治通鉴》的编年史系统,它基本上是按照秦王李世民的活动为主要线索加以演义铺排,紧扣住世民协助李渊于太原起兵和统率大军东征西讨,逐个削平群雄取得一统天下的过程,很少枝蔓。然而,它也只是在不照抄史书这一点上体现出艺术上的进步,至于书中大量采用的民间传说和神话,则十分粗糙可笑。如书中有若干未卜先知的人物,如李靖、徐茂公等,无论是取胜还是失利都能预测到,那么为什么不主动堵住造成失败的漏洞呢?“这是天数”,这就是作者对历史进程极简单的并且十分可笑的解释。真龙天子李世民,每当遇到磨难就会有上天关注,千篇一律很少变化;其它如天降飞鼠把李密粮食搬运走、六丁神教尉迟敬德兵书战策、桓法嗣设坛借神兵等情节大讲怪力乱神,这些虽然比照搬史书要有点儿创造性、要生动一些,然而由于这些游民知识分子知识浅陋,其历史观比所谓的“小儒”更为粗浅,所以其构思简单、单调,前后矛盾,还有许多极不合理与十分可笑之处(如一写到行军打仗就是夜间偷寨劫营)。因此,从艺术上来说,明代这四个“说唐”系统的小说都属于初级阶段,其水平是不高的,而且仍然没有完全脱离编年讲史系统。
《隋史遗文》的出现是“说唐”小说系列的重要转折。它是“说唐”系列从“讲史”到“英雄传奇”转变过程中第一部有代表性的作品。它仅刊刻过一次,即在崇祯癸酉(1633)。不过在此书之前一定还有一个“旧本”。《遗文》的批语里常常提到此外还有一个“旧本”或“原本”,如第三回“总评”有云:“旧本有太子自扮盗魁,阻劫唐公,为唐公所识,小说也无不可。”在三十五回的“总评”中两次提到某情节“原本”没有,或“原本”作某,此本做了改动。而且,这个“旧本”或“原本”,当是说书人依据的底本。孙楷第也持此意见,他在《大连图书馆所见小说书目》中言及“旧本”时说:“唯观其吐属气息,诚有如于令所谓‘惊里耳而不谐于情,快俗人而不根于理’者。与其谓为文人著作,毋宁认为市人之谈。如此书固以全力写秦叔宝一人者,而所记叔宝之态度见解,乃与细民同科,豪迈不群之气,甚嫌其少,其规模气象,尚不及梁山泊武二诸人,乃以貌凌烟阁上之胡国公,亦厚诬古人,不称之至矣。余意韫玉才人,其技当不止此。或本市人话本,韫玉为润色之。考余淡心《板桥杂记》有‘柳敬亭年八十余,过其所寓宜睡轩,犹说秦叔宝见姑娘’之语。敬亭所说,以罗彝妻为叔宝姑母,正与此书同。则此书秦叔宝诸人事,盖是万历以后柳麻子一流人所揣摩敷衍者,于令亦颇采其说而为书耳”。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所出版《隋史遗文》的校点者宋祥瑞也说:“从袁于令在序文中对旧本的批评看,可以推测旧本比较通俗,适合读者喜欢故事热闹奇幻口味,这很可能与说书人有关。说书人为引人入胜,常采取各种传闻、记载、小说加以敷衍。”又说:“说书人讲故事,有人据以记录或改写,大概即袁于令所说的原本或旧本。”(见《隋史遗文》所附《袁于令和〈隋史遗文〉》)夏志清更进一步论断说:“袁本《隋史遗文》刊出前,市面上已有了更接近说书传统的刻本。”“但事实上,唯其《隋史遗文》布局设计这样精细,绝不可能是一位文人的独创,而是好几代同一地区说书人的心血结晶。”“很可能袁于令从一位说书人手里拿到了《隋史》的话本,先把它印出来,这就是袁氏在好多则‘总评’里所提到的‘原本’、‘旧本’。后来因为书销路很好,袁自己花了气力再把它增改加评重印。”因此,考之原书,这种推断是合理的。可见“说唐”系列从“讲史”到“英雄传奇”的演变是由说话艺人完成的。
《遗文》完全改变了《隋唐》、《志传》等书的写法。虽然,它仍然是写唐取代隋的历史,但是,却以秦琼生平活动为主线,生动刻划了秦琼、单雄信、程咬金、罗成等艺术形象。前面说过,说话艺人要取悦听众,不可能只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演说。这样会导致形象干瘪、情节单调,缺少生活气息;如果以人物的符合其个性的行为和具有戏剧性的遭遇为线索安排情节,那么这部作品便能构成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从而受到听众的欢迎。这一点在《词话》中已露端倪。不过《词话》作者选择的不是秦琼,而是尉迟敬德。在敬德出场时介绍了他牧羊出身,被乡人资助从军,又通过他“伏铁妖”、“降水怪”等情节突出其神勇的一面,但这在全书中不占主导地位,只是一带而过。《遗文》之中,作者把书中主要描写人物换成了在唐开国武将中地位仅次于尉迟敬德的秦琼,其原因可能是他跟随李世民更久,传奇经历更多。从他晚年自称“吾少长戎马,所经二百余阵,屡中重疮。计吾前后出血亦数斛矣,安得不病乎?”(《旧唐书》本传)这种悲壮的经历也易于激动作者与听众的心灵。《遗文》把隋唐史改编为秦琼的传记,这是它最大的变动。
应该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遗文》秦琼形象的描写和叙述上是有矛盾的。例如在第三回秦琼出场而介绍他时言秦琼“到十二、三岁时,便会打断街、闹断巷生事”,又言他“最懒读书,只好抡枪弄棍,厮打使拳;在街坊市上,好事抱不平,与人出力,便死不顾”,是带有草莽英雄特点的人物,也是江湖艺人们最为熟悉的游民中的精英人物。可是从小说情节的发展中,秦琼的士大夫色彩越来越浓。例如他向往隐居生活:“若不得志,有这几亩薄田,几树梨枣,尽可以供养老母,抚育妻儿。这几间破屋中间,村酒雏鸡,尽可与知己谈笑。”他的处事原则,特别谨小慎微,注重一个“忍”字。他在潞州落魄时对势利小人王小二的态度、在破劫皇杠案时对县官的委屈求全,在与齐国远游长安时的种种想法,以及念念不忘对他颇有恩遇的隋朝上官等等,都表现出文人士大夫的为人处世原则。在他为李密出使唐朝时,因他对李渊有恩,李世民再三挽留,他垂泪说:“秦琼武夫,荷蒙公子德意,怎不知感?但我与魏公相依已久,已食其禄,一旦背之不义;出使不复,不信;贪利忘恩,不仁。不仁不义不信之人,公子要他何用!”这完全是儒家的道德观念,与游民是不相干的。这是袁于令对于旧本的修订的结果。旧本因是江湖艺人说书时用的底本,他们是用游民眼光看待隋唐之间的变革和在此期间所产生的英雄人物的;而作为文人士大夫的袁于令认为这其中有的是属于“传闻之陋,过于诬人”的,并且“悉为更易”,因而才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然而,《遗文》全书的故事体系、整个结构与主题思想还是被游民知识分子确定下来的,并且“英雄传奇”的故事体系使得《遗文》更富于文学性,作为对通俗文学特别具有鉴赏力的戏剧家袁于令不可能对旧本作根本的改动,因而新本子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如果说“说唐”小说系列的讲史阶段主要是讲建立新朝之不易;而《遗文》则是讲当统治者腐败糜烂的时期,
反抗、造反便具有了合理性。在第十八回开端便说:“如今人最恼的无如强盗,不知强盗岂没人心?岂不畏法度?有等不拿刀斧强盗,去剥削他、驱迫他。这翻壮士有激胡为,穷弱苟且逃死,便做了这等勾当。”作者在议论中犹称起义者为“强盗”,但在具体形象的描写上则几乎是完全的肯定;不仅对秦琼参加瓦岗军是这样,即使在描写尤俊达、程咬金劫皇杠、王薄聚众起事、刘霸道被迫造反、被冤杀一家后的窦建德投入武装起义的队伍等,作者都采取了同情的态度。这虽然是江湖艺人们的游民性质所决定的——游民群体的天然的反社会性,使他们对反抗既存秩序的人们容易产生共鸣,但也与士大夫的修订有关,他们的帮派意识比较少,所以把游民的反社会行为化作为追求普遍的正义而进行的奋斗。正是由于底本出于游民之手,作者把书中的敢于走上叛逆道路的人们加以改造,把他们平民化,甚至游民化。历史上隋唐改朝换代之际,许多英雄都是贵族出身,有些还在隋朝作过官。江湖艺人却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他们钟爱的英雄人物变成与听众、或与说书人类似的人。例如史书记载秦琼“少长戎马”;程咬金曾“聚徒数百,共保乡里,以备他盗”;徐世勣则是“家多僮仆,积粟数千锺”的豪富。对这些起兵反隋而争天下的所谓“山东豪杰”,陈寅恪在《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一文中指出,他们实乃是一群胡汉杂糅,性格勇强,工骑射,善战斗,务农业而又有组织的集团。然而在《遗文》中,他们都变成游民或接近游民的角色。秦琼成了历城县的小吏;程咬金则是无业游民;徐世勣变成云游四方的道士。这种改动不仅使得听众易于接受,而且书中主人公“发迹变泰”的过程,正反映了江湖艺人的个人追求和社会理想。从而也使得生活在下层社会的人们和一无所有的游民羡慕不已,在心理上获得一种满足。
因此可以说,《遗文》是以游民知识分子的创作为底本,经过文人的修饰,共同完成了脱离讲史轨迹的过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小说,而且基本保留了游民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
3.作为游民知识分子作品的《说唐》
《遗文》对已经不传于世的“旧本”或“原本”的修改,使得原书中由于说书人参与创作而渗入的游民意识受到削弱。在《遗文》出版后六十二年,褚人获的《隋唐演义》出版了(《遗文》仅在明崇祯六年(1633)刊刻一次,《演义》初刊于康熙三十四年——1696)。褚氏是袁于令的同乡后辈,其著《演义》受到袁的影响是很自然的。他在序中说:“昔箨庵袁先生,曾示予所藏逸史,载隋炀帝、朱贵儿,唐明皇、玉环再世姻缘事,殊新异可喜。因与商酌,编入本传,以为一部之始终关目。合之《遗文》、《艳史》,而始广其事,极穷幽仙证,而已竟其局。其间阙略者补之,零星者删之,更采当时奇趣雅韵之事点染之,汇成一集,顿改旧观。”这个“旧观”是包括《隋唐》、《志传》、《遗文》以及《遗文》之“原本”等书而言的。使原来近于话本的《遗文》进一步文人士大夫化。特别是褚氏从齐东野人等文士创作的《隋炀帝艳史》(下简称《艳史》)中吸取了许多情节,有的甚至是照抄原文。这样,把原本已经基本上脱离了讲史系统而转向了英雄传奇的《遗文》,变成了传奇与讲史的杂糅。《演义》在内容上基本上是隋炀帝的荒淫史、唐朝的开国史和秦琼、程咬金等下层人物发迹史的拌合,缺少统一而明确的主题,全书风格也不统一,因此它在艺术上也不是十分成功的。虽然《演义》刊刻多次,但是江湖艺人在演说时不用它作底本,就是因为这三条线索很难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说书人用的底本是《说唐》。乾隆四十八年(1783)刻本署名“鸳湖渔叟校订”,前有“如莲居士”写于乾隆元年(1736)的《序》。这个本子内容就比较单纯了,它主要是以秦琼、程咬金、单雄信、罗成、王伯当、徐茂公等人传奇经历为线索,展示了他们的英雄性格以及在社会大动乱时期他们的人生选择。书中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游民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和历史观。我在《〈水浒传〉的主导意识——游民意识》(《文学遗产》1994,5)一文中曾指出:作为封建宗法社会的零余者的游民,他们在群体性格与思想意识上和宗法社会中过着较为稳定生活的士农工商有很大不同,他们对既定的社会制度不满,甚至反抗既存的社会秩序,在封建社会各个阶层里,游民最富于进击精神;他们注重眼前利益,不甚关切与实际利益无关的东西;他们脱离或背离主流的意识形态,不能或不愿遵守儒家思想对于社会成员的规范;为了生存,游民必须要结成团体,他们推崇和信仰游民群体的纽带——义气。由于《说唐》是说书人集体的作品,而说书人是浪迹江湖的游民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意识不能不反映到小说中去。《说唐》在《遗文》原本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把其中的主人公游民化。而且书中最精彩、最感人的情节正是游民行为、游民道德观充分表现的时候。如秦叔宝落魄潞州卖骏马、绿林豪客单雄信挥金全义友、程咬金卖柴扒、咬金劫皇杠、秦琼烧捕批牌票、贾家楼结拜、瓦岗寨举义等等;至于那些谋臣用计,武将交锋,战场取胜,宫廷政变反而没有什么意思。这与作者对所写生活熟悉程度和对所写内容倾注的力量有关。游民的生活和性格是他们最了解的,至于上层社会的活动以及帝王和高官的思想感情则多靠猜测与推想。
《说唐》中一号主人公还是秦琼,这点与《遗文》相同,但是它大大增加了二号主人公程咬金的故事,甚至让他当了三年瓦岗寨的假皇帝——混世魔王。这是毫无历史依据的。为了编造这个情节,作者甚至割舍了瓦岗寨第一任真正的领袖翟让及其事迹。这个情节具有象征意义,作者让程咬金这个不折不扣的游民登上封建时代的顶峰,正代表了游民群体的期望与理想。作者特别钟爱程咬金这个形象,因而对于他的一言一行作了十分精彩的描写。程咬金的经历是卖私盐、当响马、作假皇帝,而且自作响马以后,响马就成了他的专业了,只要一当不成官,就回到本专业,作响马去了。而且,他处处以响马(响马乃土匪之别名)自居、自豪,毫不以作响马为非、为耻。后世说书人甚至把《说唐》直称为《响马传》,甚至再加上“忠义”二字以褒美,与此书精神是一致的。程咬金许多蛮不讲理的行为(如卖私盐、卖柴扒时的强买强卖),作者都抱着欣赏的态度去写,表现出他们的立场与价值取向。在这一点上,它甚至超过了《水浒传》的作者。《水浒传》中的宋江还带着一些士人的特点,如忠君意识、忍让精神以及舞文弄墨、吟诗作赋等等,而《说唐》中的程咬金则没有一点文人士大夫气味,甚至一字不识,完全是个不折不扣的游民。而他却一度登上了帝王的宝座,实现了游民的最高向往。《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在大闹天宫时所说的“皇帝轮流作,今日到我家”正是把游民这种最高向往神话化了,表现出他们与现存社会秩序的对立和敌视,以及政治上的主动进击精神,与有严格君臣之分的封建时代的儒家主流意识形态是大相悖谬的。
游民注重小团体,结拜是他们最原始的结合方式,在此基础上他们还要组成更大的团体。《说唐》中最感人的一幕就是贾家楼结拜,《遗文》中是没有这个情节的。《说唐》还增加了程咬金再劫皇杠,被杨林抓起来,贾家楼盟兄弟为了援救结拜兄弟便在济南仓促起义。这不是生活中的偶合,而是出于小说作者的设计。当时游民已经有了自己的秘密团体,这一点在《遗文》中就有所反映:书中把单雄信写成秘密会社的首领,当王伯当通知单九月二十三要为秦琼母亲拜寿时,单雄信拿了两支令箭去通知自己的拜盟弟兄。褚人获的《隋唐演义》照抄此情节,在此回之后评曰:“单雄信邀集朋友,却用令箭,一奇也。”又说:“此都是无中生有,忙处无漏笔,闲处有补笔,细心点染,看者幸勿草草忽过。”把地下秘密组织的联系方法称之为“无中生有”或仅仅是一种制造情节迭荡的笔法,说明了文人士大夫对游民的秘密活动是不甚了解的。《说唐》的作者因为是浪迹江湖的游民知识分子,就对这类事情是十分熟悉。他在写到单雄信听了王伯当的通知后“说:‘原来如此。如今事不宜迟,即速通知各处兄弟,同去恭祝。’说罢,即取绿林中号箭,差数十家丁,分头知会众人,限于九月二十三日,在济南府东门会齐。如有一个不到,必行重罚。”从单的口吻到行为以及号箭的作用都可以看出雄信领导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社会的游民秘密组织,这种秘密组织在明代已经存在了。《明熹宗实录》记载天启三年汪元洪组织“票党”,他与多个和尚结为异姓兄弟,北方五人,以仁义礼智信为号;南方五人,以金木水火土为号。他们通过散发票符发展党徒,从事秘密反明活动。其次天启三年泉州又出现了“一钱会”;崇祯间苏州地区游民结有“天罡党”,湖北麻城有“里仁会”等等(见赫治清所著《天地会起源研究》)。这些正是江湖艺人描写单雄信等人秘密活动的生活基础。
《说唐》之中游民向往的归宿是瓦岗寨,它是单雄信领导的秘密组织逐渐壮大与公开化的结果。隋末群雄并起,有所谓“十八路反王,六十四路烟尘”,作者都称之为“贼”。他所肯定的只有瓦岗寨,只是因为作者心目中的英雄大多在瓦岗寨中,于是便把他们写得在轰轰烈烈的反隋斗争中独树一帜、大逞威风(天地会会众特别羡慕瓦岗寨威风)。这一点在《兴唐传》、《忠义响马传》等评书演播记录本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前面说过游民的帮派意识特别强,这也反映到《说唐》之中。他们以瓦岗寨为坐标,特别是在程咬金作混世魔王时期的瓦岗寨,它象《水浒传》中的梁山一样,是游民心目中的圣地。凡是拥护、帮助瓦岗寨集团的,作者就肯定,反之则否定。这与“说唐”系列中的讲史作品只肯定当朝的统治阶层,而把其它与隋、唐对抗的政治和军事力量都视为叛逆反贼是大不相同的。它反映了文人士大夫与游民在思想意识上的差别。
复仇本来是生活在注重血缘关系的社会中人们的道德准则,可是作为当时社会主流的儒家思想又认为中庸是天下之“大德”,不会把复仇的原则推到极端,因此他们又有“犯而不校”、“以德报怨”等调合主义作为补充。而脱离了主流社会的游民则不愿意接受中庸之道,他们习惯把事情推到极端,在这点上是与游侠一致的,游侠便把复仇当做美德。《水浒传》一系列的复仇行为(如武松杀嫂、石秀杀海和尚等)正是游民极端思想的表现,也是江湖风波险恶、游民看不到自己前途的反映。在《说唐》中,同秦琼对李渊家有恩这一线索同等重要的是单雄信与李家有仇。这个情节在《遗文》中就出现了。《遗文》与《说唐》对单雄信形象的塑造非常感人,他对江湖义气、特别是对秦琼的关爱与对李渊一家的仇视是同样的执着的。如果实事求是地分析,李渊打死单雄信的哥哥,只是一次误伤,并非有意与单家结仇,而且是由于受到隋炀帝的陷害才导致这场灾难。以单雄信与秦琼交情与秦琼与李家的关系,及其他们共同反隋的政治立场来看,单、李的矛盾满可以化解。然而,为了强调有仇必复和独立自主的选择,书中把单、李矛盾写成十分情绪化的不共戴天之仇,正体现了游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说唐》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与《遗文》也有差别。作者无论处理什么题材,他们生活的经验和对生活的认识与理解都不能不反映到其作品中去。《遗文》是文人士大夫修订的,因此在塑造人物时有着明显的文人化的倾向;而《说唐》无论是写什么人都在向游民看齐。如秦琼在《遗文》中是文质彬彬的,到了《说唐》之中就恢复了他的游民的粗豪本色,卖私盐的程咬金一派匪气更不用说。即使象伍云召一类的隋朝的高官出口也是江湖气,根本不象太守一级的地方大吏,当他遇到了山大王雄阔海,听得阔海自报了家门,便说:“本帅今日意欲与你结拜为兄弟。”这哪里是什么出身名门的高官,分明象走江湖的豪客了。因此通俗戏曲的改编和评书艺人的演说都用《说唐》作底本,其原因在于书中所反映的游民的历史观、人生观、审美观与表演者、演播者是一致的;《说唐》中的思想意识也易于被广大的游民听众所理解。夏志清说这是“劣币通行,良币就被藏了起来”。这是文人或者说是小说家的看法,对于以广大游民演说者和游民听众却不一定是这个意见。
4.背离了社会主流思想的游民意识
游民不是社会中的新兴力量,而是从宗法社会这个网络游离出来的零余者,因此,这个网络在他们身上留下许多印痕,而游民知识分子正是他们思想意识的代表者与群体情绪表现者。
我们说他们背离了社会主流意识并非是说他们发现了或接受了某种新的意识形态,而只是把主流思想倒过来罢了。作个不恰当的比喻,如果说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只漆雕斑烂的手杖的话,那么游民意识只是剥落其雕饰、把它颠倒过来使用罢了。
例如天命论、英雄史观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人们对于历史变革的普遍看法,统治阶级、士农工商、游民社会各阶层,概莫能外。作为主流意识的表达者文人士大夫在阐释这些概念时基本上是用儒家思想。如讲“天命”不只是那高高在上主宰人间万类的神灵,而是强调“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重视民心的向背。在明智的统治者的心目中,“天命”就是民心;而处于社会最下层的游民却把“天命”看成历史一种绝对的支配力,这是谁都无力改变的。游民知识分子创作的通俗小说和通俗戏曲中对“天数”的相信已经达到痴迷的程度,这一点在《词话》与《说唐》中有极充分的表现(如《词话》中写李世民被俘、《说唐》写李元霸之死)。中国的游民大多来源于农民,他们虽然脱离了宗法社会的共同体,但是由于个性发展不成熟,对命运感到迷茫,他们的社会化程度很低,在强大的社会势力面前有一种无力感,因之,他们反而没有士大夫的思想家们更能意识民心与人的力量。
在动荡的社会变革中,游民们更是盲目崇拜武力,特别是个人的勇武和蛮力。在他们眼中的战争就是个人凭着武力单打独斗。李元霸独战一百八十万军马的故事,这在有理智的文人士大夫笔下是不可能出现的,而游民知识分子却把它作为一个“精彩”的情节大肆渲染。因此,同样是英雄史观,文人士大夫认为历史的演变取决于“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帝王将相;而游民知识分子则认为是由他们中间的“勇敢分子”决定的。
在审美观、艺术观方面,游民知识分子也与文人有显著的区别,特别是以历史为题材的作品。游民们文化水平低、历史知识有限,很难创造历史氛围,只是善于以其经历的现实生活去填充,又由于他们对游民中“勇敢分子”的崇拜,于是讲史小说通过他们的改造往往离历史越来越远,成为带有草莽气质的英雄传奇。例如东西汉变成刘秀、姚期、马武的故事;明英烈变成了朱元璋、胡大海、常遇春的故事。当然,这些系列演变的脉络没有“说唐”这么明显,但确实是客观存在的,因而,这些英雄传奇的通俗小说人物类型化、脸谱化的倾向便十分严重。在结构与语言上也较文士的作品粗糙一些。但总的来说,英雄传奇是比编年讲史更富于文学性的。
我们从对“说唐”小说系列变化过程的考察,可以看出游民知识分子(有文化的江湖艺人)对于古代通俗小说的形成与演变有着重大的影响,他们的群体意识与思想情绪渗透在这些小说思想内容之中,并传播到民众中去,甚至影响到历史的进程。这些不仅是文学史上的问题,也是社会史上的问题,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