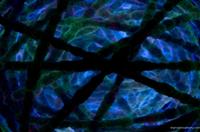
我们研究《楚辞•招魂》的作者及所招的对象是谁,只能从《招魂》原文中探求,因为每一文学作品无不打上时代和人物的烙印。我们先撇开前人提出的“宋玉招屈原说”、“屈原自招说”、“屈原招怀王生魂说”、“屈原招怀王亡魂说”、“屈原招顷襄王”等说法,单从《招魂》涉及的时代、地理状况、人物来探求《招魂》所处的时代及地域,从而推论出《招魂》的作者以及为谁招魂的结论来。
一 “江南”“梦”地沿革考
《招魂》“乱曰”是全文的总结,叙述了作者于“献岁发春兮汩吾南征”的途中作《招魂》,地点在“与王趋梦兮课后先”的“梦”地,原因是作者在“梦”地“目极千里”惨状,逼得他从内心发出“魂兮归来哀江南”的呼号,点明了作者是为“哀江南”而作《招魂》的。
江南即长江之南。楚国江南在哪里?作者为什么要“哀江南”?楚国历史上习惯把黔中郡洞庭之域称之为江南地。这里不但位于长江之南,而且距郢都纪南城很近。楚人称其为江南名副其实。这里土质肥沃,气候温暖,物产丰富,是楚国粮油基地。这里历史悠久,人口稠密,交通方便,商业繁荣,文化先进,是兵家必争之地。江南自春秋晚期楚国开拓到楚国灭亡时一直是楚国的疆土,对楚国的发展及稳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战国中期,秦楚争雄,秦国多次想攻占楚江南地,楚予以坚决护卫,在此曾发生过拉锯战。据《秦本纪》载:“二十七(昭襄王),……又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中郡,拔之。”《楚世家》载:“十九年(顷襄王),秦伐楚,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秦本纪》与《楚世家》记载的是同一年同一战争事件,楚失去的是上庸汉北地,秦得到的是楚黔中郡。由于时代久远,人们不知道“上庸汉北”地即“江南洞庭湖滩北庸族居住地”①在楚黔中郡之域。《水经•沅水注》:“秦昭襄王二十七年,使司马错以陇蜀军攻楚,楚割汉北于秦。”记载了“汉北”在沅水流域,即沅水滩北之域。沅水自北而南,自西而东与澧、资、湘等九河汇集成洞庭,沅水滩北即洞庭滩北。“滩”“汉”在先秦时代通用,由此可知“汉北”“滩北”。顷襄王十九年时,秦国已进入楚江南地,并靠近了西洞庭湖。秦国从北、西、南三面完成了对楚郢都的包围,导致了顷襄王二十一年郢都被迫东迁和屈原南征沅湘洞庭。《楚世家》载:“二十二年(顷襄王),秦复拔我巫、黔中郡。”《秦本纪》载:“三十年(昭襄王),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战国策•秦策第一》载:“秦与荆人战,大破荆,袭郢,取洞庭、五都(渚)、江南。”叙述了楚江南地大部分地区在顷襄王二十二年时被秦国占领了,连洞庭湖区域也不例外,但时间不长。据《秦本纪》载:“三十一年,白起反魏,取两城。楚人反我江南。”《楚世家》载:“二十二年,襄王乃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为郡,距秦。”记载楚国只用一年的时间就把黔中郡及江南洞庭之域的失地又收复回来了,从此,江南直到楚国被秦灭亡时才归秦管辖②。《招魂》作者“哀江南”就是“哀”江南被秦所拔时的惨状,这时的江南民众无国无家,流离失所,到处呈现“目极千里伤春心”的状况。过去,由于人们对“目极千里”的字义没有过细考证,就不可能看到先秦时代“目极千里”的实际内容,就无法表达出“目极千里”的景象,更不能说明“目极千里”的社会状况。“目”:看。“极”:《说文》:“驴上肩也”,即放在驴背上用以载物的木驮架。“驴”,为民户所用的交通牲畜。“极”:指民户驮运物件。“千”:数字,十百为千。“里”:宅院,民户居处。《诗•郑风•将仲子》:“将仲子兮,无逾我里。”《传》:“里,居也,二十五家为里。”《周礼•地官•遂人》:“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后代“里”所居家数量时有变更,但在先秦时代“里”所居家数基本上是固定的。“千里”:即二万五千民户。“目极千里”的原意是说:“看到千万户民众赶着牲畜驴马在迁徒”。在春耕生产的大忙季节,竟有成千上万的民户在流亡,这样的状况怎能不使楚国目睹者“伤春心”呢?可见这时的江南是可哀的。然而,这可哀的江南却是作者曾“与王趋梦课后先”的“梦”地。“梦”字本作“萝”,楚谓草泽曰“萝”。《乐雅•十薮》:“梦有云萝”。郭璞曰:巴丘湖是也,即今洞庭湖。《地理志》:“南郡华容县有云梦泽。”由此推知,作者在“萝”地“哀江南”的“萝”就是楚江南地。时间是顷襄王二十二年的初春。我们弄清了“哀江南”的历史原因,再来考释《招魂》的内容,一切疑难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二 《招魂•序•乱曰》考释
《招魂》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序言,既作者自序。第二部分是《招魂》辞。第三部分是“乱曰”,全篇的总结,“发理词指,总撮其要。”
《招魂》序言:“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沫。”的“朕”即作者自指。这两句的译意是:“我从小就清白廉洁,亲身实行仁义忠信毫不含糊”。接下两句的原文是:“主此盛德兮,牵于俗而芜秽。”“主”:保持。译意是:“我一直保持着这些品德,但受着世俗的牵累使我身受污秽。”下面两句的原文是:“上无所考此盛德兮,长离殃而愁苦。”译意是:“王上不考察我这些美德,使我遭到祸殃而长期痛苦。”以上六句都是作者“朕”的自序。作者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沫”的人,是一个“主此盛德”的人,是一个无奈“牵于人俗而芜秽”的人。可惜“上无所考此盛德兮”,终于使“朕”长离殃而愁苦。”这个愁苦的人需要得到帮助和安慰,只有皇天是大公无私的神,是可以辅助人间受灾受难的难民的神,因此,作者幻设了天帝辅助“朕”摆脱愁苦的情节,以解救自己。“帝告巫阳曰:‘有人在下,我欲辅之。魂魄离散,汝筮予之。’”这几句话的译意是:“上帝告诉巫阳并对他说:有个‘长离殃而愁苦的人在下面,我想帮助他解除痛苦。他的魂魄离散了,请你为他占个卦帮忙招回魂。’”接下来是主持招魂的巫阳对天帝的谈话:“巫阳对曰:掌梦?上帝;其难从:若必筮予之,恐后之谢,不能复用。”巫阳的对曰最难解的是“掌梦”的含义。但“掌梦”是一官员无可非议。《周礼》载有“掌舍、掌葛、掌染、掌炭、掌节”等官职名,可知“掌”是掌管某地或某行业的官员。“梦”,我在前面已经考证为洞庭湖泽之域,“掌梦”即掌管梦地的官员。有人把梦王委派的“掌梦”官与《周礼•春官》中的“占梦”官混为一谈,以致长期使“掌梦”不能落实其人。这个“掌梦”就是上帝要辅助的那个“长离殃而愁苦”的人。巫阳是楚国的神巫,他最清楚“掌梦”在“梦”地所受到的挫折,他所掌管的“梦”地被秦占领了,王上不考察他失地的原因,反而要追究他的责任,因此,他忙于南征履行“掌梦”职责。“梦”地宽广无垠,巫阳也很难知道“掌梦”的去向,所以他对天帝说:“其难从”。这个“其”就是指“掌梦”。“从”:同“踪”。“难从”:即难以踪捕掌梦去向。巫阳进一步说:“若必筮予之,恐后之谢,不能复用。”这个“后”即以后。“谢”:萎谢。“复”:再。这几话的译意是:“如果硬要我占卜他的去向招回魂的话,恐怕他以后就此萎谢,招回了魂魄也没有用。”
序言叙述了作者是“朕”,“朕”是个具有美好品德的人,是个实行仁义而意志坚定的人,由于受时俗牵累而遭受挫折,加之王上不去考察“朕”受挫折的原因,因此使“朕”长期痛苦。上帝要辅助的这个人是“掌梦”,“朕”即“掌梦”,“掌梦”因受挫行踪难捕,因此,“朕”才幻设天帝命巫阳为其招魂,这就是作者作《招魂》的原因。巫阳的招魂词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曲折地反映了“掌梦”迫切希望“入修门”、“反故居”的思想感情。招魂词涉及的地方有天上、地下和人间的东南西北四方,地域虽然泛指,但方位是确切的,即以江南“梦”地为中心,其地都与“梦”地有着密切的关系。
“乱曰”是《招魂》的总结。“献岁发春兮汩吾南征,菉蘋齐叶兮白芷生。”“征”:《左传•襄》十三年:“先王卜征五年。”《注》:“征,谓巡守征行。”这两句的译意是:“第二年早春我匆匆巡守征行江南,此时正是菉、蘋长齐叶白芷发芽的时期。”接下来两句的原文是:“路贯庐、江兮左长薄,倚沼、畦、瀛遥望博。”“路”:指车马大道。《周礼•地官•遂人》注:“路容三轨”,指可由三辆马车并驾齐驱的大道。“贯”:直通。“庐”:指田间的小屋。《周礼•地官•遗人》:“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记载二百五十户的村落设有“庐”,七百五十户的村落设“宿”,都是接待宾客的地方。“江”:或曰长江,或曰洞庭九江。由于前人对楚辞中的地名缺乏认识,往往把“庐”与“江”合二为一成为“庐江”,殊不知先秦时代庐江还不曾有名,况且楚辞书面语中的“庐江”只能简称“庐”,或者简称“江”,没有连称的先例③。从“庐”字结构来看,不从水,也不可能是水名。“薄”:水边连绵不断的丛林。“倚”:依。“沼”:沼泽。“畦”:区界。“瀛”:大湖。“博”:广。这两句的译意是:“车马大道直通沿江村落,左边是长洲和大薄丛林,我依立在小泽大湖交错处遥望湖光景色。”这一景象勾起了作者的往事。
“青骊结驷兮齐千乘,悬火延起兮玄颜烝。步及骤处兮课后先,抑鹜若通兮引车右还。与王趋梦兮课后先,君王亲发兮惮青兕。”这两句的译意是:“徒猎的聚集在猎车旁开路,向导在前指挥自如向右转弯前行。”后面两句的“王”,当指楚王。“梦”:梦泽,即洞庭湖泽。“课”:考核。“惮”:郭沫若《屈原赋今译》:“惮当是殚字之误”,尽的意思。“兕”:野牛,色黑,一只角。这两句的译意是:“我与楚王一起驰骋云梦中,考察随从谁后谁先。楚王亲自弯弓鋬弩发射箭,把围着的青色犀牛都射光。”
往事的幻现,导致作者现实的痛苦,作者“遥望博”所看到的地方原来就是他曾“与王趋梦课后先”的“梦”地。这次校猎在《战国策•策一》有确切的记载:“梦王游于云梦,结驷千乘,旌旗蔽日,野火之起也若云霓,兕虎嗥之声若雷霆,有狂兕依轮而至,王亲引弓一射,一发而殪,王抽旃旌而仰兕首,仰天而笑曰,‘乐矣,今日之游也。’”《楚策四》庄辛谏楚襄王也叙述了这次校猎:“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辇从鄢陵君与寿陵君……与之驰骋云梦中,而不以天下国为事。”这两段史料叙述的是同一事件,都证明了“与王趋梦”是作者与顷襄王在梦地校猎,时间在庄辛去赵(顷襄王十八年)前不久。这时的“梦”是楚国乐土的象征。
作者“与王趋梦”已成了历史,现实“梦”地的变化引起作者无限的悲哀,他多么留恋往事,然而“朱明承夜兮时不可掩”,火红的太阳承接着黑夜,美好的时光不可以停留,眼前的“梦”地呈现的却是一片凄凉愁怅的悲哀景象:“皋兰被径兮斯路渐,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伤春心”。这三句的译意是:“江岸的小道被兰草覆盖,车马大道也长满了青草,江水是澄深的,岸上长着枫树,千万户民众赶着驴马流亡的情景使我愁苦悲哀。”此情此景发生在顷襄王二十二年春,江南被秦所拔,“掌梦”人目睹此状,心潮起伏,内心非常痛苦,作《招魂》聊以自慰,他用“魂兮归来哀江南”作全文的总结,点明了《招魂》是为“哀江南”而作。
三 《招魂》作者考
《招魂》是楚辞名篇,作者一曰宋玉,一曰屈原,两位都是楚国著名的辞赋家,究竟是谁作的,莫衷一是。
宋玉事迹,古籍记载较少,仅能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韩诗外传》、《新序》、《襄阳耆旧记》、《水经注》、《诸宫旧事》中找到零星记载。《屈原贾生列传》载:“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灭。”这段史料记载了宋玉晚于屈原。
陆侃如《宋玉评传》④、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综合前人对宋玉生平事迹考证的成果加以推测,认为宋玉生于公元前290年,
考烈王八年(前255年)。“为小臣,不久失职,作《九辩》,卒于负刍王五年(前222年)”。这个推测虽然不十分准确,但大体上的年代是可供参考的。这就是说,宋玉从事文学活动的时间应在顷襄王晚期,即楚从郢都(江陵纪南城)迁陈(河南淮阳)至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前241年)又东徙寿春(安徽寿县)以前,其活动地域,至多不超过淮、泗、颍、汝一带⑤。前面我已经考证《招魂》作者是顷襄王二十二年时南征“梦”地的,如果是宋玉的话,他便应该是顷襄王派出“掌梦”的官员,然而,此时的宋玉不过十四、五岁,是不可能在朝廷任职,更不可能在国家危难时“掌梦”。因此,宋玉作《招魂》在时间与地域上是不大可能的。况且,在宋玉的文学作品中找不到南征的内证,无法证实宋玉作《招魂》的可能。那么,《招魂》的作者就只可能是另一位楚辞学家了。
屈原者,确切的生卒时间失传⑥,但他是楚怀王、顷襄王两个朝廷的左徒,早于宋玉的年代是大家公认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余读《天问》、《招魂》、《离骚》、《怀沙》,悲其志。”记载了《招魂》、《天问》、《离骚》、《怀沙》(九章)同是屈原的作品。这段史料是汉代史官司马迁撰录的,可靠吗?不得而知。如果说这段史料是可靠的,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怀疑《招魂》是屈原的作品。可是现在和过去都有一部分人怀疑《屈原贾生列传》所述《招魂》是屈原作品的真实性,使得今人不得不对《招魂》的作者进行重新探讨,还《招魂》作者的著作权。
《离骚》是屈原作品大家没有异议,《九章》是屈原的作品也很少有人怀疑。然而《离骚》是屈原南征三年的史诗,《九章》是屈原南征“至今九年而不复的纪实”⑦内容却很少有人知道,更不清楚《招魂》也是屈原在南征途中的作品。
《离骚》、《九章》记述了屈原南征“梦”地的时间和原因,它与《招魂》的作者“朕”、“吾”的南征属同一时代与同一地域。《离骚》:“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九章•哀郢》:“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终古之所居,今逍遥而来东。”“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涉江》:“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济乎江湘……步余马兮山皋,邸余车兮方林。乘舲船余上沅兮……”《抽思》:“有鸟自南兮,来集汉(滩)北。好姱佳丽兮,牉独处此异域……”“长濑湍流,泝江潭兮,狂顾南行,聊以娱心兮。”《怀沙》:“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伤怀永哀兮,汩徂南土。”“浩浩沅湘,分流汩兮。”《思美人》:“独茕茕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都叙述了屈原南征过沅湘洞庭。屈原南征沅湘洞庭的原因尽管先秦史料中见不到记载,但在屈原的作品中却透露了出来。《哀郢》:“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虽然大家对《哀郢》东迁的原因和时间有所争议,但不影响我们考证屈原在这次东迁中南上了洞庭。“上洞庭”是屈原在《哀郢》中说的,我们就没有理由说他没有南征沅湘洞庭。他既然南征了沅湘洞庭,我们就没有理由说《招魂》“献岁发春兮汩吾南征”的“梦”地不是沅湘洞庭之“梦”。顷襄王二十二年春,楚国江南“梦”地被秦占领了,但只有一年的光景,洞庭五渚及黔中郡就被楚国收复了。《招魂》“与王趋梦”的“梦”地原是楚国乐土的象征,而眼前的“梦”地却是“皋兰被径兮斯路渐,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的凄凉景象。“梦”地民不聊生,大规模迁徙的行动只能发生在“梦”地被秦所占领的时期。
屈原南征《招魂》与《哀郢》东迁事件有关。楚朝廷、百姓东迁时,楚王派遣屈原南征“掌梦”。《抽思》:“昔君与我诚言兮,曰黄昏以为期。”就是叙述楚王委派屈原“掌梦”诚言的笔录。屈原是顷襄王二十一年仲春南征“掌梦”的,“献岁发春”,“梦”地被秦占领,这对“掌梦”军政官员来说是个莫大的打击,楚王追查责任,有理也说不清,因此,逼得他“长离殃而愁苦”,而对当前形势,构思了《招魂》激励自己,解放自己愁苦的境地。
屈原受楚王的派遣南征“掌梦”,在当时是军事秘密,屈原自己不说,后人永远无法知道的,只能误认他是被楚王放逐而来沅湘洞庭的。派屈原南征“掌梦”本来是顷襄王所定的国策,要屈原固守江南“梦”地,要把江南云梦地变成楚国牢固的军事阵地,与秦对恃,以保证新都陈的建设。可是,不到半年时间,楚王却与秦昭王好会于襄陵,商议谋平之事,用“和亲”政策代替了军事反攻,改变了与屈原“成言”的复国计划。《离骚》:“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就是叙述楚王改变国策的事。屈原却按照既定的“成言”在南征,激怒了秦军,因此派大军增援上庸汉(滩)北地的军事据点,秦军像西风扫落叶一样席卷黔中郡和洞庭五渚,使得南征的“掌梦”节节败退而失去了依靠。过去,我们没有铁证证明顷襄王二十二年屈原还活着,而今,我们知道《招魂》“哀江南”就是“哀”顷襄王二十二年早春江南被秦所拔的悲惨景象,作者是屈原,那么,我们再没有理由说屈原已死于顷襄王二十一年夏天。相反,我们应该把屈原《招魂》做为屈原南征“掌梦”的里程碑。
前面我已论及《招魂》的作者是屈原,年代是顷襄王二十二年春,地点在沅湘洞庭之“梦”。
《招魂》涉及的人物(神)只有四个,即“朕”〔(吾)、(“掌梦”)〕、“王”、“天帝”、“巫阳”,《招魂》只能招其中的一个。“天帝”是世界的主宰,巫阳是招魂的执行者,都不可能是被招的对象。大多数学者认为巫阳是为某一个梦“王”招魂。有的学者认为被招的这个“王”是楚怀王,有的学者认为是顷襄王。前面我已经论及“梦”地被秦占领是顷襄王二十二年春,这也就是说,怀王客死在秦有二十年了,他的魂魄早有安身之所,不需再招。况且,楚怀王为秦人所拘,发痛而亡于秦,并非“牵于俗而芜秽”,“长离殃而愁苦”。就其魂魄而言,是欲归而不能,并非欲“散佚”于四方。帝告巫阳曰:“有人在下,我欲辅之”的“人”是活在世上的人。如果是死人的话,辅助又有什么意思呢?招顷襄王吗?倒与屈原南征“掌梦”的时代和事迹相牵连,而且,顷襄王是个活在世上的人,“梦”地的失守,王上当然会受惊吓,但不至于魂飞魄散。顷襄王于二十一年的仲春率朝廷官员东迁于陈,派屈原南征“掌梦”,他满怀信心地忙于新都陈郢的建设,头脑是清醒的。他在这年的秋天与秦昭王好会于襄陵,改变了国策,屈原却按照“成言”“掌梦”,破坏秦楚“和亲共处”,“梦”地的失守是楚王意料中的事,决不因此而吓得魂飞魄散,更不需要别人为他招魂。
“梦”地的失守,使“掌梦”官员魂飞魄散,王上怪罪他,他有理也说不清,需要皇天的辅助,才可能逃过临头的灾祸。屈原的作品往往假托神巫活动和人物对话来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解决矛盾,因此,他借助于上帝命巫阳为自己招魂。可见《招魂》乃屈原自招的文学作品,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五 余论
近读安徽师范大学潘啸龙教授在中国屈原学会第六届年会的学术论文《楚辞•招魂研究之商榷》,作者在论文提要中说:“自明清以来将《招魂》断为‘屈原所作’的论据无一可靠。因而长期以来的《招魂》研究,是在不正确前提下的失误。《招魂》的作者应是宋玉,其所招对象不是客死于秦的楚怀王亡魂,而是射猎云梦惊失的楚襄王生魂……”他在文章第一大段结语强调指出:“明清以来治骚者否定宋玉作《招魂》的证据,实无一条是可靠的。而被乐观地声称‘屈原作《招魂》说’已成‘公认’的定案,倒是一桩至今未能证成的悬案。因此,建国以来以此说为前提所开展的争论,诸如是‘屈原自招’还是‘屈原招怀王亡魂’等等,恰使《招魂》的研究,长期徘徊在误区之中,现在是应该予以认真反思的时候了。”故特作文与之商榷。结论是:《招魂》乃屈原自招。
注释:
①③拙作《屈原新考•屈赋地名浅论》,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6月版。
②贺刚《论湖南秦墓、秦代墓与秦文化因素》,《湖南考古辑刊》第五集。
④陆侃如《宋玉评传》,《小说月报》17卷号外,1927年版。
⑤蔡汝鼎《“招魂”二论》,《楚辞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⑥⑦拙作《屈原新传》,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