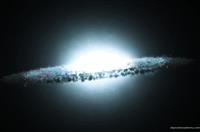陆游在旧时评论家眼中,诗名最著。宋末刘克庄即言:“近岁诗人,杂博者堆队仗,空疏者窘材料,出奇者费搜索,缚律者少变化。惟放翁记问足以贯通,力量足以驱使,才思足以发越,气魄足以陵暴。南渡而后,故当为一大宗。”①至清代赵翼,则直以陆、苏相颉颃,且力辨放翁作诗,实有胜过东坡之处。②其以苏、陆并举,乃是着眼于彼此成就可以等价齐观,且着力辨析陆胜苏处作为其立论的有力证据,绝未联想到放翁继承东坡之处。而自方回《瀛奎律髓》到刘熙载《艺概•诗概》,均从作品解析和理论概括方面,极力表彰陆游诗风得力于白居易之处,很少言及苏轼与陆之间的前后联系。至于词,则多有注意两家风格的联系者。杨慎《词品》评放翁词“雄快处似东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放翁词提要》亦谓陆游作词,欲驿骑于苏东坡、秦少游二家之间;刘熙载也有类似的评价。③然这种较为笼统的称说,并不能让人明白二人词风相似的深层次复杂联系,但它有助于我们由此作进一步的探索分析,去寻找其所以然的多层原因。鉴于古今论者对两位大家的作品已有较多的研究,故本文将重点放在苏、陆二家在哲学与政治思想、学习方法与文艺观念两大方面,作一些分析评述。
一、哲学与政治思想
就笔者所知,在人生哲学观念上,注意到苏陆二家相似之点的,是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他认为陆游诗歌的抒情方式,与杜甫有明显的不同,因为陆游“已经从苏轼那里继承了宏观的哲学与抵抗的哲学。”吉川氏申论之曰:“他(陆游)的诗之所以既富于感伤,又不沉湎于感伤,是因为受了他所继承的由苏轼开创的宏观哲学的影响之故。”他分析苏轼的宏观哲学有四个层次,即:(一)以庄学的“相对”观承认悲哀的存在;(二)用悲哀存在的普遍性来否定对悲哀的执着;(三)把人生视为一个漫长的持续的时间过程以减轻悲哀与绝望;(四)把握人生的主动权与悲哀抗争,变绝望为乐观与希望。显然吉川氏已注意到,何以杜甫与陆游处于类似的君国不幸的时代里,陆游诗中流露出的情感,不像杜甫在诗歌中流露的感情那样“异常悲哀”。
吉川氏又特别指出如下两个方面,以证实苏陆人生哲学的相似之处。“他(陆游)也像苏轼一样,肯定忧愁、悲哀作为人生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到处存在的。”这即是前述苏轼对人生悲哀存在的普遍性的哲学认识。”与此同时,陆游还认为,人生不只是由悲哀构成的,幸福也是到处都有的,这种哲学,也是从苏轼那里继承而来的。”④这便是苏轼以“相对”观既看到人生的悲哀,又看到人生的欢乐,并且相信在漫长的持续的人生变化过程中,机遇和希望是永远存在的。所以,在他流落天涯的迟暮晚年,以乐观旷达的生活态度把北还的希望变成了现实。陆游身历六朝,几进几退,当国家民族仇恨未雪、个人婚姻生活又不如意的时代境遇中,居然能安享八十六岁高寿,未尝不是其善于遣哀和旷放乐观的生活态度所赐。
苏轼被贬黄州时,读佛书,狎渔樵,躬耕东坡,以闲废治学为幸,晚年以衰残之身,远贬岭海,亲断故绝,衣食所赖,一切皆无,却常以不曾考取进士自慰,视此行为冠平生的奇绝之游!“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二首》其二);“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儋耳》)岭南瘴疠,海角天涯,何尝能改变苏轼乐观豪迈的生活观念!
陆游五十一岁时,范成大来帅蜀,辟之为参议官,以诗酒相酬唱。人或讥其不拘礼法,视为颓放,乃自号放翁。其后范氏归朝,陆游东还,有《长相思》词咏其事。词云:“桥如虹,水如空,一叶飘然烟雨中,天教称放翁。侧船篷,使江风,蟹舍参差渔市东,到时闻暮钟。”五十六岁复作《放翁自赞》以明志:“遗物以贵吾身,弃智以全吾真。剑外江南,飘然幅中。野鹤驾九天之风,涧松傲万木之春。或以为跌宕湖海之士,或以为枯槁陇亩之民,二者之论虽不同,而不知我则均也。”⑤陆游之所以不以“跌宕”或“枯槁”之一格自拘,就在于他认同了庄子的相对主义人生哲学,仕与不仕,出处进退,辄以随缘任运、纵浪大化处之,“湖海”、“陇亩”固然是拘束不住的。当然,仕途淹蹇,闲散无聊时,仍如东坡先生一样,努力去发现生活的别样价值,为自己确定新的位置。他的两首《破阵子》词,即比较突出地表现了这种人生观。兹抄录其二:“看破空花尘世,放轻昨梦浮名。蜡屐登山真率饮,筇杖穿林自在行,身闲心太平。料峭余寒犹力,廉纤细雨初晴。苔纸闲题溪上句,菱唱遥闻烟外声,与君同醉醒。”
陆游借老庄哲学以解悟人生、慰藉失意,表明了他对老庄哲学用途的认识,这与苏轼相似。与此同时,又并非专奉道家的信徒,其对儒释道三教关系的认识,亦取苏轼兼融三教,杂取用之的态度。这一相似之点,只要对照苏轼《上清储祥宫碑》和陆游《洞霄宫碑》,就可以得到清楚的结论。苏轼谓道家“以清净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以慈俭不争为行,合于《周易》‘何思何虑’,《论语》‘仁者静寿’之说,如是而已。”⑥,陆游则言,道家“其书为《易》六十四卦,《道德》五千言,《阴符》、《西升》、《度人》、《生神》之经,列御寇、庄周、关喜之书,其学者必谢去世俗,练精积神,楼于名山乔岳,略与浮屠氏同;而笃于父子之亲,君臣之义,与尧、舜、周公、孔子遗书无异,浮屠氏盖有弗及也。”⑦虽然他们是从道家通于儒佛之处立说的,但由此可以窥见其沟通三教、并为所用的基本立场。钱钟书《谈艺录》引曾几《陆务观读道书,名其斋曰玉笈》诗,称其“三家一以贯,不事颊舌竞。”钱氏云:“是放翁欲融贯通三教,而非攘斥二氏也。”⑧观《渭南文集》,特多为释氏作的碑传表记,则曾几之言不虚也。
在对于“礼”的设置和用途的认识上,苏、陆二人亦显示出惊人的一致。苏轼在元祐时期与程颐的矛盾冲突,主要便是起因于程颐拘执古礼,苏轼讥其“不近人情”。他在《礼以养人为本论》、《礼论》、《直不疑买金偿亡》、《书李简夫诗集后》等文章中,极力阐明“夫礼之初,缘诸人情,因其所安者;而为之节文。凡人情之所安而有节者,举皆礼也,则是礼未有定论也。”他所强调的,一是礼因人情而设,二是礼因时代变化而变。后人非要拘执几千年前的所谓“古礼”,就是虚伪矫情,不知变通。⑨陆游对此不仅有与苏轼相同的看法,甚至措辞都极其相似。《宁德县重修城隍庙记》:“礼不必皆出于古,求之义而称,揆之心而安者,皆可举也。”⑩《潜亭记》:“自尧舜周孔,其圣智千万于常人矣,然犹不以异于人情为高。”(11)可以清楚地看出陆游对苏轼礼学思想的忠实继承。
在对待仕途出处的态度上,苏轼于熙宁五年(1072)所作的《沁园春》词,和元丰二年(1079)作的《灵壁张氏园亭记》所表述的原则,最具代表性。词中有云:“用舍由时,行藏在我”;文中称述古之君子之道则云:“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不仕则忘其君。”这段话被罗织苏轼的群小之一李宣之加以歪曲发挥,欲诬苏轼“目无君父”之罪。(12)其实,苏轼不过具体运用了孟子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原则,企图在维护人格独立的前提下,去发掘人生的多元价值。与此同时,他欣赏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的认真态度(《书李简夫诗集后》),并不讳言封建时代士大夫求取俸禄是生活的必然选择,甚至承认士大夫为宦四方就是要获取较为优裕的物质享受。(13)陆游《答刑司户书》则云:“吾曹有衣食、祭祀之累,则出而求禄,恐未为非。既不免求禄,则从事于科举,亦未为可憾。”(14)《答王樵秀才书》云:“士以功名自许,非得一官,则功名不可致。虽决当绌,尚悒悒不能已,况以疑绌乎?”(15)此言算得是很实在的大实话。由此可知古代文人何以仕途失意时往往悲苦叹惋,专制制度愈强化,文人的出处进退态度愈“灵活”。然苏轼与陆游能公开承认这一点,平实地谈论它,远比那些故作清高者令人尊信。
二、学习方法与文艺观
由于宋代人文条件比往代更有改善,且印刷术日益普及使通过书本获取知识更加容易,故宋代文人很重视书斋生活,也很看重一个人的学养功夫。尤其那些有家学渊源的书香门第,其对经史典籍的学习非常系统化,也非常广泛。陆游祖父陆佃以学问著名,陆游是在一个书香门第成长的。《上执政书》云:“某小人,生无他长,不幸束发有文字之愚。自上世遗文,先秦古书,昼读夜思,开山破荒,以求圣贤致意处。虽才识浅薄,不能如古人迎见逆决,然譬于农夫之辨菽麦,盖亦专且久矣。原委如是,派别如是,机杼如是,边幅如是,自六经《左氏》《离骚》以来,历历分明,皆可指数。不附不绝,不诬不紊,正有出于奇,旧或以为新,横鹜别驱,层出间见……”(16)此文作于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时年37岁。从文中的叙述可以看出,陆游学习传统经典不仅早,而且相当系统化,对其源流条贯有清楚的了解。上书执政,虽然有“推销”自己的用意,但如果没有长时间的学习积累,也是不好贸然自饰的。《答刘主簿书》又述及二十岁左右“始发愤为古学”的情况,自谓主要是通过独立摸索,“以意度”古人用心处。大概从二十岁开始,陆游就注意把学习知识与文学创作和立身处世结合起来,故探求“古人用心处”就特别重要了。
所谓“求圣贤致意处”,“古人用心处”,就是强调读书不可僵死拘执,不可只做背诵章句的书橱,而应该直取古人作文之“意”,明白其根本所在。抓住了根本,就比较容易看清古代文化的因承条贯,理清其“原委”“派别”“机杼”“边幅”。然后把古人的东西变成自己的活知识,奇正乘除,新旧变通,直至达到横鹜别驱,灵活运用。这就正如他批评那些读《易》之人所指出的:“今读《易》不能知伏羲之心,读典谟不能知尧舜禹皋陶之心,虽典坟尽在,亦何益于稽古。”(17)不求用而稽古,那就失去了学习的真正目的,没有任何意义。
苏轼把书籍与象犀珠玉、金石草木丝麻五谷相比较,认为书籍胜过这些物品之处,乃在于有用,而且可以用之不竭。他说:“悦于耳目而适于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贤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见,各随其分,才分不同,而求无不获者,惟书乎!”(18)这里指出人的才分品质不同,从书中所获亦不同,也就是揭示了学习必须独立探索,亲自体认。苏轼著名的《日喻》,用比喻的方法揭示出,“求道”不通过亲自去学习认识,那就只能像眇者一样,误以为钟、烛就是太阳。与此同时,苏轼所谓“道可致不可求”的道,就是指基本规律、根本原理。学习是为了致道,也即陆游所强调的,学习是为了得古人“致意”“用心”处。为了对书中意思条贯有系统化的了解,苏轼还发明了“八面受敌”的读书方法。他在《与王庠尺牍五首》其五中颇道其祥,曰:“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一本书经过反复数次对不同内容的系统了解,这样学过的东西,就可以“八面受敌”,方方面面都了解得很透彻了。陆游自言颇得古代文化发展的“原委”、“派别”、“机杼”和“边幅”,应是采用的苏轼学习法。在学习中专重得古人“意思”所在,尤其是他们的相似之处。
其次,苏、陆都是宋代学问广博、该通百家的饱学之士。这不仅跟他们在哲学上主张兼收并蓄、杂取百家的观念分不开,而且与他们长期勤奋学习的努力分不开。苏轼才分过人,可他从不依恃于此,而是采用了一般人都嫌“笨”的抄书办法,他还把这作为一种基本学习方法向友生们推荐。即使在被贬黄州和岭海时期,不仅从未放松过学习,反而更加勤勉,“日以三更为率”,没有半夜以前睡过觉的。苏轼广受后人称誉的广博学识,就是这样长期努力积累起来的。苏轼早年即提出“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的学习原则,(19)他平生都是这样做的。陆游对东坡诗“援据闳博,指趣深远”,有清醒的认识,所以参议成都府幕时,范成大屡次敦促他为苏轼诗作注,均“谢不能”,终身不敢注苏诗。(20)陆游天生不及苏轼,刘克庄即有“放翁,学力也,似少陵;诚斋,天分也,似李白”的说法,(21)可知陆游的成就,主要得力于天后天的学习与生活体验,观其《上执政书》所言束发唯好文,《答刘主薄书》所言“发愤为古学”,
其平生夙志与用力之处,盖可概见。钱钟书援引刘后村之言,进而论之曰:“然放翁颇欲以‘学力’为太白飞仙语,每对酒当歌,豪放飘逸,若《池上醉歌》、《对酒歌》、《饮酒》、《日出入行》等篇……有宋一代中,要为学太白最似者,永叔、无咎,有所不逮。”(22)杨慎也曾说过:“宋代惟东坡似太白。”(23)陆游对东坡学问人品的仰慕,对太白诗风的效法,不难让人看出其内在联系。大略东坡有太白之天分而学力胜之,陆游以学力而求天分,与其远取李白,毋宁近法苏轼。陆游《答刘主簿书》云:“往者前辈之学,积水以成大,以所有易所无,以能问于不能,故其久也,汪洋浩博,该极百家,而不可涯涘。如足下所称诸公,盖皆如是也。”刘主簿所称究为何人,不得而详,但作为前辈学人的代表,苏轼肯定是居于称首的。从这里,陆游指出了前辈学问汪洋浩博、该极百家的特色和成功途径,实际上也就是他所推崇和实行的一种治学方法。
其三,苏、陆均主张学习须“得于心,践于行”,学习必须有益于人的道德水平的提高、增强行动能力。苏轼的“知”“行”观,属明确的“知易行难”论者,他尤其反对坐而论道,无所行动的道学门风,也反对那些高谈阔论而办不好事的人,他在解释《易•习坎•彖》“维心亨,乃以刚中”时,有一段比喻性的引申发挥,他说:“所遇有难易,然未尝不志于行者,是水之心也。物之窒我者有尽而是心无已,则必胜之,故水之所以至柔而能胜物者,维不以力争而以心通也。”(24)这里用水作譬,谓水虽至柔却可以战胜至坚之物,乃在其“未尝不志于行”的精神。因此,只有积极地行动,才能有所作为,战胜困难,取得成功。他反思历史,对王衍清谈误国言之切切:“文非经国武非英,终日虚谈取盛名。至竟开门延羯寇,始知清论误苍生!”(25)他批评当时学风说:“近世学者以玄相高,习其径庭,了其度数,问答纷然,应诺无穷。至于死生之际一大事因缘,鲜有不败绩者。”(26)又尝讥刺道学先生,平居与孔孟无异,至其行事,莫不为天下笑。学而无用,学而不行,在苏轼看来,是一种“欺世取名”、误人误己的丑恶行为。
陆游对笃学力行,见诸行事的学风十分赞赏。《求志居士彭君墓志铭》特别欣赏彭维孝“学而不施于事,犹不学也”的观点,(27)故于墓志中表而出之。又特别推崇其师曾几“笃学力行”,为当时后学所效法。(28)不言而喻,陆游就是其中取以为法的一个。又称赞另一位曾向其学习诗法的吕本中说:“公自少时,既承家学,心体而身履之,几三十年。”(29)尤其是曾几年过七十,“三日不见,见必闻忧国之言”,(30)其深重的忧国忧民意识,对陆游投身于抗金民族斗争,有着直接影响。梁启超于家国多难时读陆游诗,感慨良深,有“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胡尘意不平”之誉。(31)陆游投身到抗金斗争的实践中去,在古代文人中,是十分突出的一个。
宋人喜欢书斋生活,注重对书本的系统学习,形成对古代文化知识及文艺观念的基本了解。故其学习方法、学习体验,往往与其文艺思想和创作观念,有着一定联系。比如强调学以致用,其创作观必然以“有为而作”、期于实用为上,且推崇文如其人;学习中注重探求古人的“意思”所在,其创作观必然重视立意、写志、遣怀;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确立内容的决定作用;学习上主张兼收并蓄,其创作实践中必然反映出杂取百家的特色,在观念上也就对“俗”的东西、“异端”的东西比较宽容,等等。以下从几个方面简约叙述陆游对苏轼文艺观的继承。
第一,诗文当有为而作。苏轼在早年写的《南行前集叙》中就提出了这一创作基本准则。从他一生创作过程看,不仅坚持了这一原则,而且恰恰是其坎坷多难的身世遭遇,成为他在文学艺术领域取得辉煌成功的巨大动力。陆游用他自己的创作变化历程,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常为人们所乐道的《九目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一诗,最为具体地谈到他从戎南郑的军旅生活,为其创作带来了根本变化。“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这与以前写诗“残余未免从人乞”、“力孱气馁心自知”的创作感受相比,不啻霄壤之异!更有趣的是,陆游这两句形容有了生活素材与真实体验之后,才有截然不同创作感受的诗句,恰恰是化用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手扶云汉分天章,天孙为织云锦裳”而来。引起这种创作变化的根本原因,就是他在《示子遹》中所总结的:“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32)这“诗外”工夫,不是其拘泥于书斋一隅向壁虚构,而是广泛接触生活,写其生活的真实见闻感觉。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尤其是仕途困顿对世道人生的认识体验,可以刺激创作激情,文情并茂的佳作,往往产生在这种生活背景和创作境界中。这又与中国传统的“穷而后工”的文艺观息息相通了。故陆游《淡斋居士诗序》云:“盖人之情,悲忧积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不然,无诗矣。苏轼、李陵、陶潜、谢灵运、杜甫、李白,激于不能自己,故其诗为百代法。国朝林逋、魏野以布衣死;梅尧臣、石延年弃不用;苏舜钦、黄庭坚以废绌死;近时,江西名家者,例以党籍禁锢,乃有才名,盖诗之兴本如是。”
第二,重视养气对创作的积极作用。如果说“有为”偏重于各种外部因素对作家创作的刺激,那么养气就是作家自觉地对自身的道德情怀、艺术情感和其它素质进行培养陶铸,是作家的一种内在主观要求。由韩愈的“气盛言宜”,到欧阳修的“道胜文至”,苏轼的“士以气为主”,都强调作家内在的修养与综合素质是写好作品的主观条件。这就是说,文艺创作不只是一种显示作家创作才能的技术活动,更重要的是一种表现作家人格情操的精神创造活动,苏轼在《上刘侍讲书》中把“才”“气”二者的关系辨析得很明白,认为只有以气御才,事情才能成功,文艺创作自然不外此理。
陆游在《傅给事外制集序》一文中,引述曹丕“文以气为主”的观点,但所指已不是《典论•论文》特别强调的气质和创作个性,而是苏轼所特别心仪于李白的“雄节迈伦、高气盖世”的胆识和气魄,“方高力士用事,公聊大夫争事之,而太白使脱靴殿上,固已气盖天下矣。”(33)故文中称颂傅给事云:“公自政和讫绍兴,阅世变多矣。白首一节不少屈于权贵,不附时论以苟登用,每言虏、言叛臣,必愤然扼腕裂眦,有不与俱生之意。士大夫稍有退缩者,辄正色责之若仇,一时士气,为之振起。”(34)《方得亨诗集序》论“才”与“气”的关系,可以说全是苏轼《上刘侍讲书》的“南宋版”。文曰:“诗岂易言哉,才得之天,而气者我之所自养。有才矣,气不足以御之,淫于富贵,移于贫贱,得不偿失,荣不盖愧。诗由此出,而欲追古人之逸驾,讵可得哉!”(35)略为不同的是,苏轼泛论“才”“气”。而偏重言政事成败;陆游专论创作,主张以“气”御“才”,方能追古人之逸驾。陆游自述创作经历则曰:“某束发好文,才短识近,不足以望作者之藩篱。然知文之不容伪也,故务重其身而养其气,贫贱流落,何所不有。而自信愈笃,自守愈坚,每以其全自养,以其余见之于文,文愈自喜,愈不合于世。”(36)把文章之气,“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的观点,用“文如其人”的时代思想,作了内涵更加丰富的阐释。故言:“君子之有文也,如日月之明,金石之声,江海之涛澜,虎豹之炳蔚,必有是实,乃有是文。夫心之所养,发而为言,言之所发,比而成文。人之邪正,至观其文,则尽矣决矣,不可复隐矣!”(37)
第三,提倡创新精神和风格的多样化,批判片面求“工”的创作风气。苏轼在这方面最为突出。他不仅在不同文体的创作实践中,不断求新求变,取得了超迈时辈、超越古人的巨大成就,他还尽力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影响周围的追随者。
陆游在《答陆伯政上舍书》、《方得亨诗集序》、《何君墓表》等文章中,反复申说:“诗岂易言”的观点,《答陆伯政上舍书》云:“诗者果可以谓之小技乎?学不通天人,行不能无愧于俯仰,果可以言诗乎!”学不究乎天人之际,行无愧无俯仰之间,自然是无法从事艺术创作的。《何君墓表》对此作了详尽的阐发,且兼包了说诗与作诗二意:“诗岂易言哉?一书之不见,一物之不识,一理之不穷,皆有憾焉。同此世也,而盛衰异;同此人也,而壮老殊。一卷之诗有淳漓,一篇之诗有善病。至于一联一句,而有可玩者,有可疵者;有一读再读至十百读乃见其妙者;有初悦可人意;熟味之使人不满者。大抵诗欲工,工亦非诗极也。锻炼之久,乃失本指;所削之甚,反伤正气。……纤丽足以移人,夸大足以盖众。故论久而后公,名久而后定。呜呼难哉!”作品给读者的不同阅读感受,必然以其新鲜独特、丰富多彩的内容和形式为保证。故他特别强调“见书”、“识物”、“穷理”要尽可能广博周至,且要根据不同时代、不同年龄、不同文体的需要,求其变化新异;而这种创新和多变,又不是雕琢出来的,必须灵活自然,天真朴茂,那种为工而工的锻炼、斫削,陆游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证明是没有出路的。
注释:
①(21)《后村诗话前集》卷二。
②《欧北诗话》卷六。
③《艺概•词曲概》:“陆放翁词,安雅清赡,其尤佳者,在苏、秦间。”
④以上详见《中国诗史》《关于苏轼》和《关于陆游》两篇,章培恒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⑤⑦⑩(11)(14)(15)(16)(27)(34)(37)《渭南文集》卷二十二,十七,十七,十七,十三,十三,十三,三十九,十五,十四。
⑥《苏轼文集》卷十七。
⑧(22)《谈艺录》第453-454页,第125页。
⑨参见拙文《苏轼与理学家的性情之争》,《四川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人大书报复印资料《中国哲学史》1993年第5期。
(12)参见王文浩《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卷十八。
(13)《上神宗皇帝书》:“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宦于四方者,宣力之余,亦欲取乐,此人之至情也。”《苏轼文集》卷二十五。
(17)《婺州稽古阁记》,《渭南文集》卷二十。
(18)《李氏山房藏书记》,《苏轼文集》卷十一。
(19)《稼说》,《苏轼文集》卷十。
(20)详见《施司谏注东坡诗序》,《渭南文集》卷十五。
(23)《升庵诗话》卷十一。
(24)《东坡易传》卷三。
(25)《读〈王衍传〉》,《苏轼诗集》卷四十八。
(26)《跋荆溪外集》,《苏轼文集》卷六十六。
(28)《曾文清公墓志铭》,《渭南文集》卷三十二。
(29)《吕居仁集序》,《渭南文集》卷十四。
(30)《跋曾文清公奏议稿》,《渭南文集》卷三十。
(31)《读陆放翁集》。
(32)《剑南诗稿》卷七十八。
(33)《李太白碑阴记》,《苏轼文集》卷十一。
(35)(36)《上辛给事书》,《渭南文集》卷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