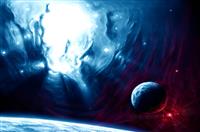李景林 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王觅泉 北京大学哲学系
过去我们研究先秦儒学,多以孔、孟、荀为对象。我们常觉得孟子继承了孔子“仁”的一面,而荀子则继承了孔子“礼”的一面,这三者似乎是一个平列的关系。其实,从孔子到孟子,先秦儒学有一个长时间的发展。这个发展,过去有思孟学派的说法。近几十年来相关简帛文献的出土和研究,使这个发展的内容有了一个展现的机会。孔子的思想是一个很平衡的系统。孟子和荀子都承认孔子思想的特点是“仁智”的平衡和统一。孟子里引子贡的话说“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孟子·公孙丑上》)。荀子也说“孔子仁智且不蔽”(《荀子·解蔽》)。其仁与礼的平衡,实根源于此仁智的平衡。结合简帛文献来看,孔子后学思想到孟子的发展,有一个内转趋向,这个内转趋势的代表是曾子、子思一系的思想。
一、孔子所开启的文化价值方向
在孔子以前,中国社会有关人生、伦理和价值的思想,表现于一种宗教的观念系统中。这个观念系统的核心,是作为至上神的“天、帝”信仰。张光直教授曾以“连续性”来概括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特征,以区别于西方“破裂性”的文明起源方式。“连续性”强调文明的创设与其所从出的原始自然状态的连续与和谐,保留了原始思维整体性的意识形式。①孔子以前的宗教伦理观念,一方面具有这种“连续性”的特征,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宗教性的观念,又表现出一种对人的功利性的理解方式。孔子所开创的儒家思想传统,与他所面对的这一宗教伦理传统的上述两个特征有密切的关系。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因为三代的天帝观保留了一种有机整体论的宇宙观和生存连续性的观念,天帝并未切断与人的亲缘性而独立为一个创世的精神本原。天帝至上神与物质世界和血缘人伦体系的未分化特征及其人格意义的缺乏,使它难以发展出作为文化核心价值基础的宗教体系。这对孔子及先秦儒家心性之学的思维方式、理论内容及发展方向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就第二个方面而言,在孔子之前,周人的文化价值观是宗教性的。在周人的观念中,至善的本原在天帝,人则被理解为一种功利性的存在。《左传·僖公五年》引《周书》说:“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尚书·召诰》说:“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这两条材料,即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在这种宗教性的视阈中,人的行为动机是功利性的(“祈天永命”),人亦由此被理解为一种功利性的存在。
孔子既继承了周人传统的“天命”观念,又在这天命观念的内部,提出“义、命”的内在区分。人之天职和使命,乃躬行仁义;行为的结果,则不在人的可求和应求的范围之内,只能归之于“天”或“命”。这种对“义、命”关系的理解,使传统的天命观发生了重要的转变:把行“义”由宗教义的祈神邀福之手段,转变成人行的内在动机和天职。孔子的这一思想,规定了以后儒家对天人关系和人之价值实现方式的基本理解。
孔子转变了周人天命观中把人仅仅理解为一种功利性存在的立场,反思并发现人之最本己的能力和可能性,在于躬行人道。对“天”或“天命”从根本上作人文的理解,从而把善的原则转变为人之本有的规定。孔子乃以“仁”这一概念统摄此点。《论语·颜渊》:“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述而》:“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都表现了这一点。这本身可看做文化价值观念意义上的一种“内转”。但《论语》言仁,多是根据学生的不同性情特点,随处点化,指示给人以切实践履以实现、领悟仁的方法和道路。而对仁之践履过程具有普遍性和奠基性的“性与天道”的问题,在《论语》中还没有成为正面探讨的显性议题。孔子的思想因而呈显浑沦圆融的气象。比如他既重视仁,也重视礼,二者构成一个平衡的系统。
但是这种平衡,不是仁和礼的平列甚至对峙,而是以人的自觉和人格的完成为其根本与归宿。相对而言,“仁”讲的是人的品德和理想,侧重于内心精神和情志内容,所以仁总与“爱”相联;“礼”讲人的社会规范,是行为的社会原则,侧重于“文”和伦理一面。孔子以忠恕论仁,即侧重爱心之推扩;讲克己复礼,则注重伦理原则的教化功能。实质上,它们从不同的角度表述了同一内容:二者可统归为“为仁由己”,即人之自觉和道德人格的挺立。在现实的修养过程中,推己及人的自觉与有意识地遵从礼义规范的磨炼可以相对地分开。但是,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已经内在地包含着礼所规定的节和度,在这个意义上,以社会的责任和义务为目的的行为和人格,仍然以人的内心的自觉为内容,仍然是“为仁由己”。由孔子开启的这一“内转”的趋向,一方面确定了一个思想发展的基本方向,即人有自身的价值和使命,人的价值之实现奠基于践履自身之使命;另一方面也蕴涵着一种理论需要,即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对“人之最本己的能力和可能性”之具体内容的理解。
二、前期弟子与后期弟子
史称孔子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余人。孔子身后儒家思想学术的发展,似乎是一件很难说清楚的事。对于孔子后学的分化,历来存在不同的看法,如从韩非而来的“儒分为八”的八派区分;传经之儒与传道之儒的划分;由《论语》而来的所谓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的“四科”划分;宋儒以来孔、曾、思、孟的道统传承说;前期弟子、后期弟子的区分,等等。这些说法之间又互有交叉。《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言孔子弟子“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而司马迁谓出于孔氏古文之《弟子籍》,有事迹和年岁者三十五人,见于《论语》者二十七人,而确有明证者仅二十人而已。这些弟子不见得都有思想上的建树,亦不见得在思想、学术发展上都有地位。看孔子后学思想发展的大势,崔东壁和钱穆先生的看法可以借鉴。崔述《洙泗考信余录》卷之一云:
《春秋传》多载子路、冉有、子贡之事,而子贡尤多,曾子、游、夏皆无闻焉;《戴记》则多记孔子没后曾子、游、夏、子张之言而冉有、子贡罕所论著。盖圣门中子路最长,闵子、仲弓、冉有、子贡则其年若相班者,孔子在时既为日月之明所掩,孔子没后为时亦未必甚久;而子贡当孔子世已显名于诸侯,仕宦之日既多,讲学之日必少,是以不为后学所宗耳。若游、夏、子张、曾子则视诸子为后起,事孔子之日短,教学者之日长,是以孔子在时无所表见,而名言绪论多见于孔子没后也。不然,闵子“具体而微”,仲弓“可使南面”,何以门人皆无闻焉,反不如“得一体”者独能传经于后世乎?由是言之,羽翼圣道于当时者颜、闵、子贡、由、求之力,而子贡为尤著;流传圣道于后世者游、夏、曾子、子张之功,而曾子为尤纯。②
钱穆先生《先秦诸子系年·二九孔子弟子通考》首肯并引申崔述之说云:
崔说甚是。余考孔门弟子,盖有前辈后辈之别。前辈者,问学于孔子去鲁之先,后辈则从游于孔子返鲁之后。如子路、冉有、宰我、子贡、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原宪、子羔、公西华,则孔门之前辈也。游、夏、子张、曾子、有若、樊迟、漆雕开、澹台灭明,则孔门之后辈也。虽同列孔子之门,而前后风尚,已有不同。由、求、予、赐志在从政,游、夏、有、曾乃攻文学,前辈则致力于事功,后辈则精研于礼乐。此其不同一也……大抵先进浑厚,后进则有棱角。先进朴实,后进则务声华。先进极之为具体而微,后进则别立宗派。先进之淡于仕进者,蕴而为德行。后进之不博文学者,矫而为玮奇。③
要言之,崔述和钱穆先生区分孔子前、后期弟子,认为前期弟子事孔子之日长,仕宦之日多,讲学时间少,且为孔子之明所掩,故其特点不在学术、思想之创造和传授,而在德行、事功等方面。后期弟子事孔子日短,教学之时间长,在孔子殁后,有机会发展出其独立的学说系统,故其特点在研精于礼乐、创立学说宗派。此说合乎情理。孔子前期弟子,多为随孔子周游列国者。其贡献在于协助孔子树立一个学行的传统。后期弟子则可有机会在此基础上对孔子所开创的儒家学说进行思想理论上的发展。《论语》中有子、曾子称“子”,《礼记》多记曾子、游、夏之言,皆说明了此点。另外,孔子对伦理、文化、礼乐及价值的重建,怀有强烈的使命感和担当意识,对社会现实亦极具批判精神。在这些方面,前期弟子的表现并不突出,这正说明其为孔子“日月之明所掩”。后期弟子从曾子始,乃显示出一种“以德抗位”之精神,体现了一种超越于现实政治的独立自觉的意识和开一代新风的气概。子思亦继承了这样一种精神。思孟都主张“德”超越于势位,孟子说“曾子、子思同道”,与这一共同的意识有关。由此,乃形成孔子后儒家之主要流派。
从文献的记述看,也是合乎历史实际的。细绎韩非“儒分为八”之说,其本意是要说明世所存者多为“愚诬之学,杂反之辞”,不足为治,必须以刑赏法度来治国,并非从儒家思想学说的关系来讲问题,实不足据以论孔子以后儒家思想学术之发展。而儒家文献中所记孔子后学言行,涉及学术思想之关系,探寻孔子以后儒家思想的开展,当以之为主要依据。如《荀子·解蔽》所述曾子、有子、子思、孟子思想,明显地就是一种注重内省的“神秘主义”。观《礼记》所记后期弟子之注重丧祭、孝道亲亲,近几十年出土简帛资料所涉及子游、子思等重心、重情、重乐、求己的思想倾向,再参照《孟子》内求于心而尽心知性知天的学说系统,大致可以看出孔子以后思想学术发展的脉络。
宋儒讲孔、曾、思、孟的传承关系,是一种道统论的讲法。但就现在所能掌握的资料看,它并非全无根据。孔子到孟子近二百年,儒家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尽管孔子的系统里已有关于人性的讨论,并肯定道德的先天基础,尽管孟子说自己“私淑”孔子,但直接从孔子来看孟子,其注重心、性、情、才、气的学说系统,仍使学者感到很是突兀。结合简帛资料和儒家传世文献,可以看到孔子以后儒家思想一种明显的内转趋势。曾子之说,实就忠恕而生发开去。曾子学说之要,乃以忠恕之道,贯乎“孝”德而为其本,由此转向内在省思之途。此一路向,既下开思孟一系,亦远开宋明理学之先。以后儒家所言心、性、情、才、气的思想系统,皆与此相关。这一趋势,子思这一系为其主要的代表。当然,宋儒的说法很粗疏。现在看来,思孟一系思想不是孤立的,它和曾子、子游、子夏、公孙尼子等都有着思想、学术上的关联。
三、圣与智
从荀子对思孟学派的批评来看,思孟的一个特征,是其“五行”说,由此而有一种神秘主义的特征。从郭店简和帛书《五行》篇我们可以知道,这五行说涉及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圣、智的问题。我曾做过一篇小文,讲荀子批评思孟五行是神秘主义,根据在其混淆了天人。现在看来,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个角度看,《五行》讲圣、智的问题,实质上是重心、重情。这与荀子的重智、重礼的思想倾向有很大的区别。从这一个角度看荀子对思孟的批评,可能更带根本性的意义。
《五行》篇既讲“五行”,又讲“四行”。而五行和四行的区分,涉及天道和人道、德与善的关系问题。郭店简《五行》篇说:
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四行和谓之善。善,人道也。德,天道也。④
所谓“和”,即能达以上诸德之内外和合而归于一心,以成就人格之谓。“仁义礼智”四行和之“善”,所成就者,即今人所谓的道德境界;而“仁义礼智圣”五行和之“德”,所成就者,则为即道德而超越道德的天人合一境界。故前者为“人道”,而后者为“天道”。
《五行》篇又以圣、智对举,“五行”和“四行”的对比,从人格成就上讲,就是“圣”和“智”的对比。郭店简《五行》篇说:
见而知之,智也。闻而知之,圣也。明明,智也。赫赫,圣也。“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之谓也。闻君子道,聪也。闻而知之,圣也。圣人知天道也……见而知之,智也……四行之所和也。和则同,同则善。⑤
智之思也长,长则得,得则不忘,不忘则明,明则见贤人,见贤人则玉色,玉色则形,形则智。圣之思也轻,轻则形,形则不忘,不忘则聪,聪则闻君子道,闻君子道则玉音,玉音则形,形则圣。⑥
我们可以把上引郭店简《五行》篇中一系列概念对照起来,看看它们有哪些不同的特点:
五行:仁义礼智圣 德 圣 闻 玉音 天道
四行:仁义礼智 善 智 见 玉色 人道
《五行》篇认为“四行”所标志者为“智”德,与之相对应的,是“善”或“人道”;而“五行”所标志者为“圣”德,圣乃能“知天道”。这与《庸》、《孟》的思想是一致的。孟子以仁义礼智四德为“善”,人先天本具此四德,故言“人性善”。又《孟子·尽心下》谓“圣人之于天道也”,正以圣人或“圣”与“天道”相对举。《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
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此以“诚”、“圣”为“天道”、“择善”之知为“人道”。《中庸》以“诚”和“圣”为同一层次的概念。又《中庸》下文既言圣可以“配天”(31章),“圣人之道”“发育万物”,“峻极于天”(27章),又言“至诚”可以参天地,育万物(22章),“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32章)。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一脉相承的思想传统。
故《五行》的系统,其核心是讲圣、智。圣者知天道,智者知人道。《五行》篇的作者以为“圣”的价值高于“智”的价值。“圣”可包含“智”的意义,反之则不可。圣、智,又以“圣”为中心。《五行》和《庸》、《孟》都强调圣者才能知天道。那么,圣人怎样知天道?通过什么方式知天道?从前面的引文我们知道,圣人的知天道,与听觉、音乐、内心的直悟所达之心灵自由有密切的关系。圣、听本为一字之分化,圣与声亦相通,其在字源上有相关性,古书圣又训“通”。故“闻而知之者圣”,注重内在的听觉意识,可能有相当深远的文化渊源。见而知之,与空间意识相关,听则与时间意识相关。后者关联到历时性的内在生命体验。⑦
《五行》讲“见而知之”者“智”,“闻而知之”者“圣”。《孟子·尽心下》也讲到这一点。“闻而知之”者,皆于文化、文明、思想有所原创者;而“见而知之”者,则只是有所继承者。这与《礼记·乐记》所说的“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明圣者,述作之谓也”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圣的“作”或原创性,表现为与天地内在精神上的沟通、对此天人合一之真理内容的把握及在此基础上所实现之思想和人文创制。《乐记》说“作者”“知礼乐之情”,下文又说“穷本知变,乐之情也”,就说明了这一点。“述者”则偏于外的认知。故以“识礼乐之文”和“明”作说明。“识礼乐之文”,或者“述”从表象上“看”即可,此由乎“见而知之”。而“知礼乐之情”,“穷本知变”,则是“作”,乃必由乎心灵的原创。
正因为《五行》篇所谓圣与“闻”的听觉意识相联系,所以,它特别注意圣与“乐”的关系。它用“玉色”来形容“智”,而用“玉音”来形容“圣”。其实,其以“玉音”说圣,决不仅是一种形容。《五行》用“乐”的“金声玉振”来论圣之集大成:“金声,善也。玉音,圣也。善,人道也。德,天道也。唯有德者,然后能金声而玉振之。不聪不明,不圣不智,不智不仁,不仁不安,不安不乐,不乐无德。”这个说法,以后孟子也在“接着讲”。孟子亦用“金声玉振”来说明孔子为圣人之集大成者。《孟子·万章下》:“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孟子还在讲“仁义礼智圣”五行的同时,又讲“仁义礼智乐”。《孟子·离娄上》:“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五行》从听觉意识和音乐的角度讲“圣”德,孟子既言“仁义礼智圣”,又讲“仁义礼智乐”,其中有甚深意味。一方面,儒家认为礼乐同源,而“乐”直接关涉人的内在的情感生活,其化人也速。而圣的成就与自由,亦必在这种内在的心灵和情感之创造性的转变的历程中见其功。《礼记·乐记》论“乐”的教化功能说:“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这段话和前引《孟子》及《五行》篇以“金声玉振”言圣德的话,精神完全一致,可以互参。另一方面,乐具有感通天人之作用。《乐记》说:“大乐与天地同和”,“乐者天地之和也”,“乐著大始,而礼居成物”,圣的成就亦具有此种内在的沟通天人的意义。
《五行》篇由“乐”而引申出一个聪、明、圣、智、仁、安、乐、德、天道的观念序列。同时,前引《乐记》的话,亦由乐以治心,引发出了一个乐、安、久、天、神的观念序列。这是两个在精神上完全一致的序列。音乐可以与天地相通,乐师、瞽史有能力以律吕和谐来沟通天人,这在古书中不乏其例。《五行》篇及思孟的系统,继承了这一点。荀子从“五行说”的意义上批评思孟为神秘主义,绝非无的放矢的臆说。
四、慎独与贵心
郭店简儒家类著作,显现出一种明显的“贵心”倾向。上文讲《五行》的圣、智系统,实即体现了这一点。“仁义礼智圣”五行所表现之圣德,其重要的特点是重听觉意识,由此关涉对“乐”,对乐之通天人的强调。我们从郭店简其他篇章中,亦可以看到对乐教的重视。如《性自命出》重“心术”:“凡道,心术为主。”又:“凡学者求其心为难,从其所为,近得之矣,不如以乐之速也。”重乐教,其实就是强调心的修养的重要。
按儒家的看法,礼和乐,都根源于情。不过礼之功用要在外范和节制;乐则直接能够感动人之内心的情感,从而具有潜移默化的感化人心和移风易俗之作用。从孟、荀两家的比较来看,孟子的重乐与荀子的重礼,不仅涉及教化之道的问题,更涉及对心性和道德本原的不同理解。《五行》篇重乐,同时亦在修养成德上转向对内心自觉和情感生活之创造性转变的强调。其对“慎独”问题的讨论,则体现了它对作为仪式系统的“礼”的看法。《五行》中关于“慎独”的理论很有特色:
“淑人君子,其仪一也”。能为一,然后能为君子,[君子]慎其独也。
“[瞻望弗及],泣涕如雨”。能“差池其羽”,然后能至哀,君子慎其[独也]。
[君]子之为善也,有与始,有与终也。君子之为德也,[有与始,无与]终也。⑧
《礼记》的《大学》、《中庸》、《礼器》诸篇皆言及“慎独”。观其言“慎独”之义,一言修为工夫,其要点在一个“慎”字。所以,郑玄解《中庸》首章论“慎独”说:“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但为什么要讲此“慎”的工夫?这就追溯到一个更深的层面,那就是人的存在是内外一体的,诚于中必形于外,心广体胖,德不可掩。形色与内心生活,是互成互体的两面,不可分割。而诚中形外的德化之效,更为儒家所重视。这一点,《大学》、《中庸》都讲到了。所以,此“独”之所重,乃在于人的内心生活之自由的完成。这就涉及在成德上人之内心情感与作为规范性的礼仪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引郭简《五行》的话,讲的就是这个问题。
《礼记·礼器》也讲到这一点,可以参照理解:“礼之以少为贵者,以其内心也……是故君子慎其独也”。注重“礼”的形式方面少一些,强调对内心的关注,这是“慎独”的更深层面的意义,它关注在“独”的内涵,而不是“慎”的工夫。《五行》的“慎独”说,讲的就是这一方面的意义。
《礼器》讲圣人立礼,应关注礼之有外内、多少、大小、高下、文素等不同的方面,“礼之以少为贵”,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五行》所言“慎独”,则是“仁义礼智圣”五行之和谐为一所达到的最高的德性成就,表现了一种根本的思想学术取向。这是应予注意的。
帛书《五行》之《说》的部分,对这个“慎独”说有系统的解说。帛书《五行》的解释如下:
“能为一,然后能为君子”,能为一者,言能以多[为一]。以多为一也者,言能以夫[五]为一也。“君子慎其独”,慎其独也者,言舍夫五而慎其心之谓[独]。[独]然后一。一也者,夫五夫为[一]心也,然后德之一也,乃德已,德犹天也。
不在衰绖也然后能[隆]哀。夫丧,正绖修领而哀杀矣,其至内者之不在外也。是之谓独,独也者,舍体也。
“君子之为善也,有与始,有与终”,言与其体始,与其体终也。“君子之为德也,有与始,无【与终”。有与始者,言】与其体始;无与终者,言舍其体而独其心也。⑨
这两者结合起来,可以看出《五行》的“慎独”是把礼的仪式系统转化为内心的自由。“一”指五行的归于一心。“有与始”、“有与终”、“无与终”,指“与其体始”、“与其体终”、“舍其体而独其心”。这个“体”字,学者多解释为身体。这是不对的。简本由“至哀”而言“慎独”。而帛书《五行》的《说》则将其解释为“舍体”“独心”。而这个舍体独心,是在强调“哀”的内心情感的充分表现。这很合乎郭店简《五行》的精神。所以,这个“体”字,应是指礼的形式而言。《礼记·孔子闲居》讲“三无”:“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孔颖达《正义》:“此三者,皆谓行之在心,外无形状,故称无也。”这应是“舍体”最恰当的解释。
这样,郭店简《五行》所说的“[君]子之为善也,有与始,有与终也。君子之为德也,[有与始,无与]终也”,就可以得到一个恰当的解释。“与其体始,与其体终”,是说始终勉力行礼,这只是“善”。而“有与始,无与终”之所以可称作“德”,而与天道合一者,它已经完全摆脱了礼仪形式的外在束缚,而完全达到了行为的自然和自由。也就是孔子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亦与《中庸》:“诚者,天之道也……诚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从容中道,圣人也”之义相合。
强调圣德合天道,是内心的自由而不由乎外,这是思孟五行说的根本精神。
《五行》由圣德与听觉意识及“乐”之间的深刻关联揭示出圣德与内心自由的关系,由慎独之独特内涵强调转化礼之形式性而归于一心的意义,皆突出了“心”之修养的必要性。这些,实与其“贵心”的观念相关。
《五行》篇有“耳目鼻口手足六者,心之役也”之说。帛书《五行》的《说》部则由之引申出心好仁义而“贵心”的看法。
“耳目鼻口手足六者,心之役也。”耳目也者,悦声色者也;鼻口者,悦臭味者也;手足者,悦勶(佚)馀(愉)者也。<心>也者,悦仁义者也。之(此)数体者皆有悦也,而六者为心役,何<也>?曰:心贵也。有天下之美声色于此,不义,则不听弗视也。有天下之美臭味于此,不义,则弗求弗食也。居而不间尊长者,不义,则弗为之矣。何居?曰:几不□<胜>□,小不胜大,贱不胜贵也哉!故曰心之役也。耳目鼻口手足六者,人□□,□<人>体之小者也。心,人□□,人体之大者也,故曰君也。⑩
帛书《五行》论人心,提出“心贵”说。此言“心贵”,要在“心悦仁义”。由此,区分出“大体”与“小体”,以“心”为“人体之大者”,而以感官为“人体之小者”。这便涉及心性与道德本原的问题。孟子论人的存在,亦区别“大体”与“小体”,强调“心”作为“思”之官的主宰作用以“先立乎其大”(《孟子·告子上》),又言“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理义”为“人心所同然”之“好”(《孟子·告子上》),这同《五行》篇“耳目鼻口手足六者为心役”之说以及帛书《说》文所作之引申,在精神上是高度一致的。当然,孟子的思想更加丰富细密,它完善了儒学关于心性和道德本原的观念和思想系统。
五、心、性与情、才
陈荣捷先生研究孔子后学,揭示出一个重要的特点,即从《礼记》和《家语》看,孔子殁后,丧祭礼和孝道成为弟子讨论的中心问题。(11)丧祭礼和孝道关乎亲亲。重情,尤其是亲亲之情,这在郭店简中也有突出的表现。
郭店简讲伦理,很重视“夫妇、父子、君臣”、“六位”和“圣智、仁义、忠信”、“六德”。而“六德”对应于“六位”,构成后者的德性内容。对此,不仅《六德》篇有集中的讨论,《成之闻之》更把它看做天所降之“大常”的具体内容。《成之闻之》:“天登大常,以理人伦,制为君臣之义,作为父子之亲,分为夫妇之辨。是故……君子治人伦以顺天德。”又:“昔者君子有言曰‘圣人天德’何?言慎求之于己,而可以至顺天常矣……是故君子慎六位,以祀天常。”由此可见“六位”、“六德”的重要意义。应该注意,这里的“圣人天德”以及求己、慎六位而能达天常的思想,正与五行之和的圣德可达天道的观念一致,证明它们都属于思孟的思想系统。
而“六德”、“六位”,其所重,正在亲亲之情。《六德》篇提出“仁内义外”,说明了这一点:
仁,内也。义,外也。礼乐,共也。内立父、子、夫也,外立君、臣、妇也。疏斩布绖杖,为父也,为君亦然。疏衰齐牡麻绖,为昆弟也,为妻亦然。袒免,为宗族也,为朋友亦然。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为昆弟绝妻,不为妻绝昆弟。为宗族疾朋友,不为朋友疾宗族。人有六德,三亲不断。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斩恩。(12)
这个仁内义外说,讲的是家族伦理与社会伦理在治理原则上有不同的特征和偏重。这和孟子所批评的告子的仁内义外说的角度有所不同。这里一是强调亲亲重于尊尊,所谓“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二是强调尊尊的社会伦理规定本原于亲亲的原则。可以结合《礼记·丧服四制》和《孝经·士章》来理解这一点。
《礼记·丧服四制》说:“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贵贵尊尊,义之大者也。故为君亦斩衰三年,以义制者也……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之也。”《孝经·士章》说:“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丧服四制》和《孝经·士章》揭示出“父”的兼具“亲亲”与“贵贵尊尊”这一特征,从理论上更清楚地说明了这内与外的内在联系和区别。“父亲”这个角色,兼具“爱”、“亲亲”与“敬”、“尊尊”这两面,所以,社会伦理可以从家族伦理中推出,社会伦理应以家族伦理为本原。下文说“先王之教民也,始于孝弟”,也是这个意思。由此可见《六德》之重亲亲之情。
从内容上看,《唐虞之道》乃以亲亲、尊贤言仁、义,并由此理解禅让之义:“尧舜之行,爱亲尊贤。爱亲故孝,尊贤故禅……孝,仁之冕也;禅,义之至也……爱亲忘贤,仁而未义也;尊贤遗亲,义而未仁也……爱亲尊贤,虞舜其人也。”又:“禅也者,上德授贤之谓也。上德则天下有君而世明。授贤则民兴效而化乎道。”(13)此以亲亲、尊贤释仁义,以尊贤或上德授贤释禅让之义。那么,从禅让的角度看,这个“尊贤”或“上德授贤”与“亲亲”是什么关系?《唐虞之道》说:“古者尧之与舜也:闻舜孝,知其能养天下之老也;闻舜弟,知其能事天下之长也;闻舜慈乎弟[象□□,知其能]为民主也。故其为瞽盲子也,甚孝;及其为尧臣也,甚忠;尧禅天下而授之,南面而王天下,而甚君。故尧之禅乎舜也,如此也。”由此看来,尧之以“尊贤”或“上德授贤”为内容的禅让,完全被归结为孝弟亲亲之德。“亲亲”与“尊贤”、孝与忠,表现的是内与外、血缘伦理与社会伦理的关系。
郭店简《性自命出》篇从比较普遍的理论角度提出了一套以性情论为核心的性命天道论,以为其治心成德的教化修养论提供根据。《性自命出》开首一段说:
凡人虽有性,心无定志,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定。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知情者能出之,知义者能纳之。好恶,性也,所好所恶,物也……凡性为主,物取之也……虽有性,心弗取不出。(14)
这里所说“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和“好恶,性也”都不必视为对“性”所下的定义,而需从“情生于性”或“情出于性”的角度来理解。这里讲“凡人虽有性,心无定志,待物而后作”,又“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又“凡性为主,物取之也”,都是在说,“性”在“心”与“物”相交感中表显于喜怒哀悲或好恶之“情”。这心与物的感应,乃由善恶之趋向表现出来。《性自命出》重乐教,强调“乐”为“求心”之捷径,正是着眼于这个感应。又《性自命出》以为教化成德虽必在人心之感物而起的情态表现上见其功,但并非出离自然,背离其性,对此,性自命出有一个表达,叫做“反善复始”。总而言之,即情言性,在心与物相接的感应上言教化,并以“反善复始”的“复性”义规定此教化成德之本质内涵,这是《性自命出》性情论的特点。
谈到性、心、情的关系,有人认为那是宋儒才讨论的问题。其实,对这个问题,先秦儒家已多有论述,且已构成其性善观念、自力超越价值实现方式的思想依据。《中庸》首章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又“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此言“中和”,其核心内容是“情”(喜怒哀乐)。但是,由于《中庸》在讲天命性道和“中和”的这两段论述之间还隔着一段论“慎独”的话,所以,天命性道与“情”(中和)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不是太清楚。但我们从《性自命出》“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的说法可以显见,《中庸》“喜怒哀乐”之发与未发的中和论,讲的正是“情生于性”的问题。从《中庸》后文也可以知道,在其作者看来,“情”之“中和”便是“尽性”,便是天道之落实与呈显。《中庸》首章未直接讲到“天命之谓性”与“中和”之“情”的关系,其实是把“即情显性”的性情关系当做一个已知的前提了。
在先秦儒家的观念中,出自天命的性,其内容即一个“情”字。在“情”上才能见“性”之本真。由此,才可理解孔子为什么重视人的先天质素对人之成德的意义,才可理解孟子讲“性善”,为什么从“情”上说。正是基于对性、心、情关系的这种理解,先秦儒学形成了其独特的“圣人之道”,就是尽心知性以知天,存心养性以事天。这里,“心”的核心内容是“情”,不是“知”。
情与“才”的关系问题,由孟子提出,“才”即与“气”相关。但在简帛文献中,“气”的问题已经提出,如上《性自命出》所言“喜怒哀悲之气,性也”。这个说法很容易使人把它理解为仅以人的生物本性为内容的所谓“自然人性论”。但是,从上面的分析来看,这里的“气”也许应该理解为人之生命实存之整体,而情感正是此生命实存之表现。《性自命出》即情言性,而教化成德亦是着眼于人心以情应物,从而实现生命实存之转化与提升。
《五行》篇经部虽不言“气”,但是它谈论德性之修养也注意从人之情感、容色等实存方面展开,如说:“仁之思也精,精则察,察则安,安则温,温则悦,悦则戚,戚则亲,亲则爱,爱则玉色,玉色则形,形则仁。”这里对仁之思的描述,从内心态度、情感到形色逐步转化,细致入微。最后落脚于“玉色”,这表征着人之生命实存转化提升之后的整体气象。帛书《五行》之《说》部有“仁气”、“义气”、“礼气”之说,“知君子之所道而然安之,仁气也”;“知君子之所道而然行之,义气也”、“安而敬之……既安之矣,而有愀愀然而敬之者,礼气也”。此“气”,乃指一种与心相关之“情”和力量、冲动之表现。帛书《五行》之《说》部把“气”理解为人的德行之内在的驱动力。它已经注意到德行不仅仅是知和情的问题,道德之知和情之所以具有发行实践的能力,乃是因为它伴随着一种内在的冲动力量:气。气乃是着眼于人之身体性的一个概念。帛书《五行》之《说》部尚未形成一种关于“气”的系统观念用以表征人的身体性。孟子则提出“养气说”,统以“气”表述人的身体性,以志、气并举,从本体论和修养论上系统地论述了身心合一这一原则,从而对性善的观念作了更深一层的阐述。
综上所述,出土文献所呈现的孔孟之间儒家思想开展的丰富图景告诉我们,孔子之后,在他所开启的“内转”之途上,其弟子后学从心性论、修养论、形上学、伦理及政治思想等各方面展开探索,丰富了对人之最本己的能力和可能性及其实践道路的理解。孔子的浑沦圆融的思想体系,通过弟子后学有关心、性、情、气等各种具体论题的讨论,其理论内蕴得以充分展开。有这些探索做铺垫,孟子的出场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注释:
①张光直:《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载《中国青铜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487-496页。
②崔述:《洙泗考信余录》卷3,载《崔东壁遗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78页。
③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94-95页。
④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8页。
⑤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9页。
⑥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8-79页。
⑦李景林:《听——中国哲学证显本体之方式》,载《本体诠释学》第2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⑧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9页。
⑨【】中文字原缺,此据魏启鹏先生《德行校释》校补,成都:巴蜀书社,1991年,第29-32页。
⑩此处引《五行》篇,据庞朴先生《竹帛<五行>篇校注》,见《庞朴文集》第2卷《古墓新知》,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6页。
(11)参阅陈荣捷《初期儒家》第1节、第9节,《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7本,1976年。
(12)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31页。
(13)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5、96页。
(14)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8页。“虽有性,心弗取不出”,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断为“虽有性心,弗取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