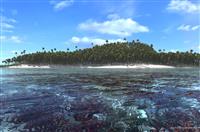战国时期,华夏民族的活动范围西起渭水流域,东至黄河下游,南到长江中下游流域,北达蓟辽地区,在这广阔的地域上,并立着秦、楚、赵、齐、魏、韩、燕等七个诸侯大国,此外,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存在着宋、鲁、赵、周等次要诸侯国。这些大小诸侯国还分别形成了四个大的文化类型,即:三晋文化、荆楚文化、燕齐文化、邹鲁文化,而以三晋文化为主导。由于周、宋、鲁等小国对当时战略格局的演变没有太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分析论述战国时期的兵要地理,当以七雄为具体的对象。
一流与准一流
战国七雄中,以秦、楚、齐为头等强国。秦是所谓的“虎狼之国”,“有吞天下之心”(《战国策·楚策一》)。楚国的实力也很可观,“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交争,其势不两立”(同上),有“横成则秦帝,纵成则楚王”之说。齐国自西周以来始终为东方大国,战国中期更一跃而为第一流强国,史称齐湣王为东帝、秦昭王为西帝即是证明。魏与赵为第二等强国,“魏王拥土千里,带甲三十六万”,“秦王恐之,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战国策·齐策五》)。至于赵国,则是“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强于赵”(《史记》卷六十九《苏秦列传》)。其不同的是,魏国强盛于战国之初,赵国崛起于战国中后期。韩与燕相对较为弱小,史称韩国的战略地位是“今天下散而事秦,则韩最轻矣;天下合而离秦,则韩最弱矣”(《战国策·韩策三》)。又称燕国“燕固弱国,不足畏也”(《战国策·赵策二》)。均说明韩、燕在七雄竞争中处于软弱无力的境地。
“执牛耳”的超一流强国:秦国。
秦是春秋四强之一,据有今陕西省大部和甘肃省一部,即东距黄河桃林、崤函之塞,南接秦岭,西依陇山,北抵平凉、泾川附近。但由于强晋在崤函一带设防,扼其咽喉,使其长期无法东出逐鹿中原,“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史记》卷五《秦本纪》)。
然而,到了战国,历史为秦国提供了新的机遇,强晋分裂为魏、韩、赵三国,力量大大削弱,秦国遂把握时机,重新启动东进的战略。而秦孝公任用商鞅进行变法,开阡陌,废井田,致力耕战,推行“尚首功”的政策,遂使秦国迅速强盛起来,为秦国夺得山东六国的战略优势,并进而兼并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秦国又实施连横策略以破合纵联盟、远交近攻等一系列正确的策略方针,为达到其战略目标开辟了道路。至战国中期,秦国的实力已俨然驾乎山东任何一国之上:“秦地半天下,兵敌四国,被险带河,四塞以为固。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积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难乐死,主明以严,将智以武,虽无出甲,席卷常山之险,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后服者先亡”(《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尤其是秦国的民风尚武乐战,骁勇强悍,“怯于私斗而勇于公仇”,所以秦国的军队战斗力在七雄中为最强,“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荀子·议兵》);“秦性强,其地险,其政严,其赏罚信,其人不让,皆有斗心,故散而自战”(《吴子·料敌》)。这样的军队在作战中自然是所向披靡,攻守皆宜了:“山东之士披甲蒙胄以会战,秦人捐甲徒裼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夫秦卒与山东之卒,犹孟贲之与怯夫;以重力相压,犹乌获之与婴儿”(《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
秦国战略优势地位的确定,是与其兵要地理环境优越相密切联系的。班固尝云:“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特别是秦统治中心关中地区的地理条件更是十分优越,它作为四塞之地,“带山阻河,地势便利”,处于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有利地位,占有了它,对敌便拥有主动和行动的自由。兼之它土地肥饶,水利灌溉系统发达,特产丰富,“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沃野千里,民以富饶”(《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活动,故一直成为秦国实施兼并统一战略的有力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秦国长期贯彻拓土开疆,扩展战略纵深,巩固战略后方,争夺战略要枢的方针,先后攻占河西、上郡、陕等地,完全控制黄河天险与崤函要塞,向南灭亡巴蜀,夺取汉中,向西北攻灭义渠,并进而占领黔中、陶邑、南阳、河内等战略要地,几乎将主要的兵家必争的战略形胜地区大部分都划入了自己的疆域,进一步占有了地理环境上的优势,为展开席卷天下、统一六国的战略行动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用苏秦的话说,就是“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众,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称帝而治”(《史记》卷六十九《苏秦列传》)。
“纵则楚王”的楚国
楚国在战国七雄中疆域最大,全盛时其地奄有今湖北、湖南、安徽三省之全部以及贵州、陕西、河南、山东、江苏之一部。楚文化滋生于江汉流域,具有其独特的风格,很少受周礼传统文化的束缚,故自其立国以来,始终以兼并小国、逐鹿中原为战略上的根本选择,并取得了重大的成果,成为能与秦国相全面抗衡的唯一强国:“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强则秦弱,秦强则楚弱,其势不两立”(同上)。在战国时期,楚国扮演了合纵抗秦之中坚的角色,曾多次出面组织合纵阵线,扼制秦国咄咄逼人的进攻势头。
楚国之所以能发挥这样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和它地大物博、人口众庶、军力充足、兵要地理条件有利直接相关的。众所周知,在战国大部分时间里,楚国的统治中心在郢(今湖北江陵),它地处南北中枢,北据汉沔,襟带江湖,东连吴会,西通巴蜀,远接陕秦,且内阻山河之险,易守难攻。故苏秦有云:“楚,天下之强国也;王(指楚威王),天下之贤王也。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陉塞、郇阳,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夫以楚之强与王之贤,天下莫能当也”(同上)。
然而,楚国在地缘战略上的优势,却随着其政治的腐朽、外交的失败而渐渐消磨殆尽。在战国时期,楚国旧的宗族贵族势力始终强盛,政治黑暗,吏治腐败,上下离心,民怨沸腾,除了楚悼王任用吴起进行改革,稍有振作之外,楚国长期走下坡路,直到走向灭亡。对此,秦将白起曾有准确的分析:“楚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既无良臣,又无守备”(《战国策·魏策一》)。吴起也指出楚军的弱点:“楚性弱,其地广,其政骚,其民疲,故整而不久”(《吴子·料敌》)。尤为致命的是,楚国在外交事务上也屡犯错误,虽然组织和参加合纵抗秦,却往往瞻前顾后、虎头蛇尾,没有能真心全力以赴。又听信纵横家张仪之言,企图与秦国约为“兄弟之国”,轻率地“闭关绝约于齐”,瓦解了与齐国的战略同盟,终陷于孤立挨打的处境。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楚国地虽广,人虽众,兵虽多,地理环境虽优越,也不能不江河日下,危亡必至了。等到秦国据有汉中、巴蜀、黔中之地,“起两军,一军出武关,一军下黔中”(《史记》卷六十九《苏秦列传》),对楚国形成两路夹击之势后,楚国就大势尽去,只能坐以待亡了。
东方领袖齐国
战国中期,齐威王发愤图强,改革吏治,任用邹忌、田忌、孙膑等贤能之士,发展农业生产,增强军事实力,在战国七雄中崭露头角,“齐,负海之国也。地广民众,兵强士勇”(《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及至宣王、湣王之世,“齐之强,天下不能当”(《战国策·齐策一》)。短短近百年内,齐国先后大破魏军于桂陵和马陵,终结了魏国的霸权;伐燕灭宋,张扬齐国声威于天下,左右着当时的战略局势,齐国进入了国势最鼎盛的阶段,“齐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三军之良,五家之兵,进如锋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史记》卷六十九《苏秦列传》)。但是到了乐毅率五国联军伐齐之后,齐虽凭藉田单即墨保卫战的胜利而免于覆灭,但实力已受根本性的损伤,难以重振雄风,更无法对战国历史的进程施加决定性的影响了。
齐国在战国期间的兴衰存亡,固然与其政治的得失、军事的成败、经济的利弊、外交的正误直接有关,但也不能不看到地理环境、民风习俗所起的作用,换言之,在齐国所选择的基本国策、所制定的军事战略或外交斗争方针的背后,蕴含有齐国特定的地理环境以及民风习俗的深层次因素。
齐国擅有渔盐之利,农业发达,工商业繁荣,民众生活比较富裕,这一点司马迁在其《史记·货殖列传》中曾有概括的描述:“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优裕的生活环境,使得齐国民众不乐意于耕战,这直接导致齐国军队战斗力不强,所谓“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荀子·议兵》);“夫齐性刚,其国富,君臣骄奢而简于细民,其政宽而禄不均,一陈两心,前重后轻,故(齐阵)重而不坚”(《吴子·料敌》)云云,正反映了齐军缺乏战斗力的特点。
从战略地理环境来看,齐国处于中原争战之地的边缘,既可西进,雄霸诸侯;亦可退守,固据山川形势,自成格局。即如古人所云:“济清河浊,足以为限,背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悬隔千里之外”(《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在较长的时间里,强秦的兵锋对齐国并不构成太大的威胁,齐国自能御土自守,南面称孤,“今秦之攻齐则不然。倍韩、魏之地,过卫阳晋之道,径乎亢父之险,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比行,百人守险,千人不敢过也。秦虽欲深入,则狼顾,恐韩、魏之议其后也。是故恫疑虚猲,骄矜而不敢进,则秦之不能害齐亦明矣”(《史记》卷六十九《苏秦列传》)。但是正由于齐国拥有“悬隔千里之外”的兵要地理环境,它遂丧失了主动进攻的积极态度,在强秦面前,甘于做“自守之国”,不受兵达四十余年,到了战国末年,更朝秦输诚,坐视秦国连年攻打三晋以及楚、燕,使得秦能够逐一灭掉五国。五国既亡,秦军大举伐齐,兵入临淄,齐终于未能逃脱彻底覆灭的命运。
陷入“四战之地”泥淖而难以自拔的魏国
魏国是从晋国分裂出来的一个诸侯国。地方千里,经济发达,“南有鸿沟、陈、许、郾、昆阳、召陵、舞阳、新都、新郪 ,东有淮、颍、煮枣、无胥,西有长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枣,地方千里。地名虽小,然而田舍庐庑,曾无所刍牧。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绝,輷輷殷殷,若有三军之众”(《史记》卷六十九《苏秦列传》)。魏文侯在位时,礼贤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儒家人物,重用吴起、李悝、西门豹等才能之士,实行改革,富国强兵,先后伐秦、攻打中山。使魏国在战国初年率先崛起,称霸中原。传至其孙魏惠王时,魏国势力达到极盛,史称“梁君伐楚胜齐,制赵、韩之兵,驱十二诸侯以朝天子于孟津”(《战国策·秦策五》),就是魏国强盛,号令诸侯的具体写照。魏国的军队数量庞大、战斗力强劲,在当时也是遐迩闻名,仅吴起为西河守期间,魏军在吴起统率下,“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钧解,辟土四面,拓地千里”(《吴子·图国》)。故世人有云:“魏,天下之强国也。”
然而,从兵要地理环境角度考察,魏国的处境十分不利。它生存空间比较狭窄,战略回旋余地局促,这主要表现为其地四通八达,多面受敌,无险要可供守御,为兵家所必争,在战略上陷于内线作战的被动局面,这一点张仪曾有扼要的评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万。地四平,诸侯四通辐辏,无名山大川之限。从郑至梁二百余里,车驰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与楚境,西与韩境,北与赵境,东与齐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万。梁之地势,
固战场也。梁南与楚而不与齐,则齐攻其东;东与齐而不与赵,则赵攻其北;不合与韩,则韩攻其西;不亲于楚,则楚攻其南。此所谓四分五裂之道也”(《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张仪所言,虽或有夸张之处,但基本上是准确的。
魏国的这一地理形势特点,决定它只能成为兼并战争的主战场,兵连祸结,内外交困,以致严重限制了其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军事强盛,加上它选择了错误的四面出击战略方针,导致河西之地失守于秦,桂陵、马陵之战惨败于齐,更加加速了其由盛转衰的步伐。
令天下忌惮的北方强国:赵国
赵国亦是从晋国分裂出来的诸侯国。其疆域,北邻林胡、楼烦,东北与燕、东胡接界,东与中山、齐为邻,南与卫、魏、韩交错,西亦与魏、韩毗连。赵建国伊始,赵烈侯即任用牛畜、荀欣、徐赵、公仲等贤能之士,初行改革,国内称治。赵武灵王在位时,更推行胡服骑射为标志的大规模改革,使国家实力迅速增强,取得了攻灭中山,北逐楼烦、东胡的重大胜利,成为七雄中后起的强国,“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如赵强。赵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战国策·赵策二》)。赵国强盛之后,多次充当合纵抗秦的首领,成为抵抗秦国东进的头号对手,“收率天下以宾(摈)秦,秦兵不敢出函谷关十五年”(《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
赵国能够支撑战国后期抗秦大局,同样是与其民风习俗与兵要地理环境相联系的。赵地居北,“地薄人众”,其民风“丈夫相聚游戏,悲歌亢慨”,“矜夸功名,报仇过直”,“好气为奸,不事农商,自全晋时,已患其剽悍,而武灵王又益厉之”,“其民鄙朴,少礼文,好射猎”(《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总之其特点是“号为难治”。这样的民风,决定了赵国的军队拥有十分强大的战斗力,造就了廉颇、李牧、赵奢等一代名将,从而在兼并战争中战胜攻取、拓土开疆。就兵要地理环境而言,赵国也处于有利的位置,“西有常山,南有河漳,东有清河,北有燕国”(《战国策·赵策二》),居高临下,难攻易守。
秦国对赵国的强盛和抗秦威胁是心中有数的,它看到“天下之士,众纵相聚于赵,而欲攻秦”(《战国策·秦策三》),是自己兼并天下的巨大障碍,所以必然要以赵国为新的主要打击对象。于是它适时改变出豫西通道以东进的战略方针,改由出晋南豫北通道以攻击赵国,它先是“举安邑而塞女戟,韩之太原绝;下轵道、南阳、高,伐魏绝韩,包二周,即赵自消烁矣”(《战国策·赵策二》),对赵构成战略包围之势,“断赵之右臂”。待时机成熟后,又直接给赵国以凌厉的打击。赵虽利用地势之便,且殊死抗衡,也曾取得过阏与之战等胜利,但终因实力不逮,攻守异势,而处于战略被动的境地,长平一战,赵军主力悉被歼灭,其亡国绝祚,也就指日可待了。地理形势之胜,终竟未能挽救赵国。
弱势的雄强:韩国
韩国作为三晋之一,在战国七雄中国力较为薄弱,地瘠民贫,又四战之地,处境极为艰难。张仪尝言:“韩地险恶山居,五谷所生,非菽而麦,民之食大抵菽饭藿羹。一岁不收,民不厌糟糠。地不过九百里,无二岁之食”(《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应该说,这是符合韩国实际情况的描述。
然而韩国的兵要地理环境也有其优长之处,其疆域虽然不广,但是“北有巩、成皋之固,西有宜阳、商阪之塞,东有宛、穰、洧水,南有陉山,地方九百余里,带甲数十万”(《史记》卷六十九《苏秦列传》)。形势亦堪称险要。尤其是韩国的兵器驰名天下,“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其剑戟)皆陆断牛马,水截鹄雁,当敌则斩坚甲铁幕”(同上)。其军队的战斗力也随之而非常强劲,“以韩卒之勇,被坚甲,蹠劲弩,带利剑,一人当百,不足言也”(同上)。加上韩昭侯在位时,曾任用申不害进行改革,“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
地理环境的有利条件,兼之其他因素,使韩国能够在七雄争战中坚持很长一段时间,这也算得上是一个奇迹了。然而,韩国毕竟弱小,暂时的抗争并不能改变日益削弱的趋势。等到秦军一旦“下甲据宜阳,断韩之上土,东取成皋、荥阳”(《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割裂韩国为两部,韩国所剩下的唯有坐以待毙而已。
中原逐鹿的搅局者:燕国
燕国都蓟(今北京市西南),其疆域“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史记》卷六十九《苏秦列传》)。在春秋时期,燕僻处中原北陲,其战略地位并不显得十分重要。进入战国后,燕国真正开始崛起,与秦楚等六国并驱而争先,“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粟支数年。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佃作而足于枣栗矣。此所谓天府者也”(同上)。尤其是燕昭王任用乐毅五路伐齐,大获全胜,更使燕国声威远播,震动诸侯。
但是燕国毕竟是战国七雄中最弱小的一国,其军队的战斗力从总体上说也不算强,“燕性悫,其民慎,好勇义,寡诈谋,故守而不走”(《吴子·料敌》)。它得以后亡,主要原因是僻在边陲,远离强秦的兵锋,兵要地理环境对其生存有利。对秦国来说,其主要的打击目标是三晋和楚国;而对山东诸国来说,其当务之急,也是设法与强秦抗衡,僻处北方的燕国并不是它们的攻击对象,这诚如苏秦所言,“夫燕之所以不犯被甲兵者,以赵之为蔽其南矣……且夫秦之攻燕也,逾云中、九原,过代、上谷,弥地数千里,虽得燕城,秦计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史记》卷六十九《苏秦列传》)。燕国正是凭借这一有利的兵要地理形势,在强国的争战夹缝中顽强地生存了下来,然而一旦秦国灭亡了三晋,燕国便水到渠成变为秦国刀俎上的鱼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