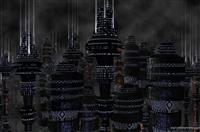摘要:甲午战争后,日本海军在对中国江海持续扩张过程中,以长江流域为重点,逐步将上海到重庆之间的区域都纳入其“巡航警备”范围之内,组成主要针对长江流域的舰队,为本国扩大市场、获取资源提供武力保障,并对沿岸民众反抗、革命运动和地方势力施压。从1917年下半年起,日舰常停泊于长江流域重要口岸;到20世纪2O年代,面对中国反帝浪潮和地方动荡,日本海军日趋暴虐,派水兵上日船护航,并实现了对陆上设施的非法拥有,在上海和汉口形成河用炮舰组装能力。日本海军在扩张过程中,长期与英国保持协同关系。从中华民国建立到国民革命前,日舰在长江流域的实力和口岸分布大体上仅次于英国,成为日本侵华势力的重要分支。
甲午战争后,日本海军以长江流域为重点,进行扩张。但迄今为止,这一问题仍是近代中日关系研究中很薄弱的环节。笔者通过研读以近代日本档案为主的新资料,认为,日本海军在长江流域逐步将触角从上海延伸到重庆,竭力维护本国攫取的权益,打压长江流域的革命浪潮、反帝运动和对其不利的势力。本文聚焦于国民革命运动前日本海军在长江流域扩张的基本形式“巡航警备”,考察其开始实行、逐步推进和强化的过程,并对其后来归结于侵华战争的基本脉络作简要叙述。
一、甲午战争后“巡航警备”的初步展开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对华实行炮舰威胁,维护和加强其侵华权益,而日本也早就有心仿效。日本外务大臣大隈重信所言可谓明证:“英法德美各国在清国之所以能步步实现其权利、获得其利益……主要是靠上述各国平时令很多军舰进出停泊,竭力以有形之威严折清国官民倨傲之念、使之降心相从,隐然充当本国商人的后盾”,“我国政府向来认为有此必要,在前年之战役以前,就令一艘警备舰常驻(上海)。”甲午战争后,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和《中日通商行船条约》,得以“一律享受”西方列强已经攫取的权利,包括随时可派军舰到中国各通商口岸“巡查”、“游弋”,日本海军由此正式开始了对中国江海的扩张。但日本在华势力受制于俄国,还未实现夺取东北南部地区的目标,因此着重在以长江流域为主的南方落实其攫取的权益。
大隈重信于1896年10月15日照会海军大臣:“上海港夙为日清贸易之中心……因战争及马关条约之结果……该港有成为在清国各港我国商人的根据地之势……就我国而言……目下实可谓奠定日清通商方面长久利权基础的关键时刻。”故此,海军对在上海的日侨加以“保护之必要非复昔日可比”,“现在须立即派遣常泊之警备舰,此外还希望再派一艘小舰经常在近海及长江沿岸巡逻,以使对辽东一役尚未特别感觉痛痒的南清顽民得见战胜国之军容、对一般日侨产牛敬畏之念”。海军省立即响应,向上海派出一艘炮舰。1897年2月1日,大隈重信又向海军大臣转达驻沙市领事的建议:“为了扩展帝国贸易,让帝国军舰不时溯航汉口、沙市极为必要。为此,希望在每年5月至11月间,即江水上涨时节,以警备舰巡航于上海与沙市之间。”于是在1897年4月27日,日本海军正式规定:以上海作为两艘日舰的常泊港,驻泊的日舰须分别开往马尾、沙市和汉口停泊。8月6日,海军省又将镇江、芜湖、九江增为“巡航警备”口岸。l902年6月中旬,日本海军组成“常备舰队南清警备枝队”(辖四舰),“以胶州湾以南、香港以北作为巡航区域”。而日舰“和泉”号所拟8月至9月的“巡航”计划称:将从上海出发,在长江分别停靠芦泾港、南京、大通镇、湖口镇、戴家洲、汉口,回程停靠戴家洲、安庆、芜湖、镇江、江阴、吴淞。这反映了日舰在长江中下游“巡航警备”范围的扩充。
日舰在长江流域的“巡航警备”,配合本国当局对华勒索权益。1897年7月8日,即日本驻沙市领事与湖北当局就日租界堤防和道路修筑问题开始谈判的前一天,日舰“大岛”号首次驶抵沙市,后“停泊洋码头江心二旬有余”,以在谈判中加重日方砝码。离开沙市时,该舰还宣称将“游历通商各口岸,以资保护,故往来无定也”。为了保持武力威慑,该舰计划驻留沙市一个月,无奈停泊困难,不得已提前近半个月离开。尽管如此,日本驻沙市领事还是为该舰“大得官民注意”而极为兴奋。次年5月9日,在沙市的湖南客民与轮船招商局的更夫发生纠纷,衍成包括日本领事馆在内的房屋及一些船只被焚事件。事发后,荆州道台很快安排日本领事等撤往汉口,清政府令正在赴京途中的张之洞折回本任处置,湖北当局速派军队赶到沙市昼夜巡逻,仅13天就将所认定的四名“首犯”枭首示众。日本由于此前在有关沙市日租界的交涉中尚未完全如愿,并且试图在其他口岸设立租界,还要预防长江沿岸不稳局面危及日本势力,故借机大做文章。日本海军省接报后,“令‘高雄’号立即赴汉口,‘爱宕’号立即经由汉口赴沙市”。而日本驻上海领事也随即故意向张之洞透露这一消息,以尽早发挥炮舰施压作用。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于5月28日向总理衙门提出五项要求,“催商甚急”。
当时,荆州道台担心“他国军舰来沙,或将导致人心动摇”,张之洞“提出阻止上航”,而日本驻沙市领事永泷久吉却宣称“不能满足这种希望,必须实行兵舰警备”,日本政府则令“爱宕”号抵汉KI后立即开往沙市。在交涉中,永泷久吉假“爱宕”号之威,将与事件毫无关系的日租界护堤修筑费用混入赔款之中,还要求“租界内道路免价豁租”,将租界内土地租价酌减,甚至抛日本政府不曾提出的占据地势高而靠近街区的官地以作为日本领事馆地基的要求。张之洞等最终同意赔偿日本损失、在日本领事馆原址修建新房供其使用,此外还答应承担护堤修筑费用的一半、界内道路用地减价免税、酌减界内租地之价等项。总理衙门也向日本公使承诺:在岳州、福州、三都澳,“如将来他国设有专界,自可允准日本一体照办”。
以一艘军舰配合施压,能勒索到如此可观的权益,日方甚为得意,永泷久吉又提出“仿英国之例,始终在长江配置军舰一两艘”,“为在长江实行警备而制造吃水浅、可在宜昌与汉口之间上下自如、运动相当敏捷之舰”。
提升自身在侵华列强中的地位,是日本在甲午战争后的重要目标之一。1900年爆发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在日本看来,正为此提供了“最初的好舞台”。它除了派海陆军加入联军进犯津京地区之外,还通过加强海军对长江流域的“巡航警备”来贯彻这一企图。当时的长江流域,因实行“东南互保”,中外“官员往来、贸易经营、船舶航行与平时无异”。然而,日本驻长江口岸领事却促请加强日舰的“巡航警备”,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声称:“在长江一带及沿海地方充分实行警备,可直接保护帝国侨民之生命财产,且能间接保护大量侨居此方面之外国人,启伸张帝国威权之端,开利益推扩之绪”。常泊上海的“赤城”号舰长也进言:派数艘军舰到长江方面,“在军略上自不必说,在政略上、商业上亦有最大之必要”。
显然,他们急于抓住时机,向长江流域增派炮舰以增强日本在列强中的分量。于是,从6月中旬起,三艘日舰相继开往上海,其中“八重山”号在七八月间往返于上海和汉口,停靠镇江、南京、芜湖、安庆、九江,在汉口驻泊35天。该舰舰长在此间发出的报告中称,长江上的外国军舰只有英舰和日舰。该舰停泊镇江时,“驻镇各国领事均诣船中,拜会管带日官,茗谈良久而别”。到汉口后,日本领事称:“我国侨民白不必说,各国之人都对‘八重山’号表示热烈欢迎”。显然,当时该舰“巡航警备”的最大效果,就是大大强化了日本海军对“各国之人”的影响力。日本乐此不疲,在10月中旬再派“摩耶”号从上海开往汉口。
还须指出的是,日本海军趁列强出兵上海之机,派陆战队非法上岸驻扎。本来,刘坤一、张之洞在与列强商议“东南互保”时,曾明确要求在上海的各国军舰“约束水手人等,不可登岸”;但各国领事仍于1900年6月17日决定在危急时请求外国军舰派兵上岸;8月6日,驻上海外国海陆军官会议又将浦东防御交给日本海军陆战队。而小田切万寿之助则以日本与上海的“利害关系”“除了英国之外不亚于任何国家”,“提议日本国也向此地派出足够的军队”。于是,日本海军立即秘密编组“枪队”。9月9日,由日本“常备舰队”司令官所率两艘军舰运载到上海的海军陆战队共455人上岸,驻扎杨树浦。1901年9月26日,日本华北驻屯军两个中队与该部换防,直到1902年11月才与别国驻军一同撤出。后来,日本参谋本部论及此事及同期海军陆战队在厦门登岸的行动,归结为“与各国拉关系”。
史实证明,日本海陆军的上述行动,对日本提升在列强中的地位,通过《辛丑条约》等获取新的重大权益起到很大作用。故在40多年后,日本海军将领还对此加以强调,认为“值得特别记忆”。
在不久后爆发的日俄战争中,日本海军“警备”又增添了与欧洲大国对抗的色彩。1904年2月中下旬,日本海军以“俄舰‘曼居尔’号久在上海,我国在长江~带的商船航线因而大受威胁”为由,令三艘军舰开到长江口,派“秋津洲”号停泊吴淞,对上海外围实施警戒,并对清政府扬言:如“听任俄舰所为,则我舰不认为现实为严正中立,将不得不采取认为适当的临机处置”。直到3月底确认“曼居尔”号解除武装后,“秋津洲”号才开往朝鲜海峡。
二、日俄战争后十多年间“巡航警备’’的扩展与变化
(一)“巡航警备”范围向长江上游及支流扩展
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强迫中国将沙市、重庆辟为通商口岸,暴露出其进入长江中上游的强烈欲望。为此,日本在恢复驻汉口领事馆之前,于1896年2月向沙市派驻领事。在1897年后的十年间,日本的大阪商船、湖南汽船,以及大东、日本邮船四会社及其组成的日清汽船株式会社,先后开辟了上海至汉口、汉口至宜昌、汉口至湘潭、汉口至常德与鄱阳湖、镇江至清江浦航线。此外,1907年日本领事报告称,沙市“呈现出我国棉纱独占之态”,出口棉花与树脂、油糟等货主要面向日本;在湖南湘潭,1905年3月调查表明“日本棉纱从两三年前骤然打开了此处的市场,其后以一泻千里之势驱逐了湖北、上海乃至于印度的棉纱,目下完全是日本棉纱独占”;湖南的麻、植物油和油糟类“有望成为对日本的大出口货”,还有很多矿山“尚未着手开采”,又“因长沙开埠为时尚短,外人尚未着手于商业,目下在湖南省从事商业者,以日本人为最”;在重庆,“拥有租界者,唯独有我帝国”,日商在租界内还开办了火柴厂。
在此背景下,日本海军急于向汉口以上的长江干支流推进,为此在1903年和1906年先后向英国购买河用炮舰“隅田”号和“伏见”号,并将它们纳入“南清舰队”(1905年12月组成)。1907年2月1日,“隅田”号舰长报告说:“去年四月,我国吃水浅炮舰……溯江而上,进入可称为我之势力地盘的湖南……横断洞庭湖……开往常德、长沙巡航,返回时又向西溯航鄱阳湖,开到江西省南昌,继而第三次与僚舰‘伏见’号溯江而上,越千海里。到达普通轮船航线的终点宜昌。”日本海军不甘止步于宜昌,认为,在长江上游,日本人的“工商、教育稳步与年俱增,目下正值日益增进其势力之时,且在不久的将来,清国内地富源开发程度会不断提升,故我炮舰得其时而逐步溯航一事就更为必要”;还必须“与在长江上游汲汲谋求领先地位的英、德比肩,发扬国威,得权力之均衡”。因此,“隅田”号、“伏见”号在1906年11月下旬开到宜昌后,两舰舰长立即雇用民船,用四天时间溯江勘察航道。后来,“伏见”号舰长桂赖三继续对宜昌至重庆之问的航道作“详细调查”,而该舰在1911年5月20日首次开到重庆。
1909年1月,“南清舰队”改称“第三舰队”,将河用炮舰主要用于汉口以上长江干支流,而军舰则一般在长江中下游、东南沿海“巡航警备”。此外,长江中下游的日舰并不以“第三舰队”所辖为限,常有其他军舰来轮替。
日舰停靠口岸主要有江阴、镇江、南京、大通、芜湖、安庆、九江、大冶、汉口、沙市、宜昌、岳州、长沙,此外还有彭泽、嘉鱼、监利、新堤、调关、湘阴等处。在长江上的日舰十分蛮横,如“隅田”号在江西任意“入湖晋省”,以至于别国军舰在被地方官劝阻开入鄱阳湖时,“多以‘隅田’藉口,强行人湖”。
(二)“巡航警备”在日本海军对辛亥革命浪潮施压中的多面展现
1911年,辛亥革命的浪潮从长江流域涌起。此间,日本海军声称,日本“在长江及其附近拥有很大的特殊利益”,故在列强施压的行动中,日本海军应居于重要地位。日舰较之别国军舰,行动更为迅速。1911年5月19日,“第三舰队”司令官得知长沙保路运动“气焰颇盛”,即令在上海的“隅田”号开往长沙,还要求“征用日本籍轮船汽艇,以本队军舰之兵器人员加以临时武装,作为暂用炮艇”。武昌起义爆发时,“隅田”号正在汉口,其迅速开到武昌窥探,“与别国军舰一同派兵登岸,把守租界”;而旗舰“对马”号,则于10月12口抵达汉口,其载有陆战队员130人,远超英、美、德舰所载人数;“第三舰队”司令官被推举为各国海军最高指挥官,该舰舰长则作为各国陆战队司令官指挥租界“防卫”。日本海军的迅速行动,使其一度在驻汉口各国海军中占据主导地位。随后,日本加紧增派军舰,到11月中旬,在汉口驻舰六艘,在上海、吴淞、镇江、南京、芜湖、安庆、九江、大冶、沙市、长沙各驻舰一艘,总数是平口的三倍多,仅次于英国。截至1912年2月上旬,日舰在长江流域驻泊口岸与英舰相当,但因其溯航重庆的能力尚弱,总体上居于第二位。为保持日本海军的优势地位,I911年10月下旬,日本向英国提出在汉口的“各国舰队首席指挥官”位置“以两国之任何一方占据”,得到英国的积极支持;到1913年10月,“所有各国驻泊沿江保商兵舰,多已驶回本国,惟日本藉口该国商人在南京被戕之故,不但不退去兵舰,且有增加”。
面对革命浪潮,日本海军省规定:为了庇护日侨和口船,日舰“可采取认为必要的方法,且在必要时使用兵力干涉之”;同时,还开列了在长江流域“有必要予以特别保护”的对象,即作为汉冶萍公司向日本借款抵押的九江和大冶的铁矿山,大冶铁矿运输矿石的铁路和缆车轨道、车辆房屋,下陆机械修理厂、萍乡煤矿、汉阳铁厂、以股票作为对日借款担保的南浔铁路,以及向日本举债的既济水电公司、武昌纺纱局、扬子机器局等,还特别强调“大冶与我国关系最深,故要以兵力占领”。
日舰奉命在长江各口岸竭力庇护日侨,同时还为日本商船充当后盾。1911年I1月2日,因长沙港守军鸣枪,流弹落到日船“湘江丸”上,驻泊该港的“隅田”号舰长提出“严重抗议”,迫使当局“道歉”并表示严处当事者。此后不久,在汉口的“第三舰队”司令官又“以近来武昌方面屡屡对外国军舰、商船加以炮击,而派‘神风’号载参谋到武昌,与黎(元洪)面会,责其不法行为,令其道歉,保证今后不再对外国舰船加以炮击”。1911年11月下旬,镇江革命党人与海关人员一同临检日本商船,亦遭驻该港的“如月”号舰长“抗议”而被迫中止。由于日本在长江流域重点维护的“权益”集中于武汉和大冶,日本海军除了长驻军舰之外,还于1911年10月12日至1912年1月3日、1912年2月5日至1913年4月6日之间分别派陆战队驻扎。在武汉,日本海军是外国租界的主要“防卫”力量。1911年10月12日,“第三舰队”司令官阻止两艘舰在租界附近江面对武昌进行炮战,理由是这会给租界带来危险;10月14日,又不许湖广总督瑞潋所乘“建威”号等停泊德、日租界江面;10月16日,要求清政府海军在“向叛军进攻时勿将军舰配置于炮火可能危及租界的位置”。对于汉阳铁厂,日本海军也有“保护”预案,在该厂被革命军占领的情况下,要求日方充分保护”,并严加监视。1912年1月初,日本陆军派遣队侵入汉口、接手租界“防卫”后,日本海军听到所谓中方转移汉阳铁厂重要设备的讹传,便马上敦促该队阻止。即使在革命高潮后,驻泊汉口的日舰舰长仍于l914年3月17日与陆军派遣队司令官和代理总领事订立《关于警备的协定》,保证在危急情况下“掩护在武昌、汉阳的日侨撤退”;对于陆军“守备”日租界和向汉阳铁厂、既济水电公司、东亚制粉会社,以及必要时攻击“暴徒”之“重点”,都尽可能予以支援。
大冶铁矿被日本视为其在长江流域头等重要的“权益”。因此,武昌起义刚刚爆发时,日本驻华公使就要求速派军舰加以“保护”,日本海军也计划直接占领。因该矿对日本输出铁矿石没有中断,陆战队兵力又难以同时兼顾汉口与大冶两地,才使其出兵计划有所延迟。1911年12月下旬,湖北当局宣布大冶矿务局“理合由鄂军政府管辖”。“第三舰队”司令官立即派人逼迫黎元洪收回指令;日本海军省则于1912年1月初作出向大冶派驻陆战队的决定;尽管黎元洪被迫召回了没收大冶铁矿的人员,但一支由47人组成的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仍然于2月5日开到大冶,随后“建造兵房”,驻扎一年两个月之久。此间,湖北军政府一再谴责日方所为“与约章殊相违悖”,要求其撤出陆战队,日本海军却置之不理。
1911年10月17日,日本海军大臣传令“第三舰队”司令官:“如有清国官宪或叛徒投身于我舰艇、要求保护,可根据外务令的精神予以处置。”该舰队遵令而行,首先对藏身汉口日租界、请求日本总领事派舰护送其逃离的汉阳铁政局总办李维格提供“保护”,11月7日,派“满洲”号将其送往上海,途中还在大冶让日本技师西泽公雄上舰,就确保汉阳铁厂向日本供应生铁、中日在上海浦东“合办”新的大铁厂等事宜,与李密谈。11月16日,“满洲”号途经安庆时,又“收容”了逃亡的安徽巡抚朱家宝。12月1日,两江总督张人骏、江宁将军铁良、江南提督张勋等逃到日本驻南京领事馆,而驻泊该地的“秋津洲”号“收容”了他们,“第三舰队”司令官还令将他们送往日本。此外,日本海军对其认为有潜在利用价值并有留日经历的革命党人,也紧盯其动向,甚至提供“保护”。如身为阳夏战争总指挥的黄兴,11月29日兵败后乘日船离汉,12月1日抵沪,日本海军于第一时间获悉,并提供了“保护”;1913年7月下旬,黄兴反袁失败,“第三舰队”司令官又传令在南京的“龙田”号予以“收容保护”。“二次革命”中在湖口起兵反袁失败的李烈钧等人,于1913年9月8日乘日船到汉口,亦由“伏见”号护送到大冶,转乘日船去日本。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海军完全丧失抵御外侮的能力,但在华日舰仍严密监视其动向,即使在辛亥革命高潮期间,也将其一举一动详加记录、随时上报。究其原因,如同“南清舰队”司令官武富邦鼎所言,这是图谋将中国海军的主导权“完全收于日本海军之一手,以作为将来在清国扶植我利权的一种手段”。从1911年l1月上旬开始,长江流域的舰陆续起义,后来南京又成为革命中心。12月中旬,“第三舰队”司令官向海军大臣汇报,认为中国海军“在和平光复后会有一大革新”。12月25日,在上海的加藤中佐又报告孙中山正物色外国人做海军顾问、海军大佐太田三治郎欲利用深得孙中山信任的池亨吉谋取该职。日本海军省认为有机可乘,于1912年年初派高级间谍、海军少将外波内藤吉来华,密令其与革命军的海军保持“声气密切相通,为今后加深清国海军对我海军的信赖之念、以我海军势力为模范打下基础”。
监视中国社会状况和列强在华动向、获取相关情报,是日舰在中国江海“巡航警备”的日常任务之一。在辛亥革命高潮掀起之后,日本海军为了伺机扩充在华权益、插手中国内政,更是大肆展开谍报活动。长江流域的“第三舰队”司令官不仅随时向海军大臣等电告各种情况,还在1911年10月16日至1913年10月6日间,陆续寄出《关于清国事变的警备报告》(1913年8月12日改为《关于支那事变的警备报告》)共238号;1911年11月10日起先后寄出《关于清国事变的密报》若干号。这些报告、密报扼要叙述在该舰队“巡航警备”区域内发生的战争、事变、交涉、日舰和别国海陆军的行动,内容主要来自各“警备舰”从驻泊口岸发出的电报和报告、日谍提供的情报,从中可见这些“警备舰”在对革命浪潮施压的同时,还充当了特殊谍报点,刺探、搜集驻泊口岸情报,并通过舰载无线电台传递给旗舰或在上海的海军武官。日本海军的首脑机关,也极为看重来自“第三舰队”等方面的情报,分别于1911年10月14日、24日开始编印《湖北事变通报》(后改为《清国事变通报》)、《清国革命乱特报》。中华民国成立后,日本海军进一步强化谍报活动,于1912年1月1口派外波内藤吉少将来华,令其“滞留于上海,视需要往来于长江沿岸及闽浙沿岸”,与日本驻华文武官员、“第三舰队”司令官、所在地日舰保持联络,“观察周围官革两军形势,调查各外国相关态度及动向,且按需要探求将来增进帝国地步之手段,加以报告”。
(三)日德开战后实行无“巡航”的“警备”
长江流域的日本海军在对辛亥革命浪潮施压过程中,军事实力大增,其“巡航警备”所涉范围之广也是前所未有。但到1914年,日本伺机夺取德国在华及太平洋的势力范围,由此,其海军在华兵力部署和运用也发生了变化,8月25日,日军向胶州湾大举出动之后,除将不能航海的三艘河用炮舰留在上海之外,不再派日舰到长江“巡航”。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17年8月北洋政府对德、奥宣战。
这一变化并不意味着日本停止对长江流域的“警备”。实际情况则是:早在1912年1月,一支700多人的日本陆军派遣队就侵入汉口,当日舰离开时,日本势力依然盘踞在对长江流域保持威慑的口岸;日舰在攻取胶州湾之后,也可迅速开进长江,与驻汉口日军协同动武。可见,即使没有日舰“巡航”,长江流域仍处于日本的威胁下。这种威胁的存在,于1915年5月上旬日本海军为配合其政府逼迫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而采取的行动中充分显示出来。当时,日本海军省令“第二舰队”司令官亲率两艘军舰和一个水雷战队速往长江口,此外还向长江口派出一个战队,同时要求驻上海海军为日舰进入长江流域准备领航员、提供情报、与在长江外的舰队保持呼应。5月6日,日舰在中国沿海的配置是:长江附近战舰八艘、驱逐舰十艘,此外马公附近战舰五艘,秦皇岛附近战舰三艘、水雷艇四艘。各路日舰都进入临战状态,其中“第二舰队”的作战计划要点是:“尽快控制江口要地,进而破坏长江干流水陆防御设施及敌舰艇,扼制从外海通往汉口的水路,以确保通航自由、保护居留民、与汉口驻屯军联络。必要时掩护陆军溯江而上,与之协同作战。”直到5月9日,袁世凯被迫接受日本的最后通牒,各路日舰才奉命返航。
但日本对无日舰“巡航”很不甘心。在“第二舰队”从长江口返航后,驻上海的海军少佐中岛晋上书军令部长称,It舰离开长江流域导致“不知我兵力之大的该流域支那人日益发生轻蔑帝国之念”,要“不失时机地采取让我舰队进人的手段,使日本人在长江一带安堵,得以自由发展”。1916年4月,日本海军开始策划恢复在中国南方江海的“巡航”,拟编组“第五战队”,以其与一个驱逐队“主要负责长江一带的警备”。
三、北洋政府对德、奥宣战后“巡航警备”的强化
(一)“巡航警备”强度加大
1917年8月14日,北洋政府对德、奥宣战。由此,中日两国在名义上同属协约国,但这丝毫没有使日本放缓对中国的侵略步伐,日本海军借机将其在中国南方江海,特别是长江流域的“巡航”恢复,并进一步强化。
1917年2月27日,日本海军将留在上海的名义上解除了武装的三艘河用炮舰编入“第五战队”,“令其担任长江流域警备”;日本国内舆论也叫嚣将这三艘炮舰“重行武装”。8月11日又宣称:“在支那对德宣战实施后,我舰船在该国港湾进出停泊将恢复到与平时同样的地位,从而不必基于中立规则受到拘束。”北洋政府宣战后,日本海军分别令“隅田”号在上海附近、“伏见”号到汉口、“鸟羽”号到重庆担任“警备”。
12月15日,日本海军组建隶属于“第三舰队”、辖五艘军舰的“第七战队”,规定其以长江流域为主要“行动区域”,“在长江一带陷于兵燹之厄时……将一部分兵力配置于大冶、汉阳等地”;必要时以陆战队与日本陆军“联合行动”、与外国海陆军“协同行动”。1918年8月中旬,日本海军又将“第七战队”改为“遣支舰队”,令其“当下主要执行长江流域的警备任务”。l919年6月,为对抗中国的五四运动,“遣支舰队”又增加了两艘军舰和由四艘驱逐舰组成的“第二十九驱逐队”。7月下旬,“遣支舰队”更名为“第一遣外舰队”。无论是“第五战队”、“第七战队”还是“遣支舰队”,都将长江流域作为主要行动区域;而“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在1921年行动计划中所列各舰行动范围,也都在长江流域以内。还应注意的是,日本海军在恢复对长江流域“巡航”之初,就将上海到重庆之间的长江干支流全都囊括在“巡航”范围内,为此将三艘炮舰分别配置于长江流域的要津重庆、汉口、上海。先前口舰开到重庆只是间或为之,但从1917年10月下旬起,就将重庆作为其常泊港。至于从口俄战争后就已是常泊港的汉口,更是常年有口舰驻泊。日本海军在长江流域“巡航警备”的强度进一步加大了。
这与日本亟欲巩固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长江流域扩张的“成果”密不可分。1919年,日本的对华出口额、进口额较之1913年,分别增长了1.89倍和4.26倍;其中,长江流域对口进口额、1916年至1919年对日出口额,都超过同期中国对日本进、出口总额的半数。《从经济角度看长江一带》一书声称:“长江流域是支那富源,又是支那经济中心地……我国工商业者登上这个舞台……侵入各先进国根基深、势力厚的范围内,在商场中逐步雄踞一方,实在可喜之至。”“战后各国的经济竞争将口益激化、在长江一带的商战将更为炽烈,是毫无疑义的。我国是否真有准备、安排和实力打赢这场炽烈的战后商战?这难道不是刻下最值得研究的问题吗?”而日本海军加大在长江流域“巡航警备”的强度,正是为了巩固日本在长江流域的既得权益,并为以后打赢所谓“商战”提供保障。
另外,1917年9月,中国爆发了“护法战争”,川、湘之间区域成为南北军队的主要战场,其后多年硝烟不断。在日本海军看来,“长江一带纷扰混沌,事态不易收拾”。这既给日本在长江中上游进行贸易、获取资源等带来较多风险,也使日本有可能从中寻求插手中国内政的机会,从而也就决定了日舰势必对长江中上游强化“巡航警备”,而重庆从1917年10月开始成为口舰的常泊港,也与此密切相关。
(二)与英美海军“协同行动”及在“巡航警备”中日趋暴虐
随着日本海军强化在长江流域的“巡航警备”,日本的贸易较别国一度更有“保障”。因此,l918年4月20日,日本海军大臣收到日清汽船株式会社社长的感谢信,内称“此前长江上游支那南北军交战……英国、支那等国航行的船舶都停止了航行,唯有本会社船舶承蒙帝国海军周到的保护,没有缺航一次”。看到日本海军的“巡航警备”很有“成效”,美国在华海军于1918年1月29日提出倡议,要求日、美、英等国海军在长江流域“为保护盟国侨民生命及财产而协同行动”,且“由所在地的首席指挥官山冈少将负责全盘处置”。2月4日,“第七战队”司令官传令所辖各舰舰长,告知日、英、美三国海军达成协议,“为保护盟国侨民生命及通商航运采取协同行动”,令各舰“对于盟国的商船也要保护”。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欧美势力卷土重来数年后,l924年9月,针对直皖军阀爆发“江浙战争”,外国势力宣称要实行所谓“黄浦江中立”,日本海军又与英美一同增派军舰、陆战队在上海上岸,担任四川北路的“防卫”。其间,日本陆战队不受英国节制,但还是与英美海军“充分协同”。可见,无论日本海军在列强中的地位是主是从,与英美协同行动却是其一贯主张。
此外还须看到,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日本海军在“巡航警备”中日趋暴虐。1920年6月上中旬,谭延闯所部湘军趁吴佩孚率军北上之机进攻衡州、长沙,“伏见”号等三艘日舰开到长沙江面实行“警备”,与谭部发生对抗,“伏见”号开火,造成谭部伤亡。此即所谓“长沙事件”。1921年8月27日,“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抱怨“炮舰不足”,“除了重庆之外,宜昌、沙市、常德、长沙(这些地方的侨民都要求派遣军舰)、岳州(为了以无线电台联络)也各需一艘,汉口则需两艘(保护商船),共计八艘,此外九江也有此愿望”。他还叫嚣要对不利于日本军舰、商船的南方军队“予以痛击”,哪怕由此“惹出极大麻烦”、“引发冲突”也要出手。10月下旬,该舰队侦知在广东的孙中山有北伐动向,便立即制订以武力对抗的预案,准备在长沙、宜昌、沙市、城陵矶、汉口、九江、芜湖、南京加强日舰“警备”,必要时向长沙派遣陆战队,如北伐军打到苏、皖,则进一步增大“警备兵力”。日本海军省收到报告后,也准备作相关部署。
1923年3月旅大租借期满后,日本拒不将其归还中国,激发中国民众的反抗运动。5月14日,日船“大元丸”抵达沙市,“学生上船检查运至沙市、宜昌之日货”,而该船招来“伏见”号,该舰“立派陆战队将学生驱出船外,并向之开枪,于是激动众愤,冲突遂起”,“华人受重伤者甚众”。6月1日,长沙民众在日清汽船株式会社及戴生昌公司船舶停靠的码头举行抵制日船航运活动,而在此“警备”的“伏见”号又派陆战队上岸镇压,开枪打死2人、重伤20多人,造成震惊中外的“六一惨案”。中国民众的愤怒无以复加,如《东方杂志》所言:“一时函电纷驰,都主张速撤日舰,再向日本严重交涉。”在湖南各地和武汉、南昌、安庆、芜湖、上海、北京、济南等地,以及在日本的数千留学生中,抗议风暴尤为猛烈,日本的贸易航运也由此遭到痛击。但日方完全无视中方的强烈谴责和正当要求,不仅拒不从长沙撤舰,还加紧向长江增派军舰,并为维持日船航运贸易,开始派武装水兵护航。8月21日,“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要求仿效英国海军,赋予其权限,对在宜昌与重庆之间航行的日船加以武装。还未得到正式批准,他就向从宜昌开往涪州的日清汽船株式会社的“云阳丸”与“德阳丸”分别派驻武装水兵12人。“德阳丸”在10月16日与重庆驻军交火,打死打伤约50人。此外,9月23日以后,“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对往返于汉口与湘潭之间的日船,也派驻了由八名水兵组成的机枪队。上述情况表明,在长江流域竭力充当本国既得利益维护者的日本海军,其所谓的“巡航警备”演变为扩大和巩固在华势力以及对中国民众反帝运动进行武力镇压的工具。
(三)非法拥有陆上设施及在沪、汉形成组装河用炮舰能力
近代中外条约从未给予外国海军在通商口岸拥有陆上设施的权利。但是,日本海军为了便于其官兵休养、保障“巡航警备”的长期实行,仿效英国等国海军,从清末就开始设法在长江重要口岸建立陆上设施。在上海,于1910年1月前后设立了“第三舰队兵员宿泊所”;1913年3月,又主要靠日商捐款,在上海公共租界内汇山公园边占地350多坪,修建了有三层楼、冬夏可分别容纳l00人、200人的“下士卒集会所”。在汉口,则于1913年借得三菱分社在日租界的房屋,设立“下士卒集会所”,1919年10月以后又由在汉口的十家日本商社分担费用,在日租界另行租房供该所之用;1922年7月驻汉口的日本陆军派遣队撤走后,海军于1923年8月下旬接收了其非法修建的部分军营,用作“海军集会所”。在长沙,1917、1918年间,日商在城对岸的水陆洲建房,供水兵休息之用;1921年3月下旬,日本“居留民会”又将该房屋及设备赠给“第一遣外舰队”,用以设立“下士官兵集会所”。在宜昌,“第一遣外舰队”于1923年5月1日设立“下士官兵集会所”。在重庆,日舰官兵起初在日租界内租房;1924年夏,日本“居留民会”决定由日清汽船株式会社出资建房,其他日侨捐建网球场,无偿用作“海军集会所”。在此基础上,日本海军省于1924年2月15日下令:“为满足长江方面行动舰船乘员举行会议和在陆上保健、休养的目的,根据需要在该方面主要停靠地设海军集会所”,“海军集会所由佐世保镇守府管辖,供第一遣外舰队使用”。1924年6月,在上海、汉口、长沙的“海军集会所”正式转为“官营”;而分别设于宜昌桃花岭、重庆日租界内的“海军集会所”,则在1928年12月下旬办理了转为“官营”的手续。这样,以往在长江流域口岸主要由日侨捐建的“下士卒集会所”、“下士官兵集会所”,先后成为由日本海军非法拥有、统一管辖的陆上设施“海军集会所”。
日本海军专用于长江流域“巡航警备”的河用炮舰,绝大多数不能航海,故最早服役的“隅田”号,是l903年在上海委托耶松船厂组装后下水的,“伏见”号也是在1906年由川崎造船所在浦东组装后下水。1922年至1923年,日本海军为了强化“巡航警备”的实力,又在上海和汉口两地分别安排日系上海东华造船会社、受日本控制的扬子机器制造有限公司,各自组装新的河用炮舰,即由神户制钢所制造的“势多”号、“坚田”号,三菱造船所制造的“比良”号、“保津”号。
四、结论
甲午战争后,日本海军长期以长江流域作为对华扩张的重点,逐步将上海至重庆之间的区域纳入所谓“巡航警备”范围之内,使日舰在长江流域各重要口岸的驻泊常态化,其根本动力来自日本在华开辟市场、获取资源的需要,其基本任务是以武力来维护和扩大日本的侵华权益。这一时期,日本海军以炮舰恫吓、陆战队登岸长驻、为日本商船武装护航等手段,大肆打压沿岸反抗运动或不利于日本的力量,所充当的对华压迫者角色,相比同时期在长江流域的欧美海军往往过之。
长江流域的日本海军力量,起初是“常备舰队”派出的一两艘军舰,后历经“南清警备枝队”、“南清舰队”、“第三舰队”(包括隶属于该舰队的“第五战队”、“第七战队”)、“遣支舰队”和“第一遣外舰队”,编制多有变化,在对德开战后的三年间还曾实行无“巡航”“警备”,但基本趋势是其实力逐步增强,且在重要口岸逐步非法拥有服务于“巡航警备”的陆上设施、在上海和汉口具备组装河用炮舰的能力,由此得以充当炮舰政策的得力工具、日本在华军力的重要分支,对长江流域乃至于中国局势的影响不可小视。
日本海军在长江流域的“巡航警备”,原本是步欧美列强后尘,又是在所谓英国在华势力范围内展开,起初在能力上较之英国等国海军相差甚远。但在日俄战争后,其势力扩展迅速,到民国建立前后,日舰在长江流域的数量及分布口岸大体上仅次于英舰,而论其活动面之广,则不亚于其他各国海军,且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国民革命兴起后。对此,仅从日本因素分析,不能充分说明问题。纵观这一时期,英国对日本海军在长江流域的“巡航警备”从未设置障碍、予以扼制,而是彼此“协同”。究其根源,当为英国对日本侵华的支持和利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英国为日本海军在长江流域迅速扩张铺平了道路。
甲午战争至大革命前,正是中国深陷半殖民地泥淖、面对外国入侵几无招架之力的时期,但日本对中国的欺凌,尤其是强逼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以后的一系列侵华行径,导致中国民众的反日风暴迭起,从而促使国民革命展开。然而,日本侵华势力却日益猖獗,日本海军对于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都以增强在长江流域的武力来施压。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日本海军不仅仍在中国江海实行“巡航警备”,还在上海、汉口长期非法驻扎陆战队,以加强威慑和控制。后来,对于日本陆军先后在东北和华北策动“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日本海军分别以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和“八一三事变”来呼应;在日军对长江流域与东南沿海的大举进犯中,也积极充当了重要突击力量。在中国兴起国民革命之后,日本逆流而动,不断加重对中华民族的压迫,一步步走上了侵华战争之路。
作者李少军,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武汉4300793
原载于《历史研究》2014年第1期
注释从略,有需要者可发送电子邮件至编辑部索取全文及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