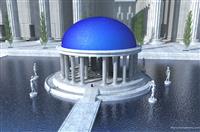汉斯•波塞 文;邓安庆 译
(汉斯•波塞,德国柏林工大哲学系教授,国际莱布尼茨学会主席,前任德国哲学协会主席)
1 导论
柏拉图在他早期涉及德性能力的对话《普罗泰戈拉篇》中,就已明白地讲述过,诸神曾委托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和厄皮米修斯[1]兄弟,把神赐的礼物分配给有生命的存在。厄皮米修斯领受此命,并公正地为所有的动物预备了坚蹄或利爪、毛皮或甲壳。可是,当动物最终进化成人时,原来的一切都白费了:人赤身裸体地来到世上,一无所有,既没有厚厚的皮毛,也没有鞋和武装。在此危难之际,普罗米修斯加进来了,在人就要看见世界之光的时刻临近之时,他知道自己没有别的妙计,只有把赫菲斯托斯[2]和雅典娜的技艺,还有火盗窃[给人类],因为如果没有火,技艺将一文不值。“这样,人才获得了幸存的手段”
就此看来,用阿尔诺德•格伦[3]的话说,人是一个有缺陷的生灵(Mängelwesen) :为了幸存下来,而又能够保持人的特点,人不可避免地需要雅典娜的科学和赫非斯托斯的技术。把使用工具、制造工具和利用火看作是向有理性的人(Homo sapiens)发展的决定性步骤,这不是偶然的,技术从一开始绝对就是人类生存(Dasein)的基本条件,与此基本条件相一致的,是世界的开放性和人的学习能力(Lernfahigkeit),但首先是针对自我设定的目标而行动的能力,以便按照自己的目的来塑造环境。有缺陷的生灵的这种结构直接给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以技术工艺改变我们的环境,究竟要达到什么目标和目的呢?因为我们本能上没有目标和目的,所以我们不得不确定它们。但是,在这里应该予以确定的是每种技术之外的最终目的,技术不是“目的本身”(Selbstzweck),而始终只是手段。手段是作为某种规则的技艺:“只要你想达到(产生出)A,你就必须做B。”技术基于知识和能力(Können),两者都是可教可学的。然而,更深的问题在于,如何涉及到目的本身。
在18和19世纪,这样的问题是令人奇怪的。目标就在于幸福的生活,而达此目标的手段就是千差万别、形态各异的技术,难道这不是清清楚楚的吗?科学和技术中的每一进步都使我们接近这一目标,难道不是不言而喻的吗?[但]对于我们来说,这样的乐观主义早已化为乌有了。雅典娜和赫非斯托斯所盗来的法宝,自身就显得矛盾重重,以致于今天追问技术所能承担的责任,完全是公众最为关切的问题。广岛(Hiroshima),博帕尔[4]和切尔诺贝利(Tschernobyl)都是因技术而对人类自身造成危害的密码:我们都是这个魔术的学徒,既不能等待也不能指望有个解魔大师(Hexenmeister)回家来。
追问技术的责任问题首先要求规定,技术是什么,然后才能与之相关地处理技术责任的向度。在此涉及的并不是经常被讨论的个别情况——臭氧空洞(Ozonloch),二氧化碳的排放,个人在媒体网络化世界中完全的可操纵性(Kontronierbarkeit),或者生命的遗传结构被侵犯[等问题]——而是要解决一些原则性的关系。
2 技术
正如前面的普罗米修斯神话告诉我们的那样,技术是人类生命延续和生活得以幸存(Überleben)的条件。柏拉图和荷马只涉及一种使人类在这个世界上自然生存的手段,然而今天的技术则渗透到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领域。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早已变成了第二自然(zur zweiten Natur)。下面我们要探讨的,就是在一切对象和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技术(因而不是探讨这个词的一种应用,即把钢琴演奏中的“指法技术”或者扒手的“调包技术”也包括在内) ,就作用方式而言,可以通过四种类型来描述处于发展进程中的技术:它的发展轨迹是从工具经过劳动机械(Arbeitsmaschine)和动力机械(Kraftmaschine)进到系统技术,在最后的第四步,即所谓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系统技术是通过思维机械(Denkmaschine)来操纵的。 这一发展的标志在于,不只是把有意识制造的东西与自然(作为已成的和前定的东西)相对照,而且取代了自然本身。比方说,当我们想保护自然时,在我们的幅度内所想到的,不是去保护一个我们既不想也不能生活于其中的原始森林,而是去保护源自19世纪初英国风景公园的审美理想的自然风景公园(Parklandschaft)。
因此,技术早就挤在我们和自然之间了。作为机械,技术也不只是我们身体器官的单纯增强或扩展,像锤子所起的作用那样;作为过程,当我们使水车产生出巨大的水力时,技术不是单纯地使用(lndienstnehmen)自然提供给我们的东西。[诚然]挖土机还能令人想起一只手,但当一个冰柜制冷或者一个CD播放器产生出鸟的鸣唱,就不能看出它是什么肢体的技术,它是基于一个在自然中找不到的东西。这种东西不只是与自然相异化的结果,它甚至连“自然的痕迹”都没有留下。相反,它导致的结果是,技术成为适用的手段,至于[技术本身的]关系,却只能为专家所理解,尽管在我们所有的工业化国家中我们仍然拥有从前任何一代都不一样的、有细微差别的自然科学的和技术的知识。
关于技术知识的类型,今天的技术与从前的所有技术都有决定性的区别。因为像一把斧头,一个锤子,一台织布机,一架水车或者一个塔楼钟,它们的功能作用,要细心地加以琢磨。技术中蕴含的合理性——雅典娜的知识——从前基本上对于每个人都是可理解的,而今天却具有被专家垄断的危险。要注意的是,这里涉及的是[技术]思想上的可理解性,而不牵涉技术行为本身。因为技术行为本身,反而是无须去理解的:技能,即技艺,如柏拉图所见,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有着天壤之别。也就是说,技艺是在[不同的]技术人员中体现出来的:“许多人共用一个医生就够了,这就像共用工匠一样”。使用一把斧头所要求的熟巧,超过了锤子,也超过了厨房里的电动机械,或者简直超过了现代的机械,因为现代机械的使用指令简单得只是按一下开关。
但是,成问题的就是技术的不可看透性,因为我虽然使用机械,但不再能够理解它,也不再能够顾及后果和附带后果(Nebenfolgen)来看待技术效用的实现,而是把所有这些问题都留给专家。技术系统的后果的涉及面越大,这个难题就越是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以至于演变成为军事上过剩的核潜能(Overkill-Potential)[的威胁问题]。核潜能的威胁问题也只是让人外在地笼统地看到,技术系统可能产生的具体危害是什么,正像人们所猜测的那样,它可能是由于氟里昂(Fluorkohlenwasserstoff)的释放所产生的危害,也可能是由于轻率地使用了白金(Platin)所产生的危害(因为白金不只是一种贵金属,而且是一种重金属)。对于核武器有可能造成人类毁灭的意识也具有某种技术的欣快症[5]的特征,它在战后重建的阶段就已经产生了,但后来在许多方面已转变为一种技术恐惧症(Technikphobie)。
从目的—手段—关系看待技术,也是不能让人满意的,这有一些更深层的原因。因为无论如何,技术的不可看透性,部分地也是这样产生的:一个技术产品,对于某些人来说,它的功用只是手段,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就会把它作为首要的目的。[所以]我们现在按照木刻术的一般进程,从工具经过机械到电脑控制系统,更准确地考察技术的目的-手段关系。
一个工具,如锤子或刀具,具有多种用途;每个工具都是[达到]不同的最高目的的手段。诚然,对于一把刀可用的目的是可以看得见的:从削土豆到杀人。
但对于一架机器来说,情况就不同了:它只是为一种特定的目的而建造的,它一旦生产出钉子时,明天把它用作螺旋就不适合了。因此转变——从军工企业转变为民用企业——是个动听的流行语,但常常只是同时表现出知识在技艺上的局限。不过,在高度网络化和专门化的系统这里,目的—手段—关系本身还是可以被改变的,也就是说,至少后果不会与原初设定的目标相一致。原子弹是美国人制造的,因为他们确信,德国人正在发展原子弹。为了摧毁纳粹(Nationalsozialismus)政权,他们必须抢在德国人之前造出原子弹。当原子弹造好了时,德国投降了。于是原子弹被投到日本领土之上,尽管人们知道,日本人并没有制造这种武器,否则也必定会抢在日本人之前。这个例子明确地告诉人们,技术的手段总是被用于其它的目的。
电脑控制技术系统及其在设备制造上的应用,又是另外的情况。电脑恰恰不是针对某个特定的目的,而是针对某些可能性的广阔领域,生产能灵活机动地适应一些新的目标。不过,表现出来的可能性,总是远远超出了硬件和软件的制造者及其工程师和程序编制员眼前所想到的一些可能性。因此,我们虽然是基于预定的目的而创造出技术手段,但在下一步我们就转变了这种关系,进而去寻找新的、出乎意料的、不可预测而又可被我们支配的手段所能达到的目的!
也许通过联系到需要,人们能够看透这种目的—手段—关系?由于从文化变迁上很难确定基本的需要,格伦试图从功能[需要]上规定技术。技术首先实现的那些功能是:
——肢体器官的增强和超越(锤子取代拳头)
——肢体器官负担的减轻(汽车代表双脚)
——肢体器官的取代(一把刀取代缺少的利爪)
在这里人们可以再辅助性地吸收其它动物的器官:我们像晴蜓一样飞翔,我们像蝙蝠一样凭着超声波(Ultraschall)而测定方位等等。但是在这种视野里,仍然失掉了关键性的东西,因为今天的技术远远超过了这些。比如,说CT扫描术(Computertomographie)是人或动物器官的延长,就没有一点意义,因为我们涉及到的是一些新的东西,甚至更常见的是,这些并不是履行器官的职能和任务,而是技术所履行的对社会文化需要的实现。无论是对于埃及的金字塔,古希腊的神庙,哥特式大教堂等建筑,还是对于高层社会地位的象征都是适用的。但是,社会文化需要的特征恰恰不是因此而得到刻画的,即,虽然它在其历史性和传统性(Traditionalität)中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它不能从基本需要(假如它们存在的话)的网络中推导出来。尽管如此,一种普遍的说法仍是可能的:当人们为发展和使用技术产品而操劳时,他们通过技术而盼望的东西,是期待赢利,这必定远远超过了对生产性中介(Produktionsumweg)的期盼。但期待赢利无论如何不能单纯从经济学上去理解:辛苦地承建一座神庙,就是这一生产性的中介,目的在于表达对诸神所怀的敬仰之情,或者说也是(如在 Agrigent)通过这个神庙的巨大规模而展示其真正的意义。在这里,技术的知识保障了一种安全的期待(Erwartungssicherheit),使之能够在以后稳当地兑现对这种辛劳的酬报,不管是肉体需要的满足,还是社会的赞美,还是对永恒福祉的希冀。这在黑猩猩那里就开始了,它们带着石块,长途跋涉,到达一个长满坚果但无石块的山谷,目的就在于能够打碎那里的坚果。被费劲地钻穿了孔的长柄石斧也是这种情况,其目的无非就是为了在砍伐应当作为燃料的树木时更省力一些。技术在这些方面涉及到每一个赚工资的从业工人的日常工作,对在若干年之后才能赚钱的高科技设备的计划和制造来说,也最适合。进一步说,它包含了如同大城市之间的高速磁悬浮列车(Transrapid)一样的象征性对象的赢利[6]。
在这里清楚地出现了我们今天的问题:预想中的安全期望,如何达到目的?因为如果这种安全期望没有了保障或者被不想看到的附带后果所损害,那么所有的目标都要泡汤了。
我们首先总结一下,鉴于责任问题,我们获得了什么样的立足点:人必然地要依赖技术而生活,放弃技术和回归自然(Retour a la nature)是荒唐的,甚至是不负责的;与之相反则恰恰产生出使用技术的责任感。至于在技术使用的过程中,哪些具体的生活必然是有问题的,哪些必然是令人满意的,这是不能确定的,因为它依赖于文化的条件。所以,技术的发展从工具经过机械到信息控制系统,
只有基于一种安全期望并鉴于满足一种文化需要的生产中介,才是可以说清楚的。
然而,安全期望成问题了,
——因为复杂系统中的知识,一般情况下虽然足以被应用但不足以被理解,所以要求教于专家;
——因为后果超出了预期,从而使生产中介失去意义;
——因为目的——手段——关系能被错误地置换,以致于一个手段被用于一些未曾预见的目标,从而也就同时导致不可预见的后果,并且
——因为技术的后果简直具有足以毁灭人类生活条件的危险,因此生产中介虽然对我显得是值得的,但对于后代而言,所有的安全期望都破灭了。
3 责任
开始我们只认识到普罗米修斯和厄皮米修斯神话的一半,另一半恰恰涉及到我们的问题,尽管在柏拉图那里,它还只是更为简单一些的形式:它同盗火和盗科学技术都无关,毋宁说它涉及的是这一问题:人尽管有他们的技术能力,但仍然很快陷入了恶劣的处境中,因为他们缺乏智慧(Sophia),聪明或科学,也即技术政策——在集体中有理性地共同生活的技术政策。但是,当宙斯(Zeus)看到,人性处于如此糟糕的境地,压根儿不懂得共同寻找保护时,这种技术政策就在宙斯那里存在了,因为人性缺乏事关德性(Tugend)和法权(Recht)的知识,于是,宙斯就让人们通过赫尔墨斯[7]而得到这些知识。不过,尽管所有的人都应该分享到德性和法权的神赐礼物,但技艺(Kuünste)的分配是不均的,因为毕竟尚无国家存在,所以,就像他们从前只得到不多的一些技艺一样,现在也只能得到很少的一份关于德性和法权的礼物。
柏拉图所看到的,是从知识和理性中产生出来的规则(Regeln),即伦理上公共的善的行为的规则。这些规则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既易于理解,又可学会的。苏格拉底不遗余力地加以探讨的道德行为,就是基于一种知识和洞见(Einsicht)之上,这些知识和洞见不是只可委派给专家的,而是直截了当地建构着民主。但正是从这里产生出责任行为的问题,它不包括鲁宾逊(Robinson)[的行为],相反它总是发生于集体之中,并且总是会影响、首先是能给予别人各种可能的自由的行为。
在现代技术的情况下,行为极端复杂,虽然也考虑到了它的诸种社会后果。所以,责任概念(Verantwontungsbegriff)将在极为不同的层面上发生作用。这些不同的层面可以作为价值层面(Wertebenen)用下图来解释:所有技术的第一个目的是通过技术手段来保障各种可能的生活得到改善,对于一种具体情况而言,这意味着一种技术的功能(Funktionsfähigkeit)。不过,这还不够,在价值的意义上,毋宁说应该把对于能量、工作、时间、物资、资本等等的资源需要的经济性(Wirtschaftlichkeit)减少到最低限度。然而按非经济的、社会目标定向的是:福利,健康,安全,环境质量和个性发展(Persönlichkeitsentfaltung),它们必定与相应的社会质量(Qualität)相连,以便在社会稳定的基础上有可能得到行动自由,使在可批评的和公开性基础上的社会正义(Gerechtigkeit)得以可能。关于技术和社会的综合关系,德国工程师协会(VDI)-指南3780-划了一个简图(它经过了新的解释),对它作出了最显目的说明:
个性发展/社会质量
福利(全体的经济性) 环境质量
经济性(具体的经济性) 健康
功能 安全
(技术行为中的诸价值)
这一切表明,鉴于技术,责任的困境,如所期待的那样,无非就是技术本身渗透到生活的所有领域所触及到的不同的责任类型。在这里,我们将只观察它们之中的伦理责任的类型。
“责任”作为伦理学的概念,是一个很新的概念,它本来是源自法律领域,指的是:某人对于一个法庭(Instanz)为了某事而要承担某些责任。然而较准确地看,它有多位的,至少有6位的关连:
这些在时间上本来是按行动的先后而出现的,然而,对于目前比较重要的类型来说,还是在先前的技术评价中得到应用的已成的和预防性的责任。进一步说,责任总是要考虑价值因素(规范、目的等等)或者代价而与行为的后果连在一起。在这里,行动包含耽搁Unterlassungen,也有不做的意思),只要什么都不做,当然一切都不成问题。不过,只要开始进行区别,诸困难就出现了:
(1)责任机关(Verantwortungsinstanz),人们是对责任机关承担自己的责任的,这个机关本来是法院(Gericht),在基督教兴起后,最后的机关是上帝。鉴于技术,责任机关不会是技术监督联合会(TÜV)或一个建筑监督部门(Baubehörde),同样也不大可能与世上的许多信仰团体那样,[认为]这个机关在于普遍地复兴(Restitution)基督教的上帝观念;相反,必须一同被思考的是这个世俗化过程(Säkularisierungsprozeß),无论是在认识论中还是在伦理学中,它都使人取代了上帝的地位而成为评判机关(Bezugsinstanz)。当然人们最终要对它承担责任的这个责任机关,既不可能是一个人,也不可能是一组人,而是作为总体的人类(Menschheit)。不过,这也需要补充,因为与柏拉图不同,我们是面对更为广泛的后果,同时也是对于所有后代而承担责任:因此,责任机关是所有目前的和未来的有理性生灵的整体! 。当然,这个整体只是作为理念(ldee)存在,而不是一个实在性(Realität)的存在,但我们仍然必须把它看作似乎真的是实在的一样。不同的是,鉴于未来的后果而仔细掂量一个生产中介完全是不可想象的。同时我们必须与柏拉图一起假定,对于每个有理性的存在,必定能够有洞见地去理解这种责任关系: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专家难题,但首先只要把对技术关系的基本理解介绍到一个开放的社会中,其次只要这个社会找到了一种可检验的方法,有意识地把履行责任机关的任务委托给一个专门委员会(Fachverständigengremium)--以所有有理性的存在的名义--那个专家难题就是可解决的。
(2)处于核心、要承担责任的东西,本来就是一种行为(Handlung),它必定间接地或直接地依赖于那些能够为行为承担责任的人。一项工艺(Technologie)尚不是一种行为—而它的发展、建立和使用就是行为了。由于今天所遇到的困局,几乎毫无例外地涉及大的社会课题,它必定使旧的、简单的、定位于个体行为的图式(Schema)得以扩大,一般地说,每次特定目的的转型(Transformation)—从起初境况到终极境况—都是要承担责任的。面对关于结果的讨论,不可解决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终极境况。这就导致要求,例如,只[承认]那些在可逆的变化中的状态才是可负责任的,以致于那些非意愿的行动后果能够再次被排除[在负责的范围之外]。诚然,从根本上说,没有哪个行动后果是可排除的。
(3)责任的主体,谁来为某事承担责任,同样是复杂的。因为这至少得涉及一个具体的行动者(Akteur)。在一台电子计算机所产生出的成就中,不仅使用者有份,而且还有程序员和硬件制造者的功劳;进而言之,当计算机元件(CIM)、计算机定向管理(CAM)和计算机目标设计(CAD)这些成果被投入生产,那么成为责任主体的人就更为广泛。在一个大的工程上,提供理念的人(ldeenprolieferanten),集体领导,合作者,赞助人,鉴定专家,决策委员会等等都是有份的。在特殊情况下,这也会导致没有谁肯负责任,因为总责任被参加者的数量除尽了,变得小到可忽略不计的程度;或者个人虽然也在一个专门委员会(Gremium)中一同参与了决定,但作为个体自然不会与此委员会完全一致。最常见的是,公开地让一个圈外的人物(例如一个政治家)象征性地为他既没有参与也不很清楚的行动负责,这就如同作自我检查,大家都说要为一切负责一样。在所有上述三种情况中,[对责任的主体]都存在特别的误解。在第一种情况中总责任是不容许被参加者的总人数除尽的;第二种情况依据的是个体伦理学(lndividualethik)内部关于个体责任的古典观念,即便如此,对于一个事件,必定也还存在责任问题。而第三种情况自然是基于原罪(Erbsüuende)思想的传播: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总是使我们自己负有罪责的。为了解决我们今天的问题,有必要[确立]一个完全改变了的模型以取代上述思想,这个模型就是一个共同责任(Mitverantwortung)模型,它将恰好按照每个人对于系统所能起到的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来分配他相应的责任。这种困难只在于,迄今为止,我们的整个伦理思想还不熟悉这样的概念,并且未把它纳入中心。为了能够使它发挥效用,不仅要在理论上使它有根有据,而且要把它纳入到与伦理责任问题的日常的实际讨论中。
(4)为什么而承担责任,这当然是为行动的后果。但这里无疑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问题。因为在那些预期的后果范围内,对其承担责任是没有问题的;而若遇到那些未曾预料到的后果又怎么办呢?在赔偿责任范围内将判危害人(Schädiger)对其行动后果负责,这同样也适用于伦理责任的概念吗?从结果看,如果结果虽然不是预想的,但还是可以预见到的,那么,这里的事情是清楚的,即这里存在着过失(Fahrlässigkeit)。不过,遇到可能要在未来才能出现的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后果(Tertiärfolgen)又怎么办呢?在这里,过去的信念伦理学(Gesinnungsethik)模型,如功利主义(Utilitarismus)和赔偿责任的模型,都失效了。道德责任作为责任的最普遍的形式,只能与人们知道的某种东西相关;不可预见的附带后果就与任何责任概念无关。只是——某事在何时是不可预见的?----在医疗手术中,人们只能仰赖医术状况(State of the art),因为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不能失去时间,因此只能依靠某种在眼前(Augenblick)能够预见或不能预见的东西。但是,在工艺中,情况不同,它非常强调要深化目前受到局限的知识,以便能够更好地评估后果。但是,在有[知识]局限的地方,这种情况下的基础研究(Grundlagenforschung)究竟会向前推进多远呢?原则上这是无法作出回答的。结果是,留下的风险责任——它总是可以妥善地得到估价的——不能由行为主体,而只能由整个集体来承担,只要这个集体总的说来是支持研究和发展的。然而,使技术保持现状(status quo)或者把它拉回到浪漫主义自然理解的基础上,都是不管用的,否则,面对艾兹病(AIDS),癌症和全球10多亿饥饿的人口,就是最大限度地不负责任。
(5)我们因之而承担责任的东西,首先当然是为行为后果,不过,这指的是所评估到的(Wertgesichtspunkten)行为后果。除此之外,还涉及到,一种行为后果或附带出现的后果是否实现了价值还是造成了代价。这样说的前提在于,我们对此已经具有伦理学上的评判标准(Maßstäbe)。联系到作为手段的技术,最终目标是包含一切后代在内的福祉(Wohlergehen)。然而,从内容上看,这个最终目标既不能使自身在文化上一成不变,也不能以一变应万变。例如,作为技术评估的德国工程师协会的指南3780,就有一个理顺各种价值观点的基本的平面图,它就是为了获得一个非常基本的评价标准指南。然而,拥有一个牢不可破的价值法典的时代——把这个法典看作是“摩西十戒”(Dekalog),看作是柏拉图意义上的最高的善的理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尽管如此,仍然不能以价值相对主义(Werterelativismus)为结果,因为正如一切科学陈述并非表达绝对的知识,而是表达当时的认识状况(不遵循这种知识或许也是愚蠢的)一样,
一个社会的价值和规范的状态也是历史形成的诸条件的组合,无视它们,意味着宣告退出所属的集体。所以,就此而言,不能排除诸价值的变化和价值转换(Wertzuschreibungen),但价值的变化和转换只能处于社会容许的条件之下。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不得不为达成意见一致找到批判性的协调(Abstimung)办法。因此,在这个技术行为极为盛行的时代为主导性的规范和价值进行争夺--在精神争辩的意义上--就用不着奇怪了。
4 行为的原则
在关于技术和责任关系的争论过程中,有许多不同的基本准则(Maximen)已被推荐出来:
不要去做所有结果不可逆转的(umkehrbar)的事情。
这种要求,极而言之,是决不可能达到的,因为任何历史事件都不可能是可逆的;当然它所指的不是这个意思,它指的是,我们不能造成不可偿还的债务(Belastungen):由于燃烧煤碳,煤气和石油所释放出的二氧化碳,使大气层一百万年以上才能复原,而地球也面临同样的历史命运,放射性的垃圾也能分裂成强烈的原子。因此,这个准则应该以调准一切工业发展的方向为结果,因为处于二难处境中的能源大约只能满足现时代世界人口能源需求的十分之一,而立足于此的反工业化(Deindustrialisierung)却又会使成百万甚至数十亿的人口不得不饿死。所以,当把这个要求极端地运用于当代时,促使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不可解决的价值冲突。就此而言,它不是一个近期目标,而只是一个可以替代的远期目标。
下面是一个弱化的准则:
一个可能是否定的结果比一个同样极有可能是肯定的结果具有更高的价值。
这个准则表达了一种安全策略(Sicherheitsstrategie),然而却不是伦理的原则。它对于风险评估(Risikoabschätzungen)简直具有重要作用,因为它使我们变得小心谨慎和三思而行(Umsicht)。而真正隐藏在背后的东西,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汉斯•约那斯[8]提议的对[康德式的]绝对命令(kategorische lmperativ)的重新解释中变得清晰可见:
要这样行动,使你行为的一切后果与地球上真正人类生命的持久性(Permanenz)相一致。
这与上文关于责任机关所表达的意思是一致的。这个准则达到了这种观念:被看作是“真正的”(echtes)人类生命的东西,是可以不依赖于历史和文化的变迁的,并且同样也不依赖于我们的生物进化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人在这个地球上只是一个过渡性现象。但是——人还是区别于动物的——人的本质是能承担责任的,他能有理性地策划(entwerfen)和实施他的行为,多亏了赫菲斯托斯的技艺,多亏了雅典娜的科学,多亏了宙斯给予他的理性的伦理洞见,使他能够反思他的行为,修正他的计划,扩展他的价值观念。人的理性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如同具有伦理的本性一样,它也具有科学-技术的本性。只有当我们如此不负责任,不再听从我们理性的召唤,我们才会丧失理性。在神话中,宙斯为了恐吓而给予人的惩罚,就是让无见识的人(Uneinsichtigen)去死,不过,在今天,它不再是惩罚个别无见识的人,而是惩罚我们所有的人。在讲述了这个神话之后,柏拉图紧接着借毕达戈拉斯(Protagoras)之口所说的话,现在越来越有效:如果每个人都分享了正义(Gerechtigkeit)和其余的公民品德,那么这说明,人不是天赋地,而必定是通过教育和学习而有了正义和其余的公民品德。这之所以可能,说明惩罚不是让一种恶行不发生或者对一种恶行进行报复,而是应该使受惩罚的人(Besraften)和其他的公民(Mitbürger)不去做非义(Unrecht)的事。对我们而言,可以做到的是,预先地阻止这类行为的发生,以便使地球上真正的人类生活得以延续下去。
--------------------------------------------------------------------------------
注释:
[1] Epimetheus,提坦伊阿佩托斯之子,普罗米修斯的兄弟,他的性格与普罗米修斯相反,既胆小又愚蠢,他不听普罗米修斯的劝告,收下了神祗送来的礼物,并同宙斯送来的潘多拉结了婚,结果给人类带来了灾难—译注。
[2] Hephaistos,火神和炼铁业的保护神,以善于制造的技艺出名。根据荷马的描写,赫菲斯托斯是宙斯和赫拉之子。而后期神话又说他没有父亲,因为赫垃忌妒宙斯独自生了雅典那,她也独自生了赫菲斯托斯。宙斯极不喜欢他,把他扔下了奥林波斯山,海神救了他,收养了他九年。这期间他为两位女神造了上千种精致的装饰物。为了报复母亲,他造了一把魔椅,使赫拉坐上去再也无法站起来。在造型艺术中,赫非斯托斯是个健壮的铁匠—译注。
[3] Arnold Gehlen-德国现代人类学家-译者
[4] Bhopal,印度中央邦首府,新兴的重工业城市,人口将近40万。曾因一家美国在当地的公司发生严重的毒气泄露导致许多人死亡-译者
[5] Euphorie,医学上的用语,指服用麻醉品后感受到的精神快感,或病人死前的回光返照-译注
[6] 高速磁悬浮列车是德国的一项高科技,但由于造价高昂,在德国没有人肯投资修这样的铁路,所以只能是“象征性”的赢利对象,作者在写此文时,尚不清楚,高速磁浮列车已在上海开始建造,使德国这项技术的赢利正在逐步变成现实--译者。
[7]Hermes在古希腊神话中,因他能够弹奏优美动听的竖琴,而化解了与阿波罗的矛盾,结成好友;又因他聪明伶俐而被宙斯看中,成为神与人之间的信使和宙斯本人的传令使。当代十分著名的释义学(Hermeneutik)就是因赫尔墨斯而得名。在这里,宙斯让他把道德和法律的知识传给人类-译者
[8] Hans Jonas,现代德裔美国伦理学家,以提出“责任伦理学”而著名-译者
原载《世界哲学》200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