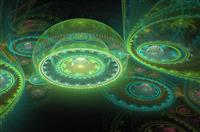一
从《论语》“樊迟请学稼……”这段记载可见,孔子词汇中,老圃老农亦属于“民,四方之民”。但当然,假如他们虽无自己的田地,却也不愿到别人田地上去做劳力,则他们可以到处流浪;然而没有自己的田地,又不愿去当劳力,则只有饿死。所以,绝大多数“四方之民”是必定要投奔拥有田地恒产的君子的,孔子对此有绝对的信心。
樊迟是孔子的弟子行列中的人,属于“君子”,他只是对“农,圃”发生了一点兴趣,也就被孔子指责为“小人哉”。可见,老圃老农一类“民”本身,就属于“小人”这个等级。孔子说,“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著名君子柳下惠之弟柳下跖属于“君子为乱”,而跟着他横行天下的从卒九千,则大体是“民,四方之民”,跟着为乱的君子去做了强盗。《水浒》里的事情,早就在庄子笔下写到过了。
孟子说,“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滕文公章句上》)。这句话里,“小人”似专指“劳力者”,与孔子语中的“小人”一词含义相同,老圃老农就是“劳力者”。而樊迟竟然要去学农学稼,身任“小人之事”,实属违背“天下之通义”,所以孔子鄙夷之。
孟子与万章对话,讲子思的事情,子思对缪公说,“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因为按“礼”是以皮冠招虞人,以旌招大夫,以旃招庶人,以旂招士,齐景公以旌招虞人,是“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子思说,“义,路也;礼,门也。唯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诗》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万章章句下》)孟子对于子思这番话,完全推崇,认为人应该遵照自己的等级行事,而君子要给“小人”做出榜样,小人要以遵礼的君子为楷模。
“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告子章句上》)由此可见,人之“大,小”,一方面虽然是他的社会等级决定的,另外,深入地说,也是由他的见识决定的,见识大的为大人,见识小的为小人,强调了认识能力、思想能力的区别。孟子这话,在一定范围内(比如相同等级的君子之间的比较),是有一定道理的,能解释一些现象,但由此扩展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逻辑,说是因为“劳力者”见识小,也就做不成“大人”,这就把社会等级的分化,归于“思”的得与不得与见识的大与小,而“劳力者”仿佛天然地和肯定地是缺少大见识的,所以劳力者只能“治于人”,这就排斥了劳力者往往从小就得不到作为人应有的文化教育这样的客观情况。对于这一点,公都子从自然人的平等角度提出了疑问,是了不起的。其实,劳力与劳心,并不能绝对地决定一个人能否识其大体,能否思而得之,在孟子之前二百三十年,《左传·庄公十年》载,鲁国的曹刿就说过“肉食者鄙,未能远谋”的话,并且用自己的实践(正确指挥了齐鲁两国之间的一场战争)证明了这一点。这些方面的情况和事实,孟子似都撇开了,因而他上述的大人小人之分的话至少是很片面的。
由孟子的话去理解孔子称樊迟为“小人哉”,从见识上说,樊迟不懂得“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见识上未能“立乎其大”,而且行动上还要去“从其小体”,所以是“小人哉”。既然这样没见识,以后的前途大体也就只能处在低级的“小丈夫”的地位上,“君子所履,小人所视”,只能成为较高地位的君子的追随者;再等而下之,就是为稼为圃,做个“治于人”的“劳力者”,为君子们供应物质需求。所以,君子里的“小人”,与“劳力者”的“农,圃”之类“小人”,除了所来的原有阶层不同之外,别的可能就没有绝对的界限,是可以混同的,像樊迟这样“小人”见识的人,谁知道他将来不会真的“堕落”去为农为圃呢?本来,一个原有君子的身分的人,却穷得,或像攀迟这样可能“自甘堕落”地,去出卖劳力,这情况想来也会是有的。
同样是君子身分,“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养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则为狼疾之人也。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告子章句上》),“大人”与“小人”的分化,自身修养有这样大与小的不同是原因。“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告子章句下》)这些终成“大人”的人,都是由低贱之处努力而上的,所以孟子强调君子要经得起锻炼和考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告子章句下》)。可见,低层的君子,或因某种原因而流入低层的君子,如果有机遇并得到诸侯赏识,仍可能建立功勋或上升到较高地位。最要不得的是像樊迟这样竟然自己任性,甘愿背离上升的路径而眼睛往低下的地方看,如不改正,以后只能混得很“狼疾”。本来好端端一个君子,而且是孔子的弟子,最后竟然去跟着老农老圃扛锄头,岂不是自甘堕落、很让人瞧不起?
从“以皮冠招虞人,以旌招大夫,以旃招庶人,以旂招士”的情况看,原则上说,这些人皆在君子之列。君子的修养有两个值得一提的榜样,一个是伯夷,一个是柳下惠,“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万章章句下》)可见,在“庶人”或“士,大夫”等等的君子中,各种德行都有,以至有可称为“顽夫,懦夫,鄙夫,薄夫”的,原则上都该称为“小人”。孟子注意到这一点,鼓励他们要向伯夷、柳下惠这些“大人”学习,伯夷是“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柳下惠是“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万章章句下》)。
虽然“庶人”之类在原则上仍算“君子”,但地位很低,习惯上一般不受重视,除非本人十分杰出并且得到有力举荐,这从《史记·司马穰苴列传》所记可以看出些具体消息。齐相晏婴推荐“田氏庶孽”穰苴领兵,而穰苴说,“臣素卑贱,君擢之闾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权轻,愿得君之宠臣,国之所尊,以监军,乃可。”后来给他派了一个这样的监军,这位监军不遵军纪,穰苴将其正法,这才树立了自己的威信。
二
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梁惠王章句上)
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是故圣贤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滕文公章句上》)
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离娄章句下》)
王者之民……民日迁善而不知者……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尽心章句上》)
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尽心章句下》)
国之财政必须“取于民有制”,不可以取得过多;国君如不与“民”同乐,只顾自己独乐,就不会有真正的快乐。归根到底,治理国家并不是依靠“善政”取民财,而是依靠“善教”得民心,意思是很好的。
为了弄清孟子语中的这个“民”字的确切所指,必须参考其语中涉及到的其他的人们或其他的说法。比如:
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离娄章句下》)
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梁惠王章句上》)
曾子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滕文公章句上》)
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离娄章句上》)
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离娄章句下》)
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谓庶人。庶人不传质为臣,不敢见于诸侯,礼也。(《万章章句下》)
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万章章句下》)
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百亩之粪(获),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万章章句下》)
从以上所引可知,庶人,仅次于下士,是最低一级的君子,亦可有“在官”的机会,如果在官了,就不用耕。“上农夫,上次农夫,中农夫,中次农夫,下农夫”这些等级,是按一夫百亩的标准获得田地的“庶人”,可统称为农夫或草莽之臣,由于他们在人力与经营等方面的原因,他们分化为上中下的不同等级,其中弄得好的能养九口之家,弄得最不好的,也能养五口之家,总之,生活就有了着落,国家的“取”也有了着落。至于那些完全靠在田野上劳力为生的人,当是另一回事,不在这样的叙述之中。
孔子在鲁国做过“大司寇行摄相事”,当有大夫以至卿的身分,他可以享禄多少?《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到了卫国,卫灵公问他,“居鲁得禄几何?”他说,“奉粟六万。”是举田地里的收获来回答的。于是卫灵公就按同等待遇给孔子,大约相当于后来汉朝的“二千石”这个级别的受禄,是较高的。设想,假如孔子作为“庶人”,只是做了一个“农夫”,按孟子的理想标准,那么能有田百亩,至多能养活九口之家,也仍是“小人也”,哪里能“奉粟六万”?
孟子所指民的恒产,按其理想中的标准说,就是一夫百亩的田地。既然有一夫百亩之说,这田地就是国家配给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分配给各级君子(拥有土地的使用权)。所以,民,不是劳力者,而是最低一级的君子,即庶人,庶人与民可以连起来称呼,比如,“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这句话里,庶民与君子是对举的,道理在于,庶民既是最低一级的君子,比起他们上面在官的各级有着“士”以上称呼的“大人”们,就要统称庶民。
“庶民”作为最低一级的“臣”,分为“市井之臣,草莽之臣”两种,他们都具有侯补的身分,随时可以“传”他们去见诸侯。“市井之臣”与“草莽之臣”的区分是其人在都邑还是在乡野。“国人”,就是指在都邑中的庶民,他们是城市里的最低一级的君子,最低的也就是人数最多的,他们的政治态度对于国君和国家的安全很重要。关于“国人”的不可轻视,如《左传·闵公二年》载:“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这是平日轻视国人的不良后果。正如《淮南子·说林训》所议论的:“君子之处民上,若以腐索御奔马;若履薄冰,蛟在其下;若入林而遇乳虎。”把某种紧张对立关系形容至尽。
“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这一句说明大夫的下一个级别是士,士的下一个级别是民,既然最靠近的下一个级别的人可以被无罪而杀死,则上一个级别的人就会有较紧迫的忧惧,就有理由见势不妙逃离而去。这是劝告诸侯国君爱其臣民、庶民、国人。总之,孟子语中的“民”,是最低一级的君子,在理论上是能得到一夫百亩的“恒产”的人们。
可见,“民”这个词,在孟子这里,或与孔子那里的含义有所不同。在孔子那里大体指直接在田地里劳作的劳力者,他们可能是绝无田产的,其实就是从各个等级上破产到底而在野外到处流浪的“氓”,往往举家而来(“襁负其子而至”)依附有田产者,身分低于自耕农。自耕农有自己的田地,因有独立的经济地位,而有自由之风,如《史记·孔子世家》以及《论语》中“耦而耕”的长沮、桀溺二人,批评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而“植杖芸田”的“丈人”大约都相当于孟子所说“草莽之臣”。《晏子春秋·景公饮酒不恤天灾致能歌者晏子谏》篇有“分家粟于氓……饥氓里有数家……民氓百姓……民饥饿穷约而无告……贫氓万七千家……”等语,这里“氓”当指无田产的劳力者,而“民氓”并称,“民”与“氓”仍是有区别的,“民”可能有点田产,但在饥荒年代生活也发生了困难。
三
孟子所言褐夫、匹夫匹妇、氓、野人,大体当指劳力者,他们多数是在田野上劳作,也有百工之人,比如,廪人、庖人、女、梓、匠、轮、舆。
关于“民”或“庶人”一般的田地情况,在当时兼并的天下,多的可能拥有较多,少的可能无立锥之地,正因为有很多连基本田产也失去的君子们,孟子才为天下设计出一种理想图景,来重新分配土地:
“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尽心章句上》)
种桑养蚕耕田劳作之人,并不是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的主人(即最基本的“庶民”),而是到他家这里来劳作并依附于他的“匹夫、匹妇”。一人耕种百亩是不可能的,因此,匹虽是单数(段玉裁:夫妇有别,谓之匹),这里的匹夫匹妇却是复数,泛指所有在这一户草莽之臣门下劳作的男女“野人”们。
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滕文公章句上》)
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万章章句上》)
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希。(《尽心章句上》)
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公孙丑章句上》)
许行自楚之滕,踵门而告文公曰,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朱子注:野人之称)。文公与之处。其徒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滕文公章句上》)
陈良之徒陈相与其弟辛,负耒耜而自宋之滕,曰,闻君行圣人之政……愿为圣人氓。(《滕文公章句上》)
辞尊居卑,辞富居贫,抱关击柝。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万章章句下》)
君之于氓也,固周之。曰,周之则受,赐之则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问其不敢何也?曰,抱关击柝者,皆有常职食于上。无常职而赐于上者,以为不恭也。……子思不悦,……曰,今而后知君之犬马畜伋!(《万章章句下》)
廪人继粟,庖人继肉(《万章章句下》)
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农夫也。(《滕文公章句上》)
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滕文公章句下》)
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滕文公章句下》)
从所引可知,劳力者们身着“褐衣”。理想中的井田制是“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这是给君子以“恒产”,让他们能够“以别野人”。野人不具有分配到井田的权利(滕,壤地褊小,更要将田地只在君子里分配)。所谓“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是说把那块公田管理好,完成给国家所应交的,是八家共同的头等大事。但这样理想的井田制当时不存在,当时情况是“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但孟子认为,只要正了经界,不准污吏之类的“慢其经界”,按井田制给君子们分配了土地,则“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孟子为天下君子设计将天下土地拿来平均地权,但野人没有享受这一“土改”的资格。
享有了井田制,也就承担了对国君的责任和义务,就是八家要共同完成那一块公田的公事,无田地的野人谈不上要承担这种责任和义务,他们只是从属于各个君子而已。
“野人”的另一称呼,是“氓”。
最低级别的吏,有“抱关击柝”,有“会计”,有“乘田”(管理田间事务),孔子身分最低时就做过“乘田”。孔子的嫡孙孔伋曾经沦落受到低于“抱关击柝”的对待,也就是把他当作“氓”一样。“氓”的地位与犬马无异,他愤而言曰,“犬马畜伋!”
《淮南子·修务训》中有一句“轻赋薄敛以宽民氓”,与《晏子春秋》一样“民氓”连称,应是指“民”以及隶属于他们的“氓”。
另外,那一社会还有工女、梓、匠、轮、舆、廪人、庖人等众(《淮南子·泰族训》:“茧之性为丝,然非得工女煮以热汤而抽其统纪,则不能成丝”。《淮南子·泰族训》:“屠割烹杀,剥狗烧豕,调平五味者,庖也。”)这些人的身分等级,或为“氓”,或为沦落的“庶民”。《左传·昭公三年》叔向说,“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那些原先的“大人君子”,经过若干代,其后人下降到皂隶的行列中,所以,《孟子》里的这些“廪人、庖人、梓、匠、轮、舆”之类,其中必有沦落的“君子”,可称“庶民”。《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史墨说,“三后之姓,于今为庶”(杜预注:三后,虞、夏、商)。君子中最低一级的庶人、庶民,其本人,其祖先都可能阔过的,现在是普通平民了。所谓“降在皂隶”,也还不是“氓、野人”,只是做着最低等的职务,或者是官奴(《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斐豹,隶也,著于丹书”。杜预注:犯罪没为官奴,以丹书其罪。又,《左传·昭公七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一般地,对地位很低的“庶人”是不必多“礼”的,《礼记》说“礼不下庶人”。《淮南子·人间训》中作为特异情况记了这么一句:“张毅好礼,……厮徒马圉,皆与抗礼”,这位有一定身分地位的君子是太注重“修其外”了,见到一般庶人,也礼以平等态度,这就是“多礼”或“作秀”。
庶民的衣着与“氓,野人”有区别,前已说到,“氓,野人”这些田地上的劳力者,一般是身着“褐衣”,可称为“褐夫”,而《淮南子·修务训》有“布衣徒步之人”、“布衣韦带之人”的描写,可见庶人身着布衣系一根牛皮带子以束身,这可能已属有些讲究了。现在也有人会炫耀名牌皮带,这可算是古风之遗存。我们估计,身着“褐衣”的“氓,野人”一类的人,必要时一定只在腰间随便系一根草绳藤条之类的就算了。“段干木布衣之士,……隐处穷巷”,有这样道德学问很高而足可称道的人物是沦落在穷巷庶人行列里了。所以,至少我们可认定,从《孟子》至《淮南子》,“庶人”指最普通最低层的“国人,民”,地位虽低,也许很穷,但仍属于“君子”阶层。颜回就是这样的一个弟子,孔子对他寄望甚大。
《孟子》里还说到了三种人:巨室,凡民,豪杰:
孟子曰,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离娄章句上》)
孟子曰,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尽心章句上》)
“巨室”之“巨”无非占拥有很多土地与民氓,至于如何能“巨”,在春秋战国以来到处兼并的天下,无非是利用强权圈地罢了,比如,鲁国的以季氏为首的三家,就是这样的“巨室”,孔子曾发起对他们的“堕三都”之战。晋国的情况是,先则形成“六将军”的势力,然后智伯灭了范氏与中行子,接着又联魏联韩而灭赵,但赵韩魏三家达成密盟,反灭了智伯,于是赵韩魏三家分晋。晋国的情况生动说明了“巨室”的兼并成长之路。在这种情况下讲“德”,也只能是相对而言,若恃绝对之“德”,则无异取消了自己的生存权。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记智伯故事之后大讲“德,才”的关系,不免流于空泛。
“巨室”来源当主要是旧日贵族之家,另外在基层当也会有强“民”以至狠“氓”发展而成的“豪杰之士”。
从孟子对“巨室”的认可,说明他很识时务,他称呼魏君、齐侯这些人为“王”,已经是违背了周礼而顺应了大势所趋,他这样肯定“巨室”,也是面对现实向这些新兴暴发户低了头。因此,他为天下所设计的理想中的“经界,井田”,其实必定是要把“巨室”占有的土地要排除在外的,而不可能是让天下庶民平分天下土地。至于氓、野人之类,当然更没有他们的分儿。所以,孟子设计的“土改政策”不但只是纸上的东西,而且也将是很不彻底的,如果付之实行,则还要加上大小“巨室、豪杰”们的干扰。《国语·晋语·史苏论献公伐骊戎胜而不吉》篇一针见血地说:
“吾观君夫人也,若为乱,其犹隶农也,虽获沃田而勤易之,将不克飨,为人而已。”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看国君的这位夫人如果谋乱,也不过是像“隶农”一样,虽然得以在肥沃的田地上劳作,所获却不可能属于他,他仍将是没饭吃的人,他永远只是在别人田地上为别人劳作而已。这句话竟以“隶农”作比喻,可见“隶农”的可悲的一般状况是世所公认的。
“隶农”一词,最准确,当即是“氓,野人”一类的隶属依附在君子田地上的农奴。从孔子语可知,他们也可能有妻室儿女,有时不免“襁负其子”到处流浪,寻求可以收容他们做“隶农”的人家,当然,战争的情况下,也可能成为被掳掠的劳力人口。
“巨室”的情况,我们可从《淮南子·人间训》一段对“大富”人家的描写中窥见一斑:
“虞氏,梁之大富人也,家充盈殷富,金钱无量,财货无赀,升高楼,临大路,设乐陈酒,积博其上。游侠相随而行。”
后来,这些“游侠”产生对虞氏不满,“悉率徒属,……攻虞氏,大灭其家”。这位虞氏是个土豪,虽富而并无多大权势,所以竟被这帮“游侠”享用并且灭了他的家。“游侠”大体该有“国人”的身分,他们的所谓“徒属”,只能是依附于他们的更为没落的“国人”与“野人”。
“巨室”,无论是从旧贵族中成长强大起来的,无论是从庶民地位上成长强大起来的,孟子都认可他们是“豪杰之士”了,其余的人们,就只能属于“凡民”。因此,孟子对于“巨室”与“豪杰”的认可,相对于他的“井田制”的梦想,是矛盾的,其道不行在当时其实就很明白。看来,孟子是当时一个半真诚半无奈的改良主义者,他的方法是:不触动兼并土地的残酷现实(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而参照古代“井田制”,对于其余土地实行某种“土改”,来安顿国中失去“恒产”的君子,认为这样可以实现“王道”。当时的齐王魏王都看出了他的“迂阔”,他的方法甚至不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但孟子的论辩性和他的“浩然之气”是很可观的。
附录:
关于旧贵族如何力求自己成长强大之一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载:虢公借口“听于神”而占有土地,所谓“神赐之土田”。
《左传·闵公二年》载:“公傅夺卜齮田,公不禁”。是说鲁闵公的师傅夺取占卜者“齮”这个人的田,鲁闵公不管。这是贵族内部以大欺小的土地兼并。
关于低职人员生动情况一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载:鲁庄公夫人孟任生子般以及子般妹,而所谓“圉人荦自墙外与之戏。子般怒,使鞭之。”后来这个受到鞭打而怀恨在心的圉人“荦”被利用为夺位斗争中的一个杀手。
《淮南子·人间训》里写西门豹治邺,“一鼓,民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再鼓,服辇载粟而至。……与民约信,非一日之积也。”此句中的“民”,当就是孟子笔下的有恒产的庶民、国人,从经济到战争,他们承担着对国家的责任和义务,他们拥有一定数量的“氓,野人”,战争时作为“徒属”随“民”出征。
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里写道,“武王以虎贲三千打败殷人,所说并非出征军队的全部,不过是其中的三千名贵族军官而已。”他指出,“苏秦第一个窥见了此中奥秘,他对赵王说,‘汤武之士不过三千,车不过三百乘,卒不过三万。’司马迁采用了此说,《史记·周本纪》写道,‘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其中‘甲士’二字应为‘卒’或者‘徒’。”
蓝永蔚所说这些情况,可用来理解《淮南子》中“一鼓,民被甲括矢”中的“民”字,他们在行伍中的身分就相当于“虎贲”、“甲士”,在他们的田地上劳作而隶属于他们的“野人”们,就是行伍中的“卒、徒”,最普通的战斗员。一般“士卒”连称,但“士”与“卒”是两个等级,“士”从“民”来,“卒”从“氓”来;“士民”连称,“士”与“民”是一回事,入伍则为“士”,在家则称“民”,是最低层的“庶人”,在“君子”的范围里。
“文侯曰,民春以力耕,夏以强耘,秋以收敛,冬间无事,又以伐林而积之,负轭而浮之河,是用民力不得休息也,民以蔽矣。”《淮南子·人间训》这句里的“民”,当也是指那些“与民约信”的“民”。为了一年四季的农业,“民”们固然也会有辛苦的一面,但真正从事“春以力耕,夏以强耘,秋以收敛”之类劳作的主要劳力,是他们身后的“氓”们,战争时就充当“卒、徒”。由此亦可见,《家语·王言解》里孔子要求的“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实在是办不到的事。
《淮南子·人间训》还写到,“孔子行游,马失,食农夫之稼。野人怒,取马而系之。使子贡往说之,毕辞而不能得也。……乃使马圉往说之,……野人大悦,解马而与之。”这个小故事里,“农夫之稼”里的“农夫”,是田地的主人,是“庶民”,他不在现场,而“野人”,是具体的劳作者,马圉是为孔子管马的人,他或者也具有“庶民”的身分,但贫穷得只能给人当马圉,他与田地上的“野人”的沟通,竟然比最善言语的子贡还强。“马圉”对“野人”说的话,反映了“野人”是田地上的具体劳作者:“子耕于东海,至于西海,吾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这句恭维话把其实寸土也没有的“野人”说得高兴了起来。
《淮南子》在《汜论训》中也提到“野人”:
“秦穆公出游而车败,右服失,野人得之,穆公追而及之岐山之阳,野人方屠而食之。穆公曰,‘夫食骏马之肉,而不还饮酒者,伤人。吾恐其伤汝等。’遍饮而去之。”
是说秦公丢失骏马,发现是被一些“野人”吃了,他不但没有拿“野人”问罪,而且给他们喝了美酒。这个故事里的“野人”,显然就是田野上的劳力者,这个身分概念的使用,亦与《孟子》一致。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载,晋逃亡公子重耳“乞食于野人,野人与之块,公子怒,欲鞭之。”重耳向“野人”乞食,“野人”给他一个土块,其时“野人”一定是无言的,意思是说,哪有吃的呀,只有吃土块吧。这样的“野人”,当就是在田间的劳力者。《孟子》、《淮南子》所言之“野人”,与此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