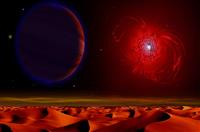
当下中国正处在一个大变革时代。中共新一届的领导人就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去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选择“全面深化改革”这个术语来描述其施政目标。不过,对于中国的执政者来说,如何妥善处理改革与秩序、现实与规范之间的紧张关系,依然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法律体系并不完善,加之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发展战略,所以人们对于改革的合法性问题并不是特别敏感。比如,虽然骆锦星(深圳房地产公司原总经理)认为他1988年竞得深圳市第一块土地使用权,“是触动《宪法》和《土地法》的大事啊,当时宪法对土地买卖是明文禁止的,买卖出租土地犯法,是要坐牢的”。但事实上,他并没有被关进大牢,反倒是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迅速修改了宪法和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参见刘伟: “土地拍卖‘第一槌’促成宪法修改”,载《深圳特区报》2010 年7月19 日,第A02 版)
深圳市1988年的这次土地使用权拍卖,确实推动了中国城市土地制度的改革,影响和改变了中国后来的城市化和社会发展进程,但其是以损害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性来推动改革的,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在这一先例的指引下,改革成了大写的真理,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性和对人们行为的规范性倒不那么重要了。今天许多中国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违法史,不突破现行宪法和法律就不能推动改革。这种认识就是建立在对类似改革经验的体验和总结基础之上的。
如果说在改革的初期,持有这种认识还情有可原,毕竟一切都处在重建阶段,不能要求太高。但当历史的车轮走进新世纪以后,再持有这种立场和观点就难以为继了。这不仅是因为我们的法律体系日益严密和完善,立法权限和规则已经基本确立(特别以2000年《立法法》的颁布为标志),违法改革会损害法律的权威性和法律秩序的统一性,更是因为违法改革会让民众、基层工作部门和司法系统无所适从。
那么,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当如何处理改革与秩序,现实与规范之间的关系呢?近年以来,中国的立法者探索出了一种新的法律发展模式,即对通过暂停实施部分法律条款的方法来支持那些具有探索性质的改革措施。比如,2012年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在广东省暂时调整部分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同意广东省暂停实施《海关法》、《城乡规划法》等25部法律的部分条款。2013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又授权国务院在上海自贸区内暂时停止实施《外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等3部法律。三年后,实践证明可行的,修改完善有关法律;实践证明不宜调整的,则恢复施行原有法律。
在去年年底的文章中,笔者曾高度赞扬这种新的法律发展思路,并提出,法治国家的建设应当以尊重法律权威为前提,不能将法律作为“制度稻草人”随意摆弄和丢弃。因为“法治”并不仅仅指惩奸除恶、维护公益,也不仅仅是要约束公权、保护人权,还要求我们在面对改革巨大红利时,保持镇定,小心翼翼,以合法的方式推行改革。(参见程雪阳:《深圳“农地入市”:违法的改革》,FT中文网,2013年12月31日)
立法法修正案(草案)的起草者们显然也持有相同的看法。从目前公布的和相关立法说明来看,立法者特别强调,要“按照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的要求”,“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并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根据改革发展需要作出决定,就特定事项在部分地方暂停适用法律的部分规定”(草案第5项)。这种将立法实践中发展出来的有益创举加以总结和提炼,是非常有必要的。可以预见,这种创举不仅有助于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法制度,而且有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所以,对于这一重大的立法体制调整和法律发展模式创新,笔者是热烈拥护的。
不过,笔者认为目前草案第5项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一立法体制的调整和法律发展模式的创新,主要是在“央地关系框架”内进行的,侧重于解决地方在改革过程中“先行先试”的合法性问题。然而,当下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所要面对的合法性难题,并不仅仅来自地方实验,还可能来自某些波及全国的特殊领域。
以目前正在开展的不动产统一登记改革为例。依照国务院办公厅2013年3月28日发布的《关于实施<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任务分工的通知》,“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会同法制办、税务总局等有关部门负责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并于2014年6月底出台《不动产统一登记条例》”。然而,依照《物权法》第6条关于“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的规定,物权的具体类型必须要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制定法律明确规定,任何人不得创设法律所不承认的新的物权类型。如此一来,《不动产统一登记条例》就不能要求不动产登记机关将草原使用权、养殖权、林地使用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等本质相同的权利统一登记为“农业用地使用权”,也不能要求将宅基地使用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统一登记为“建设用地使用权”,否则不但会违背《物权法》的上述规定,而且会违背《立法法》第79条关于“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的规定,并侵犯到宪法第62条和第67条赋予给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权力。
但这里的问题在于,如果《不动产统一登记条例》不对目前散乱在各个部门法中的相互独立、相互分割的不动产权利名称和权利体系进行“格式化”,那就无法实现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这一重大的改革目标。因为所谓“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不仅包括登记机构、登记信息平台和登记簿册的统一,还包括登记依据和不动产权利体系的统一。
那么,如何确保《不动产统一登记条例》在合宪合法的基础上实现上述目标呢?前一段有学者提出,要确保不动产登记条例顺利出台,首先要对阻碍统一登记的法律条文进行“立改废”。如果我们认真查阅相关法律的话,就会发现这种建议在实践中很难操作,因为这需要对《物权法》、《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草原法》、《森林法》、《海域使用管理法》、《渔业法》等法律进行一揽子修改和完善,工作量之大,没有数年的调研论证和立法讨论恐难以完成。
国土资源部和国务院法制办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不愿意大费周折地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上述诸多法律,因为这样一来,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不知道要拖到哪年哪月才能建立了。不过,他们也不愿意冒违宪违法的风险突破现行的不动产法律体系。在2014年8月15日公布的《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中,这部条例的起草者们试图将《物权法》、《土地管理法》、《森林法》和《草原法》规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国有农用地使用权”、“林地使用权”、“草原使用权”整合为“耕地、林地、草地等土地承包经营权”,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整合为“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管理法》和《渔业法》所规定的内地水域“水面、滩涂的养殖使用权”没有被提及,同属于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宅基地使用权”则继续被单列(《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第4条第4-6项)。
然而,这种做法仅仅是一种折中式的权宜之计。既不符合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建立的初衷,也不利于未来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的实施。其不过是将散乱的不动产权利体系作为“不良资产”留给了后人罢了。笔者曾经建议,相关立法起草者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申请暂停上述冲突法律条款的实施,为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的建立和相关条例的制定扫清法律障碍,他们似乎也不愿意接受。
当然,也不能将全部责任都推卸到国土部和国务院法制办的头上。从上文的分析来看,即便是目前公布的立法法修正案(草案),也并没有给他们提供请求暂停实施相关冲突法律条款的渠道,而且《不动产统一登记条例》目前所面临的困境不只是一个特例,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这种问题可能会接连不断发生。因此,立法者要未雨绸缪,要有顶层设计,要系统地看待相关问题,不宜就事论事式地修改立法法。
正是基于这种原因,笔者建议,立法法的修改不但要总结过往成功的经验,而且还要再向前迈一步,允许“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根据改革发展需要,就特定事项在全国或部分地方做出暂停适用特定法律部分规定的决定”,然后允许国务院或者地方人大及政府制定暂行条例来解决相关问题。事实上,在过去的30年多间,中国的立法工作在这个方面也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有许多带着“试行”字样的法律或者法规就是通过制定暂行法进行改革探索的例证。
另外,对于立法法修正案(草案)第5项规定的“就特定事项在部分地方暂停适用法律的部分规定”中的“法律”是否包括宪法呢?或者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能否根据改革发展需要,就特定事项在全国或部分地方做出暂停适用宪法部分规定的决定”呢?从草案以及相关立法说明来看,立法法修正案的起草者们似乎并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可能也超出了立法法修改所能承载的范围。
不过,依照笔者愚见,这个问题值得立法者认真考虑。毕竟中国大陆现行宪法(特别是总纲部分)有大量关于经济制度和社会事务的具体规定,而在这个大变革时代,我国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发展每天都有日新月异的变化。中国人经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哪些变化是值得支持的,哪些变化是需要反对的,需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但由于我们现在不得不要求“改革实践也要于法有据,不能违宪违法改革”,所以人们探索和实践的机会就会受到限制,检验真理的渠道也可能会变窄。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必要的时候也可以赋予全国人大及常委会暂停某些宪法条款实施的权力。
当然,对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在这个问题上的授权应当严格进行限制。比如,在范围上只能暂停总纲中涉及经济制度的条款,在事项上必须清晰明确,在期限上也应当以五年为限,在方式上,如果能采用宪法解释的方法化解相关矛盾,就不应当暂停相关宪法条款的实施。毕竟,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不应当轻易地暂停实施、修改或者废止。另外,全国人大或者其常委会还应当定期展开调研,并向国民报告相关宪法条款暂停实施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情况,从而未来中国的宪法发展提供实践经验。
笔者的这种建议并不是异想天开,其他法治发达国家已经早有先例。比如,加拿大1982年通过的《权利与自由宪章》第1条规定,立法机关可以在“明确的,且在自由民主的社会中可以被证明为正当”的前提下,通过制定法律合理限制宪章中所确认的权利。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还通过判例为“明确的,且在自由民主的社会中可以被证明为正当的合理限制”设立两个具体的标准:(1)如果国会或者省议会希望颁布一项限制宪章所保护的权利的法律,那么该法律的立法目的必须充分且必要;(2)通过法律限制公民权利的措施或者方式应当符合比例原则,且符合立法目的。这里所谓的“比例原则”包括三个方面:a对于立法目的而言,限制公民权利的措施必须谨慎设定且极为关联的;b限制措施必须尽可能减少对公民权利的损害;c限制公民权利的措施不得超过达成立法目的之必要性。
举加拿大的例子,并不是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全盘“加拿大化”,事实上,照搬照抄别国的经验,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笔者想强调的是,既然我们已经决意要进行全面深化改革,要推动“改革再出发”,而且我们已经探索出了一条新的法律发展道路,那么就应当将这种宝贵的经验加以总结和提升,并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和更大的理论勇气来看待宪法和法律的发展。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不辜负这个伟大的变革时代。
注释:
本文系作者在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暨莫干山会议30周年纪念会闭幕式上的主题报告修改版,文章发表于FT中文网2014年9月24日,原题为《让改革不违法的可能途径》。
程雪阳,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