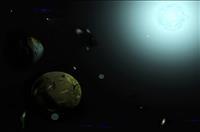在我看来, “唯物史观的当代解读”这一题目至少包含这样一层意思, 即重新阐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 以再现一个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
一
众所周知, 马克思恩格斯对他们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首次表述是在写于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如果从那时算起, 这一理论从问世到现在已有160多年时间了。那么时至今日,我们为什么还要提出重新阐释它的问题呢?
一个尽管实际存在、但却很少为我国学者明确指出的原因, 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给我们留下一个现成的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虽然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标志性成果之一, 但由于种种原因, 除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下简称《序言》)中对其做过集中然而非常简要的表述以外, 无论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没有做过专门的阐释。当然, 这不是说他们没有论述过历史唯物主义, 恰恰相反, 他们对它有大量的论述; 但这些论述大多散见于他们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问题的论著中。而且, 仔细研读一下这些论述不难发现, 它们有的只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粗线条的勾画而缺少细节的说明; 有的只涉及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概念和原理而没有涉及其他概念和原理; 有的只是将历史唯物主义应用于具体问题而没有对这一理论本身做出阐释。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包括《序言》在内的相关论述还存在两个明显的不足。一是缺少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明确而严格的定义, 例如, 关于经济基础概念马克思至少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1)“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 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第32页) ; (2)“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简言之, ‘社会的经济结构, 是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马克思, 第99页) 。二是缺少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精细而严密的论证。以“人类历史发展表现为不同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这一原理为例, 马克思在《序言》中将它表述为: “大体说来, 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第33页) 但他对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却没有做进一步的说明, 对为什么可以将它们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也没有做进一步的论证。此外, 他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 》中还提出过人类历史的发展表现为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三大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 第104页) , 这种表述与前一种表述是什么关系? 对此马克思也没有做进一步的说明。
另一个原因是我们对现有的国内外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感到不满意。我们知道, 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 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阐释历史唯物主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也取得了众多的成果, 如拉布里奥拉的《唯物史观论丛》、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考茨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梅林的《论历史唯物主义》、列宁的《卡尔·马克思》、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以及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德拉·沃尔佩的《卢梭和马克思》、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等等。此外, 前苏联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在阐释历史唯物主义方面也做了很多努力, 其成果主要体现在由他们编写的各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上。然而, 我们认为上述成果仍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当然, 对于存在哪些问题人们有种种不同的乃至截然相反的看法, 但有两个问题却是被大家所共同认可的, 一是这些成果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与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相关论述存在诸多不一致, 二是它们都没能再现一个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
正是上述两个原因, 使得我们今天仍有必要对历史唯物主义做出新的阐释。
二
重新阐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无疑应以他们本人的相关文本为依据。就这一点而言, 在当前我国哲学界存在三种错误的作法。
一是只以马克思的文本为依据, 而将恩格斯的文本排斥在外。采取这种作法的学者提出, 恩格斯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者而只是马克思思想的阐发者, 而且他“对马克思思想的‘阐发’是有偏差的, 甚至在某些重要的观点上错误地解释了马克思思想的本真含义”。(俞吾金, 2005年, 第453页) 我认为这一看法是不能成立的, 因为它与在这一问题上最有发言权的马克思的看法相悖。马克思在《序言》中曾明确指出: “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 发表以后, 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 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 当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 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 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第33 - 34页) 马克思这里讲的“他从另一条道路……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 指的是恩格斯独立地得出了和他一样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见解;“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 指的是他和恩格斯共同阐明他们的见解---历史唯物主义; 那个“心愿”的“实现”, 指的是他和恩格斯合作完成的对历史唯物主义做出首次表述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些难道还不足以表明恩格斯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者, 而且与马克思的见解是完全一致的吗? 这里还需强调指出, 恩格斯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者之一, 而且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要大大多于马克思, 因此, 将恩格斯的文本排斥在外将会使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缺少大量而可靠的依据。
二是只以马克思的早期文本、特别是《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为主要依据, 而将他成熟时期的文本排除在外。(参见段忠桥, 2006年) 这种作法是错误的, 因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在1845年最终形成的, 并且是在1845-1846年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阐明的。因此, 马克思的早期文本虽然有助于人们理解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形成过程, 但却不能作为再现这一理论本身的依据。实际上,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对他们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文本有过明确的说明。例如, 马克思在《序言》中就指出: “我们当时从这方面或那方面向公众表达我们见解的各种著作中,我只提出恩格斯与我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和我自己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 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第34页) 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一封信中也说过, 他在《反杜林论》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两部书里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就他所知是目前最为详细的阐述。(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第697 - 698页) 可见, 仅以马克思的早期文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在逻辑上讲不通, 而且还与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说明相矛盾。
三是仅以马克思和恩格斯1845年的文本, 即《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 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 为文本依据, 而无视此后的《序言》等文本的存在。(参见段忠桥, 2008年) 这种作法也是错误的, 因为《提纲》和《形态》只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刚刚进入成熟时期的文本, 它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表述还不十分成熟。就《提纲》而言, 恩格斯虽把它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第213页) , 但“萌芽”这一用语意指的是新出现的、还未成熟的见解。就《形态》而言,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在那里对他们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做了首次阐述, 但那些表述还只能说是初步的。对此, 恩格斯讲过这样的话: “这种阐述只是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 (同上, 第212页) 。而且, 马克思还明确表示过, 历史唯物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只是在他写于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中才“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在我看来, 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重要的文本依据应是《序言》, 因为马克思所说的“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即历史唯物主义, 只是在《序言》做过集中的表述。此外, 重释历史唯物主义还应依据马克思恩格斯那些直接涉及这一理论的文本, 如《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等。再有, 重释历史唯物主义还应依据马克思那些虽然没有直接论述这一理论, 但却是将其运用于对资本主义研究,因而对于理解这一理论具有重要意义的经济学著作和手稿, 它们包括《资本论》、《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 》、《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 》、《剩余价值学理论》、《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等等。简言之, 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在《提纲》和《形态》之后对历史唯物主义还有大量的更为成熟的论述, 因而, 仅以《提纲》和《形态》作为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文本依据是不充分的, 而无视包括《序言》在内的其他相关文本的存在则更是不合理的。
三
从某种意义上讲, 再现一个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 也就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文本进行逻辑和语言分析, 进而澄清历史唯物主义各基本概念的确切含义、各基本原理的内在逻辑以及这些原理间的相互关系的过程。我认为, 就实现这一目的而言, 当代分析哲学的一些使概念更加清晰、逻辑更加严谨的方法值得我们借鉴。关于如何将分析哲学的方法应用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文本分析, 我曾在一些论著中做过尝试。在这里, 我仅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的一段话的解读, 来展示一下分析哲学的语义分析法和语境分析法对于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积极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讲过这样一段话: “……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 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 实际地反对和改变现存的事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5页) 我国一些倡导实践唯物主义的学者由此推论, “尽管马克思在这里使用的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 而不是‘实践唯物主义’的术语, 但可以肯定的是, ‘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这一概念蕴含着对‘实践唯物主义’的认可。事实上, 没有‘实践的唯物主义’, 又何来践行这一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者’?” (俞吾金, 2007年, 第422 - 423页) 从表面上看, 这种推论似乎是有道理的, 但如果对那段话中出现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这一概念做一些语义分析和语境分析, 就会发现这种推论是不能成立的。
先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这一概念做一语义分析。从语法上看, 这一概念是由作为形容词的“实践的”和作为名词的“唯物主义者”构成的, 马克思恩格斯将“实践的”加上着重标示就表明了这一点。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结构, 让我们再来看看这一概念的德文表示和英文表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文原著《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实践的唯物主义”被表示为“denpraktischen Materialisten” (Karl Marx Friederich Engels: Werke, Band 3, S. 42) ;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英译本中, 这一概念被表示为“the practical materialist” (Karl Marx Friederich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ume 5, p. 38)。
可见, 无论在中文、德文还是英文中, “实践的” (德文的prak tischen和英文的practical) 都是作为形容词来修饰名词“唯物主义者” (德文的Materialisten和英文的materialist) 的。
如果“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这一概念的语法结构是这样, 那就不能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使用了这一概念就蕴含着对“实践唯物主义”的认可, 因为“实践的”是修饰“唯物主义者”, 而不是修饰“唯物主义”。
再从语境上分析。应当说, 构成“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这一概念组成部分的作为名词的“唯物主义者”的含义是清楚的, 即它指的是信奉唯物主义的人。那么构成这一概念组成部分的作为形容词的“实践的”含义是什么? 我认为, 既然马克思恩格斯在提出“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这一概念的那段话中没有对其中的“实践的”的含义做专门的说明, 那么对“实践的”的含义就只能在其出现的语境中去理解, 即在其出现的那段话中去理解。然而, 在那段话中我们只能看到“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这样的表述, 只能推断由于“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存在全同关系, 因而后者的含义对于理解前者具有重要意义, 却看不出“共产主义者”这一概念本身的含义是什么。这样一来, 要弄清“实践的唯物主义者”的含义, 就需要将语境扩大到《形态》的“费尔巴哈”章, 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那里对“共产主义者”有多处论述。以下是两段直接相关的论述:
(1)“费尔巴哈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全部推论无非是要证明: 人是互相需要的, 而且过去一直是互相需要的。他希望确立对这一事实的理解, 也就是说, 和其他的理论家一样, 只是希望确立对存在的事实的正确理解, 然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推翻这种存在的东西。”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第96 - 97页)
(2)“费尔巴哈在那里阐述道: 某物或某人的存在同时也就是某物或某人的本质; 一个动物或一个人的一定生存条件、生活方式和活动, 就是使这个动物或这个人的“本质”感到满意的东西。任何例外在这里都被肯定地看作是不幸的偶然事件, 是不能改变的反常现象。这样说来, 如果千百万无产者根本不满意他们的生活条件, 如果他们的‘存在’同他们的‘本质’完全不符合, 那么, 根据上述论点, 这是不可避免的不幸, 应当平心静气地忍受这种不幸。可是, 这千百万无产者或共产主义者所想的完全不一样, 而且这一点他们将在适当的时候, 在实践中, 即通过革命使自己的‘存在’同自己的‘本质’协调一致的时候予以证明。” (同上, 第97页)
如果在这两段话中出现的“共产主义者”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中的“共产主义者”是同一概念, 那么我们就可以做这样的推断: “实践的唯物主义者”指的就是“推翻这种存在的东西”的, 或“通过革命使自己的‘存在’同自己的‘本质’协调一致”的唯物主义者。由此可以进而推断, “实践的唯物主义者”中的“实践的”的含义, 指的就是投身于“推翻这种存在的东西”, 或“通过革命使自己的‘存在’同自己的‘本质’协调一致”, 简言之,投身于推翻现存事物的革命。这种理解可以而且恰好与“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出现于其中的那段话的其他内容相一致: “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 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现存的事物”。
以上分析表明, 那种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使用了“实践的唯物主义者”的概念就等于认可了“实践唯物主义”的看法, 是站不住脚的。可见, 如果我们能在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 借鉴一些分析哲学的使概念更加清晰、逻辑更加严谨的方法, 这对于再现一个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将会大有益处。
参考文献:
段忠桥, 2006年: 《对俞吾金教授“重新理解马克思”的三点质疑》, 载《学术月刊》第4期。2008年: 《什么是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历史唯物主义? ---与孙正聿教授商榷》, 载《哲学研究》第1期。
马克思, 1975年: 《资本论》第1卷, 人民出版社。
俞吾金, 2005年: 《重新理解马克思---对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和当代意义的反思》,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 《问题域的转换---对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的当代解读》, 人民出版社。
Karl Marx Friederich Engels Collected Works, 1976, London: Lawrence &Wishart.
Karl Marx Friederich Engels: Werke, 1959, Berlin: Dietz Verl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