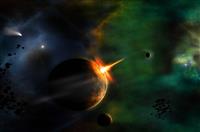读了刘学伟先生的《人民主权论的破绽及修补》给我的迷惑就是和读大多数主流学者的著作一样——到底是这位长期生活在国外的法国博士刘学伟先生对民主政治理论真的无知到还不如我这个中国普通的下岗人员,还是在故意地说假话瞎话。客观事实就是在这篇文章中的观点,可以说是漏洞百出、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请容我逐一地批判。
一、“人人生而平等”并不是指“绝对的平等”,仅仅是指人类社会规律性的结果,也就是指从不平等逐步地发展到相对平等的过程和目标。
刘学伟先生说:“美国独立宣言中那句著名的话:‘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段话的确有着永恒的美学价值,也可以说是一个崇高的理想。但它却不是一个社会科学的真理,更像是一个宗教信条。……理论除了解释现实,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提供一个理想,一个奋斗的方向。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还未实现的理想之符合真理的把握,远逊于从大量的现实中归纳出的规律。……但是有太多的崇高理想,尤其是宏大的理想经不起实践和时间的检验。……无论在中国、在其它发展中国家,还是在西方发达民主国家,我都可以轻而易举地举出海量的例子来证明,这个理想从未达到。我要从逻辑上证明它永远也达不到也真是很容易。”【1】
在这里,刘学伟先生认为“人人生而平等”只是一个美好的理想,却不是科学,更像是个宗教教条。其理由就是,无论在美国宪法建立时,还是几百年后的今天,美国以及发达国家,到处都存在着“不平等”的社会事实,而且“人人平等”在现实社会中永远也无法真正地实现!
说实在的,这话实在是对科学的无知,打个比方,我们难道能够因为现代医学不能够治愈不治之症,就可以否认现代医学的科学性?所谓“人人生而平等”,仅仅是指明了一个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以及不断地向这个目标靠近的发展过程。也就是我们必须承认“人人生而平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目标,而且还必须逐步努力地沿着这个目标从不平等不断地发展到相对的平等。而绝对不能因为“人类社会永远不可能实现绝对的平等”的客观事实为理由来否认“人人生而平等”的科学性、正确性和先进性。所以,在这里要么是刘学伟先生对现代宪政理论和“人人生而平等”概念的无知,要么就是在故意说瞎话。
其次,“人人生而平等”及其所必需的民主宪政制度,不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和目标,而且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目标。说起“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许多学者都不承认这个概念,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充满着偶然性的无序的过程。但我之所以承认人类社会具有客观发展规律,就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也就是实践的证明出发来论证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尽管在文化、教育、艺术、文学等方面实践的过程和结果是多元化、多方向、多目标地发展的,各民族和国家都产生了相对的差异。但在生产性经济发展领域,以及经济发展所依赖的科技发展领域,都是“一元化”的,同一方向、同一目标的。世界各国基本上都非常一致地经历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畜牧业→农业自然经济→工业化的萌芽时期手工业时期→工业化时代,并一直发展到现代的信息化时代。而且我们还可以在世界各国不同的多元文化中看到和不同经济发展时期一一对应的文化因子。如果我们不能否认世界各国在社会发展历史和人的实践上存在着这种“同一性”,那么我们就同样不能否认这种“同一性”就是体现了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所以,所谓“天赋人权”中的“天”,既不是指“神的赋予”,也不是指人为的“法定”,而是指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决定”。而且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从政治角度来分析这种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都非常一致地指向了同一的目标——“人人生而平等”及其所必需的民主宪政制度。(请看下面进一步论述)
我实在搞不明白的是,既然刘学伟先生明白人人生而平等的“人的权利的确是存在的,但它既不是上帝所赋予,也不是理念中的先定,并不与每一个人的生命俱来,也不与人类在地球上的诞生一起诞生,它其实是一种社会的权利,历史的权利,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而逐步完善丰富起来的权利。”【2】那怎么又会得出“不是一个社会科学的真理,更像是一个宗教信条。”的结论呢?既然明白“人权并非仅由法定”,怎么又会以此来否认“人权没有法定是万万不能的”的科学道理呢?这就好比“幸福并非仅有金钱能够决定”是不错的,但同样“没有金钱是不可能幸福的”也是不可否认的简单道理。这些自相矛盾的理论,充分说明了一个事实,真要说假话,是很难自圆其说的!
二、实现“人人生而平等”及其所必需的民主宪政制度的条件是“工业化的历史进程”,而不是“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
刘学伟先生说:“看看那些长期保持了政治稳定,经济高速发展的无论大中小国家,(主要集中在东亚,嘿嘿!)在它们的起飞阶段,在工商业和中产阶级成熟以前,可以说都是威权政体保证了政治的稳定和经济高速发展所必须的其它各项社会条件。而后,民主制度则可以在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条件下逐步建立起来。……民主必须建立在一个以中产阶级主导(即使他们还占不到人口的多数)的社会中。上层人数太少,他们永远不会企盼民主。当中产阶级已占到人口多数时(发达国家的现状),就可能推行正常的民主制度。当中产阶级占不到人口多数时,则只能寻找一种折中的民主制度。由宝塔型社会的庞大底座部分主导的民主,绝不可能正常运行。”【3】
在这里,刘学伟先生把“一个以中产阶级主导的社会”作为“人人生而平等”及其所必需的民主宪政制度的必要条件,并认为:“由宝塔型社会的庞大底座部分主导的民主,绝不可能正常运行。”这观点实在是没有击中要害,“人人生而平等”及其所必需的民主宪政制度的必要条件是“工业化市场经济”,而不仅仅是一个中产阶级阶层!是因为工业化市场经济的发展才产生了中产阶级,并进一步产生了“人人生而平等”及其所必需的民主宪政制度的历史需求,而不是先有中产阶级才会有“人人生而平等”及其所必需的民主宪政制度的条件。
这是因为工业化是以更精细的分工为前提;而分工又“必然”产生商品交换,于是市场经济就“必然”应运而生;市场经济中的这种商品交换又“必须”是自主、自愿和自由的,也就是只有“公平的交换”所规范和产生的“公平的竞争”,才是产生市场经济效益永不枯寂的源泉。所有“不公平的竞争”统统都是社会经济效益最可怕的“杀手”。于是,市场公平交换和公平竞争又“必需”民主的政府的“宏观调控”来辅助市场经济的机制,同样也唯一地只有民主的政府才是能够相对有效地保障公平竞争的制度原则,于是这种“公平竞争”的市场原则又“必然”地孕育和催生了民主政治制度。这就是我上文指出的“人人生而平等”及其所必需的民主宪政制度体现了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
其次,一个相对庞大的中产阶级阶层,确实能够促进“人人生而平等”及其所必需的民主宪政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但是并不是如刘学伟先生所说,只有等中产阶级阶层产生后,才能够启动民主化进程。这实在是在为维持集权制度寻找理由了。从全世界发达国家的民主化实践历史可以证明,只要进入工业化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就应该鼓励民众起来争取“人人生而平等”及其所必需的民主宪政制度,因为“人人生而平等”及其所必需的民主宪政制度是应该和中产阶级阶层形成、生产力的发展及市场经济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同步发展的,他们之间是一个相互依赖,相辅相成,互为因果,互为条件,互相制约,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过程。而绝对不是只能等到中产阶级阶层形成后才能够启动民众化进程。这实在是骗人的鬼话!
三、真正的“民心”的产生的前提,是民众具有“民心”的自由表达权和决定权。
刘学伟先生说:“赵汀阳指出,中国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不是民主问题而是民心问题。‘真正的民心是经过理性分析而产生的那些有利于人类普遍利益和幸福的共享观念。从形而上学来说,作为共享观念的民心并不存在于心理过程中,而是存在于非物质性的思想空间中,它承载着人类的思想、经验和历史,简单地说,民心的存在形式是思想性的而不是心理性的。因此,民心并不就是大众的欲望,而是出于公心而为公而思的思想。那些为公而思的观念并不专门属于哪些人,而是属于人类,尽管通常是由精英所思考并说出来,所其所思所虑却不是为了精英集团,而是为了人类共同的幸福。’(赵汀阳:《天下体系》,页29。)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民主观念?是因为中国思想指向了比民主更深入的民心问题。……‘民心才是关于制度合法性的证明,而民主根本就不是,民主只是一种在操作上比较容易的程序,并不能表达好的价值。可以说,民主问题是民心问题的歪曲表现。’(赵汀阳:《天下体系》,页28。)‘民主问题与民心问题的根本差异在于,民心是制度合法性的真正理由和根据,而民主只是企图反映民心的一个技术手段’。……我还想区分两种民心。就是事前的和事后的。事前,比如这事应当选谁来办,这事应当这样办还是那样办?这样的公共选择,尤其是在复杂紧急的事态下(比如南海撞机,或911之后),遵循当下的民意经常经不起事后实践时间的检验。我建议这样的决定应当更多地由专家、上级、总之是内行的人去决定。但事后的民心,就是事后的诸葛亮倒是可以相当放心地委托给民众。一个人任职数年以后,是否胜任,一件事照某方法办,数年之后,看效果如何。这个时候,公众和专家和上级之间的歧见就会小得多。”【4】
说实在的,我并没有读过赵汀阳先生的《天下体系》,所以对赵汀阳先生观点无法评论。但是对刘学位文章中的错误观点是必须批判的。在这里,刘学伟先生提出了一个非常滑稽和荒谬的理论,就是他认为原本属于民众心愿的“民心”,应该“由精英所思考并说出来”!还把“民心”分为“事前的和事后的”,并且还剥夺了民众对“比如这事应当选谁来办,这事应当这样办还是那样办?”的表达权和决定权,刘学伟先生“建议这样的决定应当更多地由专家、上级、总之是内行的人去决定。”
刘学伟先生实在是无知到有点愚昧了,无知到我实在不相信这是他的真话。众所周知,现代民主制度中的“代议制间接民主”,和希腊原始民主制度中“直接民主”的根本区别,就是强调和促进了精英治理的作用,精英只要通过普选获得任命,就具有对政策的决策和执行的自由行使权利,民众一般不予干涉。但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常识性问题就是,精英治理作用能够产生这种效果的前提,就是全民普选的存在和制约,缺了这一环,精英凭什么真心实意地为民众着想、为民众服务?从人的理性自私的本能和本性出发,缺了“全民普选”这个大前提,一切精英治理的有效性,将会全部丧失!中国的客观事实就是如此!为什么中国官员的腐败会比发达国家严重?绝对不是因为中国官员的素质比发达国家差,而就是缺了“全民普选”这个关键的监督、制约和纠错的环节!俗话说“好的制度使坏人不敢怀,坏的制度使好人也变坏”,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中的“代议制间接民主”,是精英和民众作用相结合的共同实施,不但强调和促进了“精英治理”的优势和作用,而且也保障了民众的监督、制约和纠错的本质性关键作用。我实在是不知道刘学伟先生要剥夺民众的监督、制约和纠错的权利这个大前到底提是因为无知,还是故意在说瞎话。但任何人,包括刘学伟先生想要剥夺民众的监督、制约和纠错的权利的司马昭之心,应该是路人皆知的。
所以,真正的“民心”的产生的前提,是民众具有“民心”的自由表达权和决定权。所谓“民心”的表达权,就是民众的思想、言论、新闻、出版自由,所谓决定权,就是民众的监督、制约和纠错的普选权。这二件中缺了哪一件,都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民心”!这是显而易见的常识!
在刘学伟先生的文章中充满着各种自相矛盾,既然他承认“我现在并不清楚如何是最好的寻得民心的途径。这个事情还要探索。”那么没有探索清楚之前,干吗说那么多的言之凿凿的理论观点呢?
四、美国的“金融危机”和欧洲的“国债危机”只是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发展进程中的小曲折和小插曲,不可能彻底地影响和扭转人类社会工业化市场经济发展进程的方向和目标,也不可能改变包括民主政治在内的“全球化”的进程和规律。
刘学伟先生说:“从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开始,
西方就走上了下坡路。只是开初一段还不太显眼,没有引起大家的警觉。到今天,这个下世的光景就已经相当的明显了。只不过西方人对其严峻性似乎依然没有足够的认识。他们实在很难相信,那500年的辉煌,就会在他们这一代人的手中结束。我也不敢确定这样的前景。”【5】
既然刘学伟先生自己“也不敢确定这样的前景”,那么把这种不确定的理论观点拿出来做什么?要招摇撞骗最起码应该有点自信的底气,要不然,谁会信呢?说发达国家会因为金融危机和国债危机就会毁灭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基础——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制度,这种笑话式的论调,又有几个人会相信呢?
2012年1月25日星期三
【1】、【2】、【3】、【4】、【5】:刘学伟《人民主权论的破绽及修补》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21652
附件:
刘学伟:人民主权理论的破绽与人心理论的初步探索
这篇文章和下一篇文章是为了回复应学俊先生与我商榷的文章《对话刘学伟:台湾大选、民主与欧债危机》。应先生的文章与我商榷的有两个核心问题,第一:人民主权的理论有没有重要破绽?第二:欧债危机与这个破绽有没有实质联系?这两个问题我都有过相当长时间的思考,说句实话已经都写过很多的文章。只不过,我以前探讨第二个问题时使用的核心词是公众贪欲。
由于是旧题目,我这篇文章的还是难免相当部分地抄以前的文字,不过我保证也有很多新的思考。
先来陈述一下我将使用的方法论。
据我观察,西方的政治哲学,真的是有两类,第一类我称之为亚里士多德式的,因为亚氏是这类理论的鼻祖,他的理论是从众多繁复纷纭的政治实践中概括出来的,有着无限的丰富性。这种理论特点在近世发扬光大。比如马克斯韦伯,熊彼特等人的现代民主理论我也觉得有这种特色,就是说,他们用的是归纳法,他们建立理论的基点是已有的政治实践,他们首先想的是从实践中概括出规律,然后试图修正现存制度的缺陷。从凯恩斯开始的新自由主义(主张国家积极干预)和从撒切尔里根开始的新保守主义(再回头,主张减少国家干预)都属于这一类。他们不再祈求自然法(天赋人权)作为其理论的基石。实在是现实已足够丰富,无须那些相当理想主义甚至多少天真的说法作为出发点了。现在好像又是一个调头的时机了。(又开始扩大国家干预了。)理论总结还没有出来,还要再观察。
另一类理论我称之为欧几里德式的。它们总是想先建立几条有数的公理,然后由此演绎出整套理论体系。类似这样的理论体系似乎更多,势力也很大。卢梭的《人民主权论》是这类理论的典型代表。美国独立宣言中有关人权的哪一段著名的话,和法国的《人权宣言》则是这类理论的最著名代表。我绝不想否认,这类理论的重大历史乃至现实意义,虽然我个人更倾向于归纳法,认为那种方法论更接近于科学。我还是愿意折中地认为,两种方法论的结合,应当是接近真理的更好途径。
除了归纳法,我崇尚的另一个基本方法论是研究任何一个复杂的事物乃至观念也一样,一定要把它看成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有起源、发展、兴盛然后衰落乃至灭亡的 过程。(比如世界的民主运动,还在走前半段。但我们至少应当看到它不是一个先于经验的真理,而是一个在实践中摸索创立的过程。)
我服膺的第三个方法论是:除了人要吃饭睡觉之类的简单真理外,任何稍微复杂的真理,都会需要条件。(今天下雨是不是好事,都要依具体情况而定。)如果动不动就要标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实在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从法国的年鉴学派,我还学到一个方法论,就是:研究历史,要看重那些在较长的时段(至少几十年)内发生的社会变迁(比如工业化,城市化,第三产业化,中产阶级的扩张),而不要过分看重政治舞台上绚丽的表演。这些表演如果表达了深层的社会变迁,则有重大历史意义,否则则无。
之前不久,我才意识到,其实我一直以来还有第五个方法论,就是中道、中庸。这个基本路线是我们的老祖宗留下。在西方也有遵循这条路线的老祖宗比如亚里士多德。无过无不及,不走任何一个极端。竭力从各种对立的意见中分别吸收其合理的成分而扬弃其极端的部分。综合综合再综合,折中折中再折中。这样我们就可以更接近真理。
概括起来,我的基本方法论有五条:第一、实践主义,主张用归纳法去寻找政治真理。第二、历史主义,主张研究问题看过程,看发展。第三、条件主义,相信任何复杂的真理的存在都有条件。第四、背景主义,主张通过对深层社会变迁的研究来理解政治变革的真正意义。第五、中庸主义。中道而行,不走任何极端。
以下便是我用上述五条方法论探讨政治理论的一个实例。我还将用类似的方法去探讨有关民主的其它话题。
人民主权,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在它之前,还有一个更基础的哲学或者伦理学的概念,叫做天赋人权。谈这个概念,追根溯源,都会回到美国独立宣言中那句著名的话:“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这段话的确有着永恒的美学价值,也可以说是一个崇高的理想。但它却不是一个社会科学的真理,更像是一个宗教信条。因为它并不是从社会实践中概括出来,相反与无数的实践相冲突。先别说造物主是否存在十分可疑,如果我们从事实出发,谁也无法否认,人人生而平等,只是一个美丽的理想。不言而喻的是无计其数的相反的事实:不同的人生在非洲还是亚洲还是欧洲,生在富裕还是小康还是贫穷家庭,生在治世还是乱世,其命运绝不平等。在美国人写下“人人生而平等”的华美字句时,该国南部还盛行奴隶制,占人口一半的妇女也被不言而喻地排除在“人人”行列之外,而新大陆的老主人印第安人也是被赶到贫瘠之地去享有他们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你知道吗,欧洲人进入美洲之前,那里生活着数以千万计的印第安人。在如今美国的贫瘠印第安人保留地中,只剩下20万人。
大家都知道,理论除了解释现实,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提供一个理想,一个奋斗的方向。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还未实现的理想之符合真理的把握,远逊于从大量的现实中归纳出的规律。比如价值规律,“看不见的手”,就已经经过足够的实践检验,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是有太多的崇高理想,尤其是宏大的理想经不起实践和时间的检验。
这种没有经起实践和时间的检验的最大的一个崇高理想就是共产主义。“处处温饱,人人均平”,这个理想不知激励了多少代,多少国度的造反者,去企图建立一个理想世界。但是就如同永动机一样,终究没有一个人,一批人真正获得成功。而且这个共产理想的最终失败仅在22年前,在我们这一代每一个人的眼皮底下发生。仅仅22年以来,人类才终于认识到:财产私有制,贫富差别,是不可能消灭而只可能限制的。这种对财产的私有与差别拥有,对人类整体利益的正面价值远在其副作用之上。
现在人类还存留着退而求其次的第二个崇高理想,就是政治权利的平等,一切的人都应该拥有完全等值的政治权利。清夜扪心,平心静气想一想,这个崇高理想,比起第一个,能多出多少的现实可行性?需要我去举例吗?不用了吧?无论在中国、在其它发展中国家,还是在西方发达民主国家,我都可以轻而易举地举出海量的例子来证明,这个理想从未达到。我要从逻辑上证明它永远也达不到也真是很容易。只要你承认,有身无分文的乞讨者和家财亿万的大亨合法存在,不可消灭,你如何去设想他们拥有平等的权利还是政治权利?是不是“他们都有权在桥洞下过夜”?还记得前些日子美国人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提出的口号吧?99%对抗1%。这还是在最发达最民主的美国。那99%和1%的人的真正的政治权利可能是天赋平等的吗?
那么人权不是天赋,可是法定?谁都知道,数十年来,人权已是普世价值。世界上可以说每一个国家的宪法中都有人权条款。就是说都有法定的人权。然而在超过半数的国家中,那些法定的人权,尤其是其中关于政治权利和牵涉到大量钱财的经济社会权利,并不能得到很好的实施。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纸上的权利要变成生活中的现实,期间道路十分漫长。也就是说,广泛的事实一再证明,人权并非仅由法定。
在我看来,人的权利的确是存在的,但它既不是上帝所赋予,也不是理念中的先定,并不与每一个人的生命俱来,也不与人类在地球上的诞生一起诞生,它其实是一种社会的权利,历史的权利,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而逐步完善丰富起来的权利。
为了把分析进一步的深入,我想把人的这些公认的权利简单地分解成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生存权。包括生命权和享有最低物质保障的权利甚至尊严这样的最基本的精神权利三个部分。这是难民和囚犯都应当享有的是最起码的人权。
第二部分:发展权。这中间首先包括经济上的发展其最基本内容是私有财产权,和为保证经济发展权所必须的拥有的其它权利,如受教育的权利,医疗保险的权利,休息和娱乐的权利,养老的权利等,还有宗教信仰自由等,似也应当放在此处。这是拥有了起码程度的发展的社会都应当拥有或应当首先争取的人权。
第三部分;政治权利。包括,政治言论出版的自由,集会结党的自由,直接选举国家领导人和国会议员的权利等。这是一个已经拥有了中等以上发展程度的社会的民众才可能有效地拥有的人权。
正如任何复杂的事物,都是从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逐步发展而来,人的权利也不会例外。
在人类社会的初始阶段,部族时代,一个部族要生存下去,就是最高的人权。战俘会被杀来吃掉,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也难逃类似的命运,到了大灾之时,会发生易子而食,小人的人权也不得不被牺牲。就是到了现代社会,在一些极端情势下,比如说因难船长期漂流,也会发生人吃人的情形。我这里要说明的是,从发生学上来说,生存权,尤其是集体生存权,是最初的人权。对于任何社会时代,生存权也是高于其它任何人权的最基本的人权。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有了家庭、私有制和各种不同规模不同组织程度的国家出现。第二部分的人权就是发展权才开始出现并发展。这其中最根本的权利就是私有财产权。关于这个私人财产权的人类社会基石的地位,是直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结束的最近这20年才成为人类公认的普世价值。其它的社会权利也是近数十年来来才成为普世价值,在发展中国家努力追求,在不发达国家中无法具备的人权。就是说除了私有财产权之外,在《联合国人权宣言》中列举的一长串经济和社会权利明显的不是天赋人权,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物质富裕,逐步才可能付诸实施的“人赋人权”。在这里,光有善良的愿望是远远不够的。当然当物质条件基本具备时,人民也是要经过争取,才能获得这些权利。这时,有理念的指导,就有重大意义了。当然也不能走得太远,像西方今天一样,上去以后,退不下了,也是很麻烦的。
在人类发展的第三阶段,出现了城市、工商业和中产阶级。在这个基础上,经过古希腊、古罗马、文艺复兴(中国人惯用的这个词很不精确,欧洲人用的只是复兴restoration,是指复兴古希腊罗马的一切尤其是工商业,而不止是文艺)以来的欧洲城邦,和英国大宪章运动以来在欧美数百年的复杂实践,无数的成败利钝,才有了这第三部分的人权和现代西方的民主政治。这当然是人类最宝贵的精神成就之一。西方国家的错误就在于,想把这个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成长起来,并只能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正常运转的政治制度,强行扩充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与无论何样的社会条件无关的唯一的绝对的政治真理,并不惜试图用武力把它强制推行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上一段黑体字的结论已是几年以前写的了。根据新的社会实践,这个制度在发达的西方的运行也遇到了严峻的瓶颈,其是否真的可持续,都还要打问号。西方人还有道义高度把它向全世界强制推行吗?)
下面我们来简单看看正反两方面的例子。由于人权民主理念的广泛传播,现在世界上的可以说每一个国家,都有一部写上民权条款的宪法,都有一个议会,都在搞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选举。但更进一步看,在那些不发达的国家,就是说没有足够的工商业和中产阶级存在的国家,你有看见成功正常长期运转的民主制度吗?反过来,看看那些长期保持了政治稳定,经济高速发展的无论大中小国家,(主要集中在东亚,嘿嘿!)在它们的起飞阶段,在工商业和中产阶级成熟以前,可以说都是威权政体保证了政治的稳定和经济高速发展所必须的其它各项社会条件。
而后,民主制度则可以在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条件下逐步建立起来。这就是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对人类政治发展的最大贡献。
关于民主,我的基本观点一直是:民主必须建立在一个以中产阶级主导(即使他们还占不到人口的多数)的社会中。上层人数太少,他们永远不会企盼民主。当中产阶级已占到人口多数时(发达国家的现状),就可能推行正常的民主制度。当中产阶级占不到人口多数时,则只能寻找一种折中的民主制度。由宝塔型社会的庞大底座部分主导的民主,绝不可能正常运行。
我的关于社会治理的理论核心,现在又有新的发展。我正在开始试图用中道良治来取代加权民主,作为我打算举起的理论旗帜。用良治水平来评价治理的成功程度,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比起只看民主水平科学太多。因为有太多的发展中国家,拥有普选多党轮替的西式政治制度,却并不拥有良治。这样的国家可以民主了200年(比如海地),却依然贫穷落后。而拥有良治的国家(比如中国和民主转型以前的南韩、台湾),哪怕同时并不拥有够多的民主,最多30-50年,就可以成长为一个发达国家。这个时候,民主就不再是一件奢侈品,而是一件日常用品。因为我们可以声称,每一个富裕发达的国家,都拥有良治。尤其是,我们很可能有机会创立出一种新版的更周全的民主。
在这里,我又想介绍几句赵汀阳先生的民心理论。
赵汀阳指出,中国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不是民主问题而是民心问题。“真正的民心是经过理性分析而产生的那些有利于人类普遍利益和幸福的共享观念。从形而上学来说,作为共享观念的民心并不存在于心理过程中,而是存在于非物质性的思想空间中,它承载着人类的思想、经验和历史,简单地说,民心的存在形式是思想性的而不是心理性的。因此,民心并不就是大众的欲望,而是出于公心而为公而思的思想。那些为公而思的观念并不专门属于哪些人,而是属于人类,尽管通常是由精英所思考并说出来,所其所思所虑却不是为了精英集团,而是为了人类共同的幸福。”(赵汀阳:《天下体系》,页29。)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民主观念?是因为中国思想指向了比民主更深入的民心问题。
我们今天已经感觉到了,许多领导人虽然是根据民主制度选举出来的,但是他们并不得民心,因为从根本上并不具有合法性。民主制度本身无法证明自己的合法性。“民心才是关于制度合法性的证明,而民主根本就不是,民主只是一种在操作上比较容易的程序,并不能表达好的价值。可以说,民主问题是民心问题的歪曲表现。”(赵汀阳:《天下体系》,页28。)“民主问题与民心问题的根本差异在于,民心是制度合法性的真正理由和根据,而民主只是企图反映民心的一个技术手段”。(赵汀阳:《天下体系》,页28。)
就在今天,我还与赵汀阳先生交流过关于民心的思考。他回的电邮中说:“关于民心,我一直在想,但其中有些复杂问题还没有想清楚,现代建立了个人主体性,subjectivity,人的意愿就变成了价值标准,想想看,这样条件下的民心就很难满足了。古代的民心是有限欲望组成的,而且欲望高度一致,基本上可以表达为生存安全、基本物质需要、繁衍、天伦之乐等等,就是说,古代民心可以从人的needs就可得知,现代民心却是由wants构成的,欲求无限而且多样。我一直疑心,现代人虽然有了启蒙,却更加不理性了。”
西方的民主,是通过普选投票的方式去寻找民心。这个方式其实有很多的漏洞,所费不赀,而且十分容易被政客们操纵,让他们去谋取私利。我现在并不清楚如何是最好的寻得民心的途径。这个事情还要探索。
我也想对民心理论加以补充。比如说,我认为,人民心中所想的得到的东西,(比如永远是更多的福利,更少的工作时间。)其实并不一定符合他们自己真正的整体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打个夸张一点的比方。一个市镇举办一所小学。这里涉事的有三方:学童们的家长、学童和校方。学童们的利益应当是这个学习机构的最高利益。但校方或者说教师一方也有不可漠视的利益,但这显然不是最高利益。这个第三方孩童们的家长的价值就在于学童们还年幼,不够明事理,还不能自行全权理智地处理自己的利益。以前的人民主权或公仆理论,只承认两方存在。同时认定校方的利益必须绝对服从于孩童的利益,甚至漠视教学方的利益,完全简化了校方创造性劳动的价值,甚至提出关进笼子那样非人道的比喻,因此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执行。我之所以提出家长这个第三方,是因为看到公民的集体的处事风格的确有些像未成年的孩童,只要他们真的有权利做主,就会太多地自动地偏向于要利益要享受而不肯承担足够的相应的责任。问题是谁可以但当人民的家长?想来想去,只有求助于中产阶级和知识精英,或者如宋鲁郑建议的,年长者。他们当然也有私心私利。但相对而言应当比权方更少。尤其是他们一定比普罗大众,不分贤愚的公众(在这个比喻中—相当于学童)更理智。
我还想区分两种民心。就是事前的和事后的。事前,比如这事应当选谁来办,这事应当这样办还是那样办?这样的公共选择,尤其是在复杂紧急的事态下(比如南海撞机,或911之后),遵循当下的民意经常经不起事后实践时间的检验。我建议这样的决定应当更多地由专家、上级、总之是内行的人去决定。但事后的民心,就是事后的诸葛亮倒是可以相当放心地委托给民众。一个人任职数年以后,是否胜任,一件事照某方法办,数年之后,看效果如何。这个时候,公众和专家和上级之间的歧见就会小得多。马迎春老先生的普评制似乎就是这个意思。这一点我想我与大家都没有歧见,就是全体人民的整体长远利益,应是每一个正当的政体的最终最高追求。
概言之,事前的民心其实经常是短视的。我把这一点称作平均智商。普选表达的就是这种平均智商,而且是经过政客精英们如簧巧舌百般拨弄拉拢之后的平均智商。人民、国家或者人类的整体和长远利益,经常都不能被直接的民心所表达。这个整体长远利益,我把它称作是良治或长治久安,甚至三个代表。我觉得最能够体会到这个整体长远利益的应当是一些精英的知识分子。但是怎样把他们准确无误地选拔出来,又是一个难题。当然对他们也应当有足够的监督,不能让他们走到过分图谋私利的邪路上去。让他们大公无私也是妄想。我的核心观念就是为了达到长治久安,为了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避免民粹主义,应当修改天赋人权成人赋人权,把权利与发展,与义务(赵汀阳的说法,叫人义)联系起来。同样应当修改人民主权,让底层民众的急功近利,短视贪婪受到限制。最低限度,不要搞大规模普选,不要让政府和政府的领袖受公众贪欲太大的直接压力,才可能制定出能够导致长治久安的政策。民心的满足在事后可能比较公允。那就是公道自在人心。就是史有定评。或者说国人皆曰可杀(比如对四人帮)。在事前那就大不一定。或者说,国家的前途,人类的命运,这样的天大责任,只有摩西、华盛顿、杰弗逊、罗斯福、戴高乐、邓小平那样的伟人才能但当。这不是普选所表达的平均智商所能达到的水准。大道要靠伟人、精英和普罗大众一起来追寻。在这里,千万不要跟我讲一人一票。伟人的一票,可能顶凡人的一亿票。只有他们才可能力挽狂澜。当然他们也可能犯天大的错误,比如毛泽东。穿透当下的迷雾,看到真正的未来,那的确需要不世的天才。比如中国的政治现代化的道路,将来真的会怎样走,谁知道?又比如中国正在崛起,我们真的需要独创的意识形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但是我们今天的孔夫子在哪里?十分可惜的是,这样的伟人并不世出,就是说不是每一个时代都能碰上。比如今天的中国就显然没有。(我的这些关于民心的思考刚开始发展,还很不成熟。请大家批评。)
当然人民不可以被愚弄。人民必须有自由。毛泽东那样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全面专制是绝不能允许重演的。
关于当下中国的公众,即使是我说的中产阶级,如何从现在太盛的官权手上争取权利。我也有过好些设想。简单说起来就是落实选举法规定的间接选举,强化政协,重建阶级共和,由上而下扩大党内民主,由上而下扩大各种社会团体内的民主……已经说过很多。现在好像得等新一届领导班子习李上台之后才可能真正动起来。
我还有一个基本看法就是,只要发展在继续,崛起在继续,政治改革的背景条件就会越来越好。不怕现在还穷,只要在迅速地富起来,一切都好说。像在今天的中国。不怕现在还富,只要是在穷下去,一切都不好说。像在今天的西方。
我们现在简单回顾一下历史。整个世界,自古以来,除了希腊一脉,从来没有过人民主权一说,甚至没有拥有主权的公民一说。就是希腊一脉,也只是在古希腊城邦中,在罗马共和国中,在中世纪后期的一部分自治城市中,有公民和公民的政治权利存在。自近代英国的大宪章以来,才慢慢开始了贵族与国王的分权,资产阶级与贵族的分权。直到二战以前,西方先进国家中,还基本上都实行的是加权民主。少量的普选实践,负面教训多多。(比如法国普选出两个拿破仑皇帝,德国普选出希特勒。)真正的普选,仅在二战以后。在美国是1960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以后,才落到实处。说去说来,西方人能高举起这面普选的旗帜,其实只有50年。西方文明的绝世风华,其实也就展现在1945-1975这仅有的光荣的三十年中。请注意这30年和50年,中间只有十来年的重叠。从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开始,西方就走上了下坡路。只是开初一段还不太显眼,没有引起大家的警觉。到今天,这个下世的光景就已经相当的明显了。只不过西方人对其严峻性似乎依然没有足够的认识。他们实在很难相信,那500年的辉煌,就会在他们这一代人的手中结束。我也不敢确定这样的前景。前路还是有两条的。或者他们能脱困。那就会有一个二元的世界。或者他们终于不能脱困,制度崩溃。那一切都得另立章程。这些前景稍嫌遥远。等那种前景更清晰以后再说吧。
其实,西方人对人民主权理论的这个根本性漏洞早有警觉。以下两段留言,在每一次选举时,都在美国人的短信和电邮中反复流传。请大家参看。
“民主总是暂时性的,它根本无法成为一种永恒的政府形式。一旦选民发现,他们可以通过选票大把掏国库的钱,民主就无以为继。而从那一刻起,多数选民总会投选那些承诺要动用公款给他们带来最多好处的候选人。结果是,民主将因政府财政政策的松懈而垮掉,取而代之的往往就是独裁统治。”
“有史以来,世界上伟大的文明一般持续约200年。在这200年期间,有关国家都会经历以下的发展阶段:从(思想)受束缚到有精神信仰;从有信仰到有勇气;从有勇气到有自由;从有自由到富裕;从富裕到自满;从自满到散漫;从散漫到依赖;从依赖又重回受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