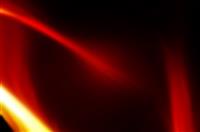一段时期以来,社会上提倡“读经”的论调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读经”行为总时不时“冒头”,这些行为、做派往往打着恢复国学经典、继承传统文化、挽救世道人心的旗号,貌似极有文化,极其严肃,极其尊重经典,结果也似乎总能引起社会舆论的一些“叫好之声”;但装腔作势、哗众取宠的作秀色彩以及骨子里的肤浅与虚妄毕竟还是掩饰不了的。近日在《书屋》(2015年第三期)上读得一篇倡导“读经”的奇文——署名刘强的《文教当继,经典可传——再论经典教育》(以下简称“刘文”),有些惊讶,因为《书屋》毕竟在国内也算是有些影响的纯学术性刊物,可竟然也乐衷于赶这趟哗众取宠的“混水”?考虑到这类文章在纯学术性刊物上出现,恐怕也具有一定的学术“感召力”,至少在编辑心目中,这应该是他喜欢的一碟“菜”。由此可见,编辑对于其中的学术泡沫甚或欺骗性特点或许已经有些麻木不仁了。对于一家学术性刊物来说,编辑有这种感觉实在不是什么好事。有鉴于此,写作此文,就不会是毫无意义的吧!
一、
“刘文”一开篇就对当年(即1912年----笔者注)中华民国教育部废止“小学读经科”的决策和做法颇为不满,继而就将批评矛头直指当年“废经运动”的主将蔡元培、胡适和鲁迅。“刘文”首先批评当时的教育总长蔡元培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为废除读经辩护及张目”;继而指责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以一种十分武断的‘进化论’思维,宣布了‘旧文学’的‘死亡’”,而1920年的“小学语文课全面改用白话文”则意味着“从此,中国的教育体系中没有了经典教育”,而中华民族则“成了抛弃自己经典的民族”了;紧接着对于鲁迅当年竟然以一种“乖张偏执的议论”,在青年中倡导“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的做法,“刘文”也显得极为不屑。
对于当年的这场意义极为深远重大的“废经运动”,“刘文”的最后论断是,“蔡、鲁、胡这几位饱读经典的文化精英”,“利用自己的职权和影响力,以改造国民性、救生民于水火的凛然大义,剥夺了孩子们学习经典的权利,也割断了经典教育的千年学统与文化命脉。从此,中华传统文化灵根倒悬,‘花果飘零’”。三位文化精英,在“刘文”的严厉指责下,俨然成了民族文化“罪人”。这种论断实在是罔顾基本历史事实的危言耸听,荒谬之极!
其实,今天稍有些历史文化常识的人,无论以什么角度来看当年的这场“废经运动”或“白话文运动”,都不难明白这场文化运动的伟大意义。
首先,在陈腐落后、臭名昭著的的科举考试已废除(科举考试的废除在1905年----笔者注)七年之后的历史条件下,当时教育部废止“读经”可以说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必然之举。当时的教育界及其社会上的大批有识之士都提倡科技救国,实业救国,强调向西方学习先进科学技术以抵御外辱,这是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想要改变落后现状的唯一思路,而陈腐不堪的“小学读经科”的课程设置明显不合时宜,所以,它的废止是势所必然、理所当然。
其次,当年小学废止“读经”以及语文课“全面改用白话文”,并不就意味着“从此,中国的教育体系中没有了经典教育”,而中华民族则“成了抛弃自己经典的民族”了。这种论断的荒谬性只要简单地审视一下中国近、现代文化史的演变轨迹就不难知晓。因为一个很简单的常识就是中华民族的经典传统不是谁想“抛弃”就可以“抛弃”的,即便当年的蔡元培、胡适和鲁迅是“真正”地仇视“经典”,要“抛弃”“经典”,但“经典”也绝不可能这么轻易地被“抛弃”的。而事实是“废经运动”或“白话文运动”自开展至今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无论中国的国家、社会性质发生了怎样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传统文化无论遭受了怎样的沧桑巨变,无论变得怎样“气息奄奄”,但“经典教育的千年学统与文化命脉”依然还在延续着,这是一个简单而铁定的事实,何曾被“割断”了?!
其三,对于像胡适、鲁迅等文化精英当年说过的诸多激进的“文化否定论”,我们也应该以历史的眼光辩证地去审视,才能真正理解这些激进言论的真正意义。比如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虽然激进地宣布了“‘旧文学’的‘死亡’”,但这并不就意味着胡适就从此成了一个传统经典文化的“抛弃”者,而事实是胡适对传统文化依然一往情深,护爱有加。他在稍后(1919年)倡导的“整理国故”的学术研究活动就体现了他对于传统文化的一种冷静、科学、理性的尊重态度,就说明胡适绝非一个要完全“抛弃”传统文化经典的人。至于鲁迅的“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的观点,也绝不可以简单从字面上去理解,而应该结合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角度以及鲁迅当时的复杂心理去全面把握理解。鲁迅说出这番话的真正意义是希望青年人真正了解中国现实,并切实以行动改变现实,而不要在古书里迷失了自己,因为接下来,鲁迅还说了这样的话: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
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所以,对于鲁迅的这段名言,决不可以如一般别有用心的鲁迅攻击者那样简单粗暴地仅从字面意义上去攻击、否定,而完全无视这番言论的真正语境以及深刻寓意;这就如一些鲁迅的攻击者把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里的“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一句话作为鲁迅心胸狭窄、仇视国人的证据一样,实在是浅薄之至!
“刘文”的“读经论”一开篇就在简单的逻辑理论上出现如此明显的硬伤;那么,接下来行文立论的肤浅与虚妄就几乎已被注定那是不可避免的了。下面我们就不妨来掂量一番他的立论主体的学术成色,看看其分量究竟几何?
二、
“刘文”在他文章第二部分正面阐述了他的理论观点,强调要“通过润物细无声的经典教育”来对国人进行“人格教育与心灵教育”,从而“全面提升国人文化素养,培养民族文化自信”;但接下来的立论逻辑却有些怪怪的,他居然没有正面论述开展“经典教育”的“深刻”意义,而是阐述“根据我个人多年阅读和教授经典的体会,总结出不读经典的‘十大流弊’”。我们知道,根据一般的逻辑学定理,否定判断只属于负判断,它的功用只是判断事物不具有某种属性,但并未能判断事物真正具有某种属性。“刘文”在这里本意应是要阐述开展“经典教育”的正面意义价值,但不知为何却自己“扭扭捏捏”地绕了一下,只说“不读经典的‘十大流弊’”。这种“回避”实在有种“欲说还羞”的尴尬,明显露出了底气不足的虚弱和犹疑。而事实是他的立论确实是肤浅加虚妄,所谓“不读经典的‘十大流弊’”,不过一番装腔作势的的概念堆砌、拼凑而已,其间的逻辑混乱、重复废话实在缺乏起码的学术水准,不禁令人想起鲁迅当年对国人“十景病”的讥讽,没想到这“十景病“的“流弊”竟然还可以在今日的学术平台上“谬种流传”,实在让人有些大跌眼镜!
一、只知有我,不知有人;
二、只知有己,不知有群;
三、只知有人,不知有天;
四、只知有物,不知有心;
五、只知有术,不知有道;
六、只知有贤,不知有圣;
七、只知有利,不知有义;
八、只知有用,不知有益;
九、只知有家,不知有天下;
十、只知有生命,不知有慧命。
下面,我们就来简单解剖析一下这“十大流弊”的具体内涵:
首先简单从这十大“流弊”的名称上,就不难发现流弊一、二、九在内容上完全是同样性质,分三点论述其实只是一种简单重复,在逻辑归类上完全没有必要。
比如在对“流弊一”“只知有我,不知有人”的分析中,“刘文”批评现代人因为“不读经典”,结果就是“常常只知有我,不知有人;只知爱己,不知爱人;一切以自我为中心,自私狭隘,充满戾气,甚至视他人为‘地狱’”。现代人的这种表现与“流弊二”的“只知有己,不知有群”的意义在逻辑上是明显重复的,“只知有我,不知有人”的自私自利之徒处理不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自然也就处理不了个体与群体的关系,这是不言自明的逻辑归属;同理类推,这种只顾自己不管别人、不管群体的人当然也不会关心天下大势,自然缺乏家国情怀,这也是不言而喻的逻辑归宿。所以,“流弊九”“只知有家,不知有天下”的分类分析也完全是重复废话,多此一举。由此可知,这三点分类其实表达的就是一个意思,现代人因为不读经典,才变得自私、偏狭,缺乏群体意识、家国情怀;但“刘文”却为了论文写作上拼凑“十流弊”的需要,废话赘言叨叨不已,本来的“一流弊”硬是生生给拼凑成“三流弊”了。
与此同时,“刘文”在说理论证上也明显牵强草率,完全缺乏说服力。如在“流弊一”中,“刘文”特别列举了大学生频发投毒、杀人等事件,以说明“不读经典”造成的“人格教育的缺失”就是导致这种恶性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这里理论逻辑的牵强及其错谬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知道政治教化的作用在历朝历代的影响都是有限的,都不可能对所有人都产生效果,任何时代都难免发生一些投毒、杀人等恶性事件。其中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如人性本质、生活压力、习惯教养、社会风尚等各种必然偶然因素的聚合,至于读不读“经典”,大概只能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种因素。“刘文”偏要把这微不足道的因素夸大成重中之重,如何以理服人?
在分析“流弊三:只知有人,不知有天”这一点时,“刘文”说到了传统文化中的“以人合天、天人合一”的“天人关系”时,阐释了古人的“天”所包含的“敬天法祖”、“慎终追远”的基本意义,强调“涵养人心、培养正信、移风易俗的朴素道德观和价值观”,“教人敬畏并顺应天命,存善心,养善性,不做逆天悖理甚至伤天害理之事”;但是,“刘文”同时又把现在的“生态环境恶化、地质灾害频发、水污染、食品安全、甚至雾霾”等种种“天人关系”的恶化现象与不读经典造成的“不知有天”联系起来,就有些离谱。其实古人“天人合一”理念中所包含的“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义,只是一种极其原始素朴的生存智慧,这与现代人的深刻复杂的环保理念根本不能相提并论。而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天人关系”恶化的现象其实是一个国际性的社会难题,这是人类文明发展所必然遭遇的一个“瓶颈”,而不仅仅是现代中国的病象;所以,“刘文”把这种现象与读不读“经典”连在一起,纯属生拉硬拽。
在分析流弊四“只知有物,不知有心”时,“刘文”引用了庄子、孔、孟关于“物我关系”的一些相关言论,其要旨就是人不要成为物的奴隶,要注重“心性”的修养。“刘文”忘了,这观点他刚刚其实已经说过了,在第三点“只知有人,不知有天”的分析中,“刘文”已经表达了传统文化“顺应天命,存善心,养善性”的道德追求,所以他这里的“心性”修养不过前面内容的重复而已,并没有什么新东西,所以,这里又是一组拼凑。
表面看来,“天人关系”“物我关系”分属两类,但其实在古人的解决办法中,二者并无多少实质性的区别,不过注重道德“心性”修养,“存善心,养善性”,如此而已。这里,不难看到儒家传统文化在如何面对诸多社会、人生问题的挑战时的极大局限性,他们除了一种理论、精神道德上的自我追求、约束和张扬外,并没有多少切实可行的主张。今天的一些学者往往把经典文化的意义、作用渲染得神乎其神,其实毫无必要,这些东西毕竟只是一些古代文人、思想家在科技水平极其低下条件下的一些主观想象而已,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不过是儒家文人学者的一种自我道德追求和心理安慰而已。
流弊五“只知有术,不知有道”的分析显得极其做作、虚妄,貌似深刻,其实浅薄。
“刘文”认为“近百年的中国教育,受西方影响,渐渐沦为专业化的知识教育、技能教育甚至职业教育。求学者只知有技、有知、有术、有器、有艺,而不知有道。”
我以为,“刘文”在这里提到的“术”与“道”的问题,不过一个伪问题而已。实事求是地讲,对于一般民众而言,“专业化的知识教育、技能教育甚至职业教育”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本,这样的教育有何不妥?其实在这里,“刘文”还忽略了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今天的大学教育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并非“专业化的知识教育、技能教育甚至职业教育”过多过滥,而是相反,恰恰就是缺少专科、职业技术教育,所有的大学都一窝蜂地往综合性大学的路上涌,以至于大学生毕业后就业路上因为缺乏一技之长,困难重重,往往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快节奏高效率需求。可“刘文”却对这种专业性的技能教育极其轻蔑,竟将他们斥之为“只知有技、有知、有术、有器、有艺,而不知有道”,实在有些莫名其妙!各行各业各持其业,各守本分,各尽其能,这是社会进步繁荣安定的大前提,民众知“技”有“艺”怎么就不行了?他们还需要懂什么“道”?而在“刘文”看来,真正的“道学”,就是中国古代哲学,可是,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他们需要明白古代哲学吗?研究古代哲学,那是哲学家的事,与普通民众何干?“刘文”摆出一副高高在上学问家的姿态,说出这一连串上不着天下不连地的空话,这种学院派的“官腔”实在酸腐难当,殊为可笑!
接下来,“刘文”在对“流弊六”“只知有贤,不知有圣”的分析中继续沿着“流弊五”的荒谬“深坑”感觉良好、自以为深刻地跳下去。
在这段文字里,“刘文”不厌其烦地阐述孔子由凡入圣的深刻伟大意义,阐释“圣人的境界和气象”以及“当今之世,圣贤之学也并非‘颗粒无收’”之类不着四六的高谈阔论,却全然忘记了所谓“只知有贤,不知有圣”的空洞迂腐的理论与“流弊五”的“只知有术,不知有道”的性质如出一辙,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也是毫无意义的废话。其实,即便从理论的角度来谈,所谓“贤”与“圣”的关系也不过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自然积累过程,只要明白了“贤”的意义,实际就迈向了通往“圣”的坦途。对于一个人一个社会而言,只要真正实现了“贤”的价值(“刘文”还强调了“贤”的另一层意义,即“多才多能者谓之贤”)就可以说是一种巨大的成功,而知不知“圣”,其实可有可无。虽然“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士兵”一直被世人奉为经典名言,但实事求是而言,真正的忠于职守的好士兵绝不会对“将军梦”有多大兴趣的,这个“将军梦”其实对他们是毫无意义的。“刘文”倒腾所谓的“只知”“不知”的玄奥,真不知想干什么?如果按照“刘文”的逻辑假定,国民虽然不读“经典”,但却已经知“贤”了,那你还有什么遗憾的,你还想要公民干什么,都要去成为道德“圣人”?这可能吗?同理,在“流弊五”中,求学者已经“有技、有知、有术、有器、有艺”了,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你还要他们“有”什么“道”?你还要他们都成为哲学家、思想家?岂有此理?
“刘文”在对“流弊七”“只知有利,不知有义”的分析中引用了一连串儒家关于“义利之辨”的论述,这固然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把当今社会许多见利忘义、惟利是图的现象发生的原因归结为“不读经典”,就又显得太可笑了。其实,关于“义利之辨”的善恶意义我想每一个成年人即便没有读《论语》也应该明白的,关键是今天社会中的许多人虽然明白这个道理,却并不愿意实施,依然要见利忘义。我想,其中原因中国人都明白,这就是社会监管不力,法律处罚不力,这与读不读“经典”无半毛钱关系。如果法律监管到不了位,你读再多的“经典”也枉然!
“刘文”在对“流弊八”“只知有用,不知有益”的分析中,本意是想强调一个人在生活中不要过于功利,只关注那些纯功利性的“有用”的事件,而应该关注一些“有益”的“无用”之事,“比如读书、听音乐、看画展、游山玩水等活动”,这些活动“大可怡情养性”,并提升“幸福指数”。这个意思本来是不错的;但是,为了强调不读“经典”的大“流弊”,
“刘文”居然断言这种只知“有用”和“无用”的“工具型人才”就“一定缺乏审美能力和大爱精神”,这种判断在逻辑上就明显有漏洞了。
与此同时,“刘文”在引用庄子“无用之用,是为大用”的话来论证他所谓“无用”之事的“有益”性时,又出现了不应该有的知识性“硬伤”,就让人不禁怀疑刘先生的国学底蕴恐怕也有些“浆糊”性质。稍有一些国学经典常识的人都应该明白,庄子的“无用之用”有他特定的深刻意义,指的是“树因不材而得以终其天年”的“无用之用”,强调的是一种因“无用”而自保的哲学思想,这是庄子在面对黑暗混乱现实时的一种生存智慧,也是他消极无为哲学思想的典型表述。所以,庄子的“无用之用”与刘先生所比附的“读书、听音乐、看画展、游山玩水”一类可以“怡情养性”并提升“幸福指数”的“无用之用”其实完全是两回事。今人喜欢把庄子的“无用之用”与今日素质教育的综合发展的积极意义相提并论,实在是会错了意,庄子的本意其实包含了某种“反智”的色彩,很有一些消极虚无的成分,这一点,今人不可不察。
在对最后的“流弊十:只知有生命,不知有慧命”的分析中,“刘文”由佛教的“色身”、“法身”“慧命”谈到儒家“三不朽”“精神慧命”的源远流长,其实并没有说出什么新东西,依然是强调儒家注重修身养性、追求道德高标的崇高境界,这层意思在“流弊三”“流弊四”的分析中已经表达过了,现在虽然换过了一些“色身”、“法身”、“慧命”的新概念,但换汤不换药,讲的还是修身养性、精神不朽这一类的老调重弹,不过是又凑成了一组“流弊”而已。
至此,“十流弊”的拼凑算是“大功告成”了;但究其实,流弊一、二、九雷同,三、四、十相近,五、六也是同一个“坑”,加上勉强可以独立的七、八,也不过“五”“流弊”而已,缩水已经一半,而在具体说理论证环节中也是废话连篇,漏洞百出。可以说,这篇所谓的“学术论文”除了让我们切实见证了一下当今注水学术论文的拼凑之‘妙“外,实在乏善可陈。
三、
从以上的简单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刘文”所阐释的所谓“不读经典”的“十大”“流弊”,除了不厌其烦的引用众多儒家的经典名言名句、再将它们与现实的“弊病”扯上许多莫名其妙的因果关系之外,实在没有多少真正的思考和感悟。
“刘文”认为,现代人因为不读经典,才变得自私、偏狭;才只知自我、自家,而不知关心他人;才会缺乏群体意识,更无家国情怀。
言下之意是不是说,如果读了经典,这些现代人的“弊病”就会消除?
“刘文”认为,现代人因为不读经典,就不懂得敬畏并顺应天命,存善心,养善性;不懂得精神慧命、道德追求的深刻伟大意义;以致于破坏“天人合一”的关系,造成生态环境恶化,并沉迷于“商品拜物教”,成为金钱财物的奴隶。
言下之意是不是说,如果读了经典,就会出现“天人合一”的和谐自然环境,人们就会变得“敬天法祖”,懂得修身养性,追求善良公正,弘扬精神慧命,不再成为金钱财物的奴隶?
“刘文”甚至认为现代人因为不读经典,所以只注重专业化的知识教育、技能教育甚至职业教育,只注重对多才多能的“贤”人培养,而不懂得中国古代哲学的博大精深,不懂得孔子由凡入圣的伟大追求和崇高境界。
“刘文”的这番指证批评实在有些莫名其妙:如果求学者真如刘先生所认为的“有技、有知、有术、有器、有艺”,且成为了“多才多能”的“贤人”,岂不大好事一桩,人们还夫复何求?难不成人人都要得“道”成“圣”,刘先生才满意?但是,这可能吗?
“刘文”又试图证明,现代人因为不读经典,所以才不懂得“义利之辨”,所以才会发生许多见利忘义、惟利是图的事情;而且变得极其功利,缺乏审美能力,生活毫无情趣,并且“一定”“缺乏大爱精神”。
这就是“刘文”列举的所谓“十大流弊”的基本内容,何其肤浅!何其空洞!何曾有丝毫的理论说服力!
何以会如此,究其原因,有三:
其一,作者本身对国学经典的认知极其肤浅,除了寻章摘句式地引经据典,堆砌、拼凑儒家概念名词外,实在说不出一星半点真知灼见。
其二、因为缺乏思想,却又偏要强为写作,以为凭着论文写作的“注水”方式,就可以轻易得逞;所以,东拼西凑,生拉硬拽,罗织了“十流弊”,表面看起来广征博引,而实质却极其空虚,色厉内荏,强不知以为知。
其三、“国学经典”本身的严重缺陷注定了论文的失败。因为无论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博大精深,但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就是,当今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以及面临的诸多困境,只有借助现代科学理念和法治手段才能解决,而所谓的“国学经典”在这方面根本无能为力,充其量只能起一种局部辅助、借鉴的作用。“刘文”把“国学经典”当作包治现代政治、人文社会百病的“灵丹妙药”,实在是陷入崇古泥古的误区太深,怎么可能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
四、
“刘文”最后甚至提出了他的“有限读经”论的一些具体要求:虽然他认为“不必搞成‘全民运动’”,而且也只能“择善、择优、择要而读”,但是,“正在学校受教育的中小学生应该读经”,“比如四书须读全本,五经、老庄及诸子百家、史部、集部等精选泛读”。
看到“刘文”这种信口开河的“有限读经”设想,我觉得实在太荒唐了。光是读完全本的“四书”会是什么概念(遑论还有其他经典的“精选泛读”)?倘若中小学的语文课堂真的以此为目标,那么,语文课就真成了“国学经典”课了,而其他的内容还要不要学了?为何“四书”就不要“择善、择优、择要而读”?难道他们就这么完美?就应该全盘接受?这是什么道理?倘若真以四书全本为教材,那么,中小学语文教学恐怕就要完全回到文言文复古教学的“老路”上了,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我想,即便当年蔡元培废除的民国“小学读经科”读的“经”恐怕都不可能是全本,而只能是“节本”,而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小学语文教学竟然要读“四书”全本“经”,这该是如何荒诞不经的奇谈怪论!?
行文至此,不仅联想到前不久国内一些著名学术网站上关于“弟子规”的讨论;而且,据说由人教出版社、教育部联合推出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全国中小学实验教材》已经出版发行,内容包括《弟子规》《三字经》《声律启蒙》《千字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道德经》《孙子兵法》《古文观止》等,学习对象从幼儿园的小班孩童到高中学生统统纳入囊中,似乎真有些读经浪潮汹涌的势头;但我对此却只有一种胡闹的感觉。
时代已经迈入了二十一世纪的高科技电子互联网时代,日新月异,改革创新求变已成为时代的主潮。如果有人还真把几千年来的旧玩意儿太当一回事,除非别有用心,否则,那就是真正疯了。一个理性的国学研究者应该明白,无论国学经典如何博大精深,也已经是糟粕精华纠缠不清,即便其中的精华成分,也难免有落伍之嫌,也基本不合时宜了,完全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了。这些老祖宗的传统文化当然要保护,要研究,但只能在小范围内由一些专业研究者去研究整理,但要将它推而广之,就不免迂腐可笑了。就如作为国粹的京剧,在今天的命运除了最后进博物馆,恐怕也难觅其他出路了。不错,京剧艺术在中国传统戏剧艺术中的确也称得上博大精深,且韵味无穷;但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审美需求和准则,京剧艺术的审美准则在今天的年轻人心目中已成昨日黄花,完全没了市场,虽然有少数的京剧爱好者在竭力保护、推广京剧艺术,但最终还会无济于事,京剧的消亡是无可挽救的事实。这是时代潮流变化所致,是无法抗拒的历史规律。历史是不可能走回头路的,京剧想要生存,也只有变革,融入现代艺术形式中,想完全保留它的“纯正清白”之身是完全不可能的了;而中国文化传统的承继也是如此,中国也绝不可能回到之乎者也的文言文时代了,国学经典也只有在大浪淘沙的自然筛选过程中融入现代文化,在其中变形、遁迹、改头换面、适者生存以求取新生,想全盘复古,全本读经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只能成为笑柄。
由此可知,现在的一些鼓吹大力推广国学的人,要么是不学无术,无知无畏之流;要么是别有用心、沽名钓誉牟利之辈。多哗众取宠之心,少实事求是之意。回到“刘文”的论文本身来看,其中的学术泡沫、注水现象一目了然,这恐怕也是当今大学学术研究普遍缺乏创新能力的一个缩影:所谓的学术论文的原创学术性往往阙如,更多的是模仿、抄袭、拼凑。近日国内一流大学复旦大学的校庆宣传片抄袭丑闻在网上引发热议,可以成为当今国内大学学术研究缺乏原创性的一种象征。堂堂一流大学学府,竟然连拍一个校庆宣传片这样的小儿科玩意儿,都得不顾廉耻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抄袭他人,连这么简单的“创新”能力都不具备,真不知那么多的专家教授是凭什么在大学里混下来的。这种状况不禁让人想起《红楼梦里的一句名言,“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原意本是形容贾府虽然表面还风光八面,但内部却早已危机重重、大厦将倾的末日光景,但我以为用来形容当今国内一流大学名不副实的学术乱象,应该是非常贴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