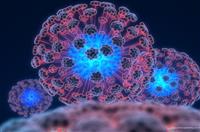
人们对“学报体”语言的厌恶和轻视由来已久。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王蒙就提出要改变中国学术文章的文风和表达方式,但时至今日,这种文体语言的枯燥、乏味和做作,不但没有丝毫改变,反而在课题经费的增多,评职的压力以及学位竞争机制的促使下,沉疴日重,且看不出有任何救治的痕迹,甚至学术中人也在私下承认,这种发表在各类“学报”和所谓的“核心期刊”上的文章,实际读者只有两个:一个是责任编辑,另一个就是作者自己。只是大多数人囿于职称、房子和学位的诱惑,牢骚归牢骚,制造归制造,且终生走不出它的怪圈。
“学报体”文章为什么作不好?首先是因为这类文章没有“问题意识”。大凡一个命题、一种学说的最初诞生,都是因为对某一种社会现象、某一条学术定论、某一个智力疑难不满,并寻求自己的解决方式,于是才诞生了一种主张、一种学理或一篇文章。这就好比先有病,然后才有医理和药方一样,没有听说哪个医生还不知道一个人有病就能开方子、动刀子。但现在大多数所谓的“学人”脑子里除了猪肉、职称和房子,哪有什么“问题意识”和“智力疑难”?
因为没有“问题意识”,当然就谈不到自己的解决方式,因而只能下笔千言,离题万里,说些大而无当、玄而又玄的“鬼话”自欺欺人。“鬼话”当然可以使住房面积增加,课题经费充裕,职称和官(学)位提高,但这对一个时代的世道人心有什么影响呢?于社会的治乱安危有什么好处呢?虽然学问不能以浅近的功利标准来衡量,但一个时代的学问家若使用着纳税人大把大把的钱,却又完全置社会的水深火热于不顾,专做一些趋时媚世,只给自己带来实际收益的文章,这种学问家不说“冷血”,至少也是麻木自私的。
古人讲,“物不平则鸣”,又说“情动於中而形诸言”,就是说大凡一个人被外界的事物刺激,就自然会用语言表达自己。铁石相激,必有火花;水气相荡,乃生长虹。一个对历史没有责任感,对他所处的社会漠不关心,对身边亿万同胞的苦难毫无知觉的人,做起文章来除了装神弄鬼,用一大堆半生不熟的“概念”、“术语”修补缝缀外,还能有什么好看?“修辞”贵在“立其诚”,而现在大学里的学者、教授写文章,先是狠狠地磨墨,然后把心中各种鲜活的感性的语言“翻译”成“学术语言”才能下笔,这种“辞”“诚”在哪里?退一步说,即使“翻译”得好,也不如这些“概念”、“术语”的原创著作更精彩,我为什么非要看你这个“二手货”?我虽然不是学界中人,但我注意到,现在不论是土博士,还是洋博士,写文章都喜欢生吞活剥一些西方重要典籍的“概念”和“学理”,又是“解构”、“建构”,又是“能指”、“所指”,可这些土洋博士没有想过的是,你即使引用得再多、再好,也不可能比原著更精确,我为什么非要相信你这个倒手转卖的人?
不错,西方的一些重要典籍已经不是西方世界的专利,作为全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和普世价值,值得一切向往文明,渴求进步的人士学习。可学问不是用来卖弄的,西方的典籍再重要,也是西方社会的有心人,对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面临的问题,提出的救济方案。作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价值,如果不能用彼时彼地的方案和学说来观照、指导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它就一点用处也没有。
我们固有的孔孟韩杨、庄老佛禅也一样。儒道再伟大,也是为解决它那个时代的困惑,满足它那个时代人心的需要而提出的救世理论。世界上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一管几千年的宗教和学说。如果不因时而化,顺应潮流,一味逆天背时,生搬“仁义”,死抠“主义”,就像拿汤头口诀治一切病的医生一样,只能延误病情,害人性命。
学者们为什么都喜欢玩弄抽象概念,而不喜欢研究具体问题?因为研究具体问题要花费精力,搜集材料,还要实地考察问题的发生根由,必要时还要召见当事人见证问题的发生过程,这一切都没有现成的例子照搬,更不能在电脑上下载几篇同类的论文拼凑剪贴,孔子和柏拉图也没有发表过现成的意见。更重要的是,这样下功夫作出来的论文当局会不会喜欢?能给我自己带来什么好处?会不会触及一些相关人事的利益?同事和领导会怎么看?玩弄一些抽象概念就不同了。有《大英百科全书》可查,有 《辞海》、《辞源》垫底,大不了几晚上不睡,整几个关键词,多搞两条注释,多抄几本参考书,多翻阅几篇同类文章,有什么难?
我当然知道,除了个别一些装神弄鬼装上瘾,装出美来的学者外,大部分学术中人如此而为也是不得已,但这能说明什么呢?难道在科举时代人人都喜欢八股文吗?我也知道,一个时代的学术风气乃至整个社会的文风与这个时代的政治制度和学术体制是有很大关系的。一种落后、腐朽的学术风气的改变,一种僵化、荒谬的学术规范的打破,要依赖整个学术体制尤其是孕育这种学术体制的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就像科举制度废除了,八股文自然就灰飞烟灭了;但在这种根本变革到来之前,我们除了同流合污、助纣为虐就真的束手无策了吗?如果我们的牢骚只表现在卧室里——顶多是在楼道内,到了讲堂上和书桌前却照样做奴隶或帮凶,那么,我们怎么能指望这种变革会自动到来呢?我的个人主义人生观厌恶一切犬儒主义的说教和生活方式。用萨特的话说就是,是英雄把自己变成了英雄,是懦夫把自己变成了懦夫。一个人即使在最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也应当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如果他没有选择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出努力,那么,他就丧失了怨天尤人的资格;就像一个人选择了反抗和水滴石穿的努力,他就有理由相信未来的一切巨变都有他的一份推力——正如一个人选择了同流合污或助纣为虐,时代或体制的罪恶自然就会有他的一笔记录一样。中国人喜欢把一个历史时期的罪孽推给时代或一两个替罪羊,但时代是谁?替罪羊是“替”了谁的“罪”?这些问题是应当引起我们每个人反思的。
2008年7月30日草于饮马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