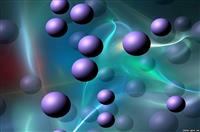2008,在中国文化脉络里面,本来是一个吉祥的数字。但自岁入戊子,却是天灾人祸不断,先是南方冰灾,接着是手足口疫,再接着是山东火车相撞,西藏闹独立,然后便是汶川的这场大地震……网上流传一个“震撼2008”的段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国也,必先下其大雪,撞其火车,抢其火炬,震其国土,涨其物价,跌其股市,空乏其民,增益其所不能……”。我不知道这段子的编撰者是语带嘲讽还是充满无奈,事实确实是这样。灾祸连连的中国,灾祸连连的2008。
与这灾祸一起而来、震荡着中国的,是社会传闻(谣言)的激增。忽地传闻北京要地震,然后是官方出面辟谣;忽地又传闻宁波淡水鱼出现霍乱,于是官方出面辟谣;忽地传闻地震十天前有美籍华裔地球物理学家曾经致函国家地震局,提醒在此期间,川内将有相当级别的地震发生,但官方置若罔闻,于是又有官方出面辟谣;忽地又出现一种说法,说2008年的天灾人祸连连,都是8字惹的祸。好家伙,2008年8月8日8时08分,那可是一连串的8字呀,都是8惹的祸,那结果怎堪设想?!于是官方又急忙出面辟谣,说这样的说法不仅是迷信,简直就是在制造谣言,并且以极严厉的口吻警告,严禁制造、散布谣言,“以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否则……
谣言真的就这样可怕?需要官方一再动用大众媒体与政府权威,作急急如命令式的辟谣止谣乃至严厉打击?
其实,这是过虑了,是对谣言的严重误解。
从传播学的视角看,“谣言”其实只是一种社会传闻,是挺普通的信息传播方式。如果我们不先入为主地将谣言当作“凭空捏造”、“恶意散布”的信息,而是按照《谣言》作者卡普费雷的提法,则“谣言这个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预示它的内容的真实和虚假”,因为,“一般来说,所有建筑在真实或虚假基础上的谣言定义都导向一个死胡同,无法解释谣言的勃勃生机。对真实与虚假的对立进行逻辑检验,结果表明将信息与谣言区分开来的界限十分含糊不清。通常,当一个新闻通过口传媒介的方式传来时,公众是无法区分真伪的。”从这样的角度,卡普费雷对谣言做如下定义:谣言是“社会中出现并流传的未经官方公开证实或已经是为官方辟谣的信息”,它“通过非正常的渠道而不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以口传媒介或散发传单的方式进行传播”。《谣言的内幕》作者罗斯诺也认为,谣言只是“夹杂了个人对世界的主观臆测的公众信息”,“表达了试图认知生存环境的人们的忧虑和困惑”。
作为社会传闻的谣言,首先是基于事实未明、一时无法准确判断时的信息散布。它不仅包括模糊的或片段的事实,也内含着情绪性的反应与评价,以及对事实的某种想象、解释与结果的预测、担忧。事实的成分与想象的成分混合在一起,情感的因素与理性判断纠缠不分,知性的解释与感性的冲动彼此夹杂。对于不确定状况的担忧与紧张;对于未明事件与原因的疑惧与警觉;对于自身危险的困惑与恐惧等等,是谣言产生的基本土壤。这种不安全感通过口耳相传与身体接触,姿态模仿与情绪感染,迅速在人群中散发,引发人群的紧张不安与预警动作(严重时也可能导致动乱),其目标只有一个:规避即将降临的危险。
除了人为制造、带有颠覆动机的谣言之外,一般谣言均不是凭空产生,而是无风不起浪,其来有自。大多谣言的产生,均与人类个体对威胁的直觉有关;对生存环境威胁的直觉,对于某种不明因素的恐怖有关。这种不安、恐怖,威胁感,通过传闻、谣言等等不能明确表达的信息传达出来,引起其他个体的连锁反应与群体行动,群体预警机制的启动,不仅能通过群体的数量加大对信息的了解、澄清模糊的信息因素,也能补救个体生命面对不明危险时的脆弱,增强个体应对危机的自信与力量,在集体行动中,避免个体直接暴露在未明威胁之下。群体的数量与巨大势力,不仅可以抵抗无法预见的灾害,也可以庇护一己的生命。
避害趋利,是谣言的基本机制。这一机制,不仅是生物的,也是文化的。
由于谣言产生与传播的这种切身性、直觉性与全息性,保证了它传播的迅捷与应对的敏锐,在许多方面,人类社会谣言的产生与传播,与动物世界规避自然灾害的本能反应具有相同的机制。
人类总是以傲慢的姿态将动物世界规避自然灾害的种种现象视作“本能”,当作低级的生存技巧,但却又不得不以矛盾的心态对这种本能惊羡不已。本能也好,智慧也好,不管人类如何解释,动物世界在面对自然灾害时的避害趋利能力,人类是无法否认的,正是这种本能保护了动物们的生命。这种机制,尽管以人类目前的知识与智慧还无法完全理解与解释,但仅就信息传播层面而言,这种机制,与人类社会谣言传播机制基本相同。差别在于,动物与动物所生活的环境关系更加密切,动物对于环境变化的反应更加全面、直接与敏感,动物的生命体验与求生的冲动更加自然、强烈,动物个体之间信息传播的方式更加直接与迅捷。 这种机制,是原始的,但也正因为原始,才是直接的、全息的与迅猛的;也正是这种原始,挽救了生命,保全了动物整体的生存。
如果将这种信息传播机制与现代传播方式进行比较,在面对突发性危机事件时的优劣可以立时互见。
现代传播机制即我们所谓的大众传播,主要由现代媒介(报纸、电视、互联网等)与新闻发布制度构成。这是一种严格专业化(技术化)与程序化(科层化)的制度体制。是一种非人身的制度。在信息采集、确认、传播等方面看,这种制度具有着明显的优势:通过高技术手段,捕获相关信息,并纳入技术——学科的确认、解释框架之中;经过确认与审查的信息,进入生产——传播流程,由现代媒体承担信息的输送与散播功能。这种工业化流程自然有他无法替代的优势:信息内容的准确、清晰;专业化传播的单一性,保证了歧义的消失;现代技术的全面使用,保证了传输的速度与广度。科层制的严格程序,保证了的信息的可复按与可证实性。同时,这种信息一旦确认,能通过同样的非人身渠道,由技术部门传输到决策部门,为决策部门提供科学的决策资讯。如果在技术上不失误,决策的正确基本可保无虞……
然而,这种专业化的准确与清晰,是以牺牲信息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过滤出来的,信息越是精确,信息量越是流失;这种信息过滤,有可能删去一些对于人类来说尚未理解但却可能是致命的信息,其次,是其专业化生产过程,往往又以时机的延误为代价,在面对瞬息万变的自然灾害,尤其是面对地震这样只有极短预警时间的灾变时,这种时机的延误,在拯救生命的第一时间内,不足以应对危机,却实足以毁灭生命。追求准确与清晰,对于决策者来说,也许无法避免,但它造成的时机延误,对于脆弱的生命来说,如果不是毁灭性的,至少,也是无法挽回的。
而现代传播却正以压倒优势,侵占并剥夺着传统信息传播方式的空间。政府又借助着越来越集中的权力打压甚至禁绝社会自传播途径。信息的独占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的常态,而为社会所习惯。这种信息独占的危害,无论是对人类文化还是对于个体生命,都将是致命的。
以阜阳手足口疫情为例。
早在官方发现并发布确切疫情报告(4月27日)之前半个多月,至少在4月6日,民间已经有了“怪病”的传闻,“怪病”的谣言引发了阜阳地区的不安,部分家长为此把孩子从幼儿园接出来,不轻易出门,有的甚至送孩子到乡下去“避难”。但当地政府却在4月15日通过媒体,正式出面辟谣,说“怪病”是呼吸道疾病。很多家长因为官方的结论,又将孩子送往幼儿园、送往医院检查,“抱着孩子来看病的家长络绎不绝,大家挤在一起,没有任何隔离措施。”(参见《南方都市报》,《潇湘晨报》等媒体)
在谣言机制之下,部分小孩本来已经避开了疫情威胁,但政府的“辟谣”,诱使他们再次暴露在疫情威胁之中,数十条生命的夭折,其中,又有多少是官方“辟谣”造成的呢?!
这样的结论,不是笔者要故意耸人听闻,责难官方,稍具常识的人都可以推出来。笔者并不想穷究官方的责任:是有意延误还是技术性失误。只想提醒一个事实:当技术与官僚为着追求资讯的精确与为信息发布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其处理信息与做出决策所必然带来的反应滞后,将直接造成生命的毁灭,在这样的困境中,作为公信力的拥载者,为什么要垄断信息的发布?为什么不将信息传播的权力还归民间?将生命自我拯救的机会还给生命自身?
在技术不能迅速做出精确判断时,为什么不能让模糊、混杂的信息自我传播,将信息真实的判断权力交回给有理性的个体?!
再以这次汶川地震为例,看看我们为独占信息所付出的巨大代价。
且不管十天之前已经有了美籍华裔地球物理学家预警这样的说法吧(以目前的资讯状况,大约是无法证实的)。至少,在震前三天,四川地面已经出现动物异常——数十万蟾蜍大规模迁移,引发诸多谣传。本来,动物异常现象,可以作多方面解释,可以是天气异常,也可以是环境污染,可能是水旱灾害,也可能是地震等等……如果让谣言自然传播,接受者会做出与自己知识及经验相关的解释,并采取相应的应急措施。姑且假设在当时当地,相信动物异常预示地震的人数只占3%吧(这当然是保守估计,但也只能是一种假设了)。如果官方不出面辟谣,不由技术官员作“单一性”的解释(据新浪网转发的消息,四川地方电视台在播发蟾蜍异动时,技术部门解释说是环境污染,这样的片面解释不仅将信息的多样性作单向封闭,也将民众行为导向单一应对模式),诱导民众放松警觉,而是在解释时将几种可能性告知民众,让民众自己做出自己的判断,则这3%的人将做出自己的避让措施,至少,会有一部分人,能因为这样的避让,得以保全自己的生命。但是,官方的辟谣,让这一部分人丧失了生存的机会……
如果再进一步追问,官方辟谣的技术依据是什么?技术部门又将如何回答?!
事后技术部门的解释是,对于地震,目前没有任何技术可以保证准确预测。我相信这样的解释不是开脱责任,而是诚实与科学的。然而,这样的解释却将技术部门逼上了逻辑的死角:既然在技术上没有任何保证可以准确预报,那么,技术部门又是凭着什么在震前做出判断,并通过媒体发布信息,说地震传闻是谣言?技术部门必须就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在自己都无法准确判断的情况下,技术部门为什么将另一种可能性完全抹杀?而这种抹杀的结果——数万生命的惨痛代价——是完全可以预计的。
也许,“稳定”是一个备选的理由,因为“稳定压倒一切”。但如果“稳定”可以扩张到忽视生命的程度,这样的政治口号之政治正确性又在哪里?!
也许,担忧谣言造成社会动荡,是又一个备选理由:不仅从政局稳定角度,也从保护生命的角度,毕竟,谣言所造成的危害,事实俱在。但这样的担忧显然是对谣言的误解,是颠倒因果:往往不是谣言导致动荡,而是动荡导致谣言的爆发,尤其是在正常信息传播渠道被窒息、政府部门丧失公信力的时候。谣言所起的作用,至多是加速社会动荡而已。
其实,人类本来具有动物式的预警本能,但却在文明化过程中退化了,其退化机制,虽然可以以“用进废退”的进化论作简单解释,但关键还在现代文明对于这种本能的压抑与打击,关键在于公信力与公共媒体对于民间社会信息传播渠道的抑制与打杀,对人类信息自由传播的一系列制度化抑制。
如果动物间的信息传播,也来一个信息生产专业化制度,一个新闻审查与发布等信息控制制度,试想——如果人类还有一点这样的想象力的话——动物的本能还可能及时“预警”吗?!动物们还能以“生死时速”来挽救自己的生命吗?!
现代传播给了人类诸多的便利,确实是文明的标志,但也同样带着致命的缺陷。本来,有一利必有一弊,乃一切制度的通例,如果我们能对这样缺陷保持必要的警惕,而保留人类自发的信息传播途径,这样的缺陷或许可以弥补。但我们的文明过于自信了,我们的公共权力过于自信与专横了。在这种自信与专横之下,现代信息传播以专业化与独占化的方式运作,并一统天下,抑制并挤占了几乎所有社会空间。而现代传播内在的致命缺陷,就在这样的自我膨胀中,被遮蔽与忽视。
这是一个致命的盲点,制度的与文化的。
这个盲点所形成的黑洞,正吞噬着无数的生命。
但文明却拒绝承认,而沉浸在进步的兴奋之中。
人类对文明的适应过程,以丧失生命本能为代价。这种适应,是文明造成的“习得性失能”。
但我们却忽视了这种丧失之痛,而将之作为动物的专利弃如敝屣。
在现代文明、尤其是在现代传播手段如广播、电视,报纸以及互联网产生以前的数十万年,人类信息传播手段,主要是传闻。报纸、广播等现代传媒很晚近才出现,政府控制的新闻发布制度更晚。相对于人类漫长的历史来说,文明不仅短暂得可怜,而且很不完善、脆弱到“弱不禁风”,在面对自然的巨大灾害时。
面对越来越严重的自然灾害、上天之惩罚,人类除了谦卑地低下自己的头颅之外,还需要反思,反思现代文明中过度的权力膨胀——对于自然与对于人类自身的控制欲望。重新清理传统积淀与历史所创造的人类机制,尊重智者海耶克所说的自发自生秩序为人类留下的智慧,约束权力冲动,谨守权力边界。对于谣言等社会传闻,给予尽可能大的空间,避免对另一种可能的扼制。
沙思危机、禽流感、手足口疫、汶川地震……近年以来越来越密集的系列天灾人祸,期间都能听到政府权威的最强音:禁止谣言。也许,从一面看,这是一个责任政府的职责所在:灾祸所在,政府所在。但如果从另一角度回看,也许会有“政府所在,灾祸所在”的背反结果。事实上,政府过于强烈的止谣声音,所产生的结果,无不是以那些无辜生命为代价而收场。这样的结果,难道仅仅是对谣言的误解与担忧造成的?毕竟国内与国际学术界对于谣言的研究早已有了基本共识。面对谣言,请教专家,这也是现代技术政治的常识。但我们却始终能在这样的灾难之前听到这种近乎严厉的止谣辟谣之声,听到“负责”政府权威的无处不在。显然,止谣辟谣,已经不仅是对谣言的误解,而是那无法遏制的权力冲动:对社会信息全面控制的权力冲动。
信息自由载在国宪,但信息自由要落到实处,首先要允许社会、尤其是民间社会自由传播,不管这样的信息是谣言还是新闻、是否经过技术与官方的证实。如果官方可以凭着行政权力将任意一种信息当作谣言禁止,则不啻是对宪法的亵渎与侵犯,在程序上,也是对司法权力的僭越。
谣言承担着生命的自救,
但谣言更是人类的基本权利!
2008年5月24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