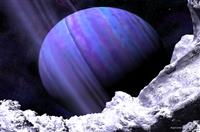我们试图用现代性转型这样一个命题来表述当代中国问题,实际上它也是近代100多年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主要脉络。现代性不是一个时间逻辑,它有特定的内涵和指向,现代性转型是指从传统社会向以现代核心价值观(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支撑,以市场经济、民主宪政和民族国家为基本制度的现代文明秩序的转变。
起源于欧洲的现代性价值观和制度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但“现代性”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的广泛使用则是上个世纪中叶才开始的,其背景是“后现代”思潮的出现,为了区别两者,他们将欧洲启蒙运动倡导的价值观及后来由此产生的西方工业化社会称为现代性和现代性社会,并对之提出质疑、解构和批判。与现代性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现代化,或现代化理论。帕森斯继承和开拓了韦伯关于现代化的理论,对现代社会形态做出解释。在冷战时期,这一理论又被用来与社会主义理论争夺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道路选择的主导权。“社会转型”是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研究的课题,上世纪冷战后它专指从专制向民主政体的转变并形成了相关的理论。
在学术界,在不同的语境下,现代性、后现代性、现代化、社会转型这几个概念的内涵和价值判定始终存有较大争议。对概念、逻辑和语言思辨性的追究是学术研究的一个癖好,我们今天关注的是中国的现实问题,是一种“问题意识”,以此为出发点并寻求相关的理论解释。
二、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对“阶级斗争历史观”的反思
我们最早接受的历史观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它通过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使生产力得到解放。据此,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几个阶段。依照这个史观,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均被视为中国近代史上具有主线意义的标志,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应具有社会转型的标志性意义,中国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阶段,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
与马克思理论范式不同的是韦伯的现代化理论,它认为欧洲经历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是对人的价值的发现和认同,使人从神权和皇权的专制统治中解放出来,获取了本来就属于他们的自由、权利和理性。为了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人们选择了市场经济、民主宪政和民族国家的制度。这样一种价值观和制度被称为与传统社会不同的现代社会或现代性社会。依照这一史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应是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主线标志,而在此之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以及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与改革开放对中国社会转型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中国的现代性转型并未实现。毛泽东建立的新中国实现了民族国家的构建,中国从此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主权,同时启动了工业化进程,但新中国的国家治理仍带有较强的传统社会色彩。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从异化中回归,并首先在经济领域开始了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创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但邓小平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依然是一个未完成的课题。
上述两种历史观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因果关系的认识是相反的。我认为影响历史变迁的因素是多元的,各种因素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关系,在不同条件下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可以发生变化。在这个意义上讲韦伯的历史观是有启发意义的,它至少告诉我们不应把阶级斗争作为决定历史变迁的唯一因素。从实证考虑,中国的近现代史变迁的动因和内因逻辑是寻求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性社会的转型,韦伯的历史观可以对这一历程做出更准确解释。
三、八十年代初的思想启蒙与改革:内在逻辑的一致性
八十年代初是中国现代性转型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年代,其主要标志是所谓“第二次思想启蒙运动”的发端和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现在回顾这段历史,后者成为主线,前者似乎被遗忘和淡化了。当然,就深度和影响而言,对那次“思想启蒙”也不应给予过高的评价。但两者发生在同一个时期是有内在逻辑一致性的,因为市场化改革是现代性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意义不仅仅是资源配置的效率,也不仅仅是民族的振兴和民众福祉的改善,在更深的层面上它反映出了人的自由、理性和权利为代表的现代价值观得到了认同和尊重。尽管当时人们对这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的认识尚不深刻,但启蒙和改革曾经是当时政治家、社会精英与民众的共识。中国的现代性转向也从中获得了不可估量的活力。
四、共识的破裂:中国道路之争
九十年代被称为共识破裂的年代,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今天。八十年代初的“思想启蒙”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中夭折,并变奏为官方主导的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目标的“思想解放运动”;政治体制改革被悬置,市场化改革在产权、政府职能、要素价格方面裹足不前。在经济改革取得进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贫富悬殊、贪污腐败、道德失范、信用缺失、环境破坏等诸多负面的现象。如何认识这些问题?其症结是“改革惹的祸”还是缘于出现了“改革疲劳症” 和“改革恐惧症”?对此,社会上产生了不同的认识,精英的共识也破裂了。
进入新的世纪,中国已成为全球经济的大国。与此相对应的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和价值体系的缺失,这使得社会转型呈现出扭曲和失衡。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走到了一个关键的路口,面对未来的选择,政治家和社会精英应承担起历史的责任,营造包容、开放的文化,以寻求新的共识。
我认为,中国社会转型的进程不应被引导到“现代化建设”的路径上。因为在中国的语境中现代化即是“民富国强”,它的内涵主要是经济和物质的指标,而价值体系和制度安排则被抽离。在当今的中国,现代性被现代化所替换并表现为一套“中国现代化的叙事”,这套叙事的话语包括稳定、和谐、民生、国家利益(民族振兴)、治理的效率(集中力量办大事,举国体制)。在稳定与自由、和谐与多元、民生与民主、国家利益与个人权利、治理的效率与制衡之间应寻求一种均衡,但前者不能代替后者,因为后者是现代性社会价值体系和制度中的核心和基础。
中国社会转型的进程也不应被“新左派”对当代西方社会的解构和批判所消解。“新左派”是后现代思潮在中国的反映,他们认为中国已被纳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市场化改革中出现的各种弊端反映出中国已染上了正在走向崩溃的资本主义社会病。中国应该而且有机会选择一条不同于西方社会的道路,这不仅关乎中国的命运,也是人类的希望。所谓“北京共识”,各种版本的“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成为他们热衷的话题。中国面临的问题和社会发展阶段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成就只能称为“经济增长的奇迹”,而“中国模式”的形成则须以社会转型为标志。西方社会呈现出的病态需要医治,但不意味着它的价值和制度体系的死亡;中国的现代性方案也不可能是西方模式的简单复制,它必然包含中国传统、中国经验的元素,它应该体现我们对西方社会危机和病态的认识和批判。
五、激进与保守:中国社会转型路径选择的悖论
自欧洲启蒙运动以降,产生了三种近代思潮,即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英国经验主义”(洛克的“自然法”、苏格兰启蒙思想)和“大陆理性(唯理)主义”(笛卡尔的“科学主义”、卢梭的“积极自由主义”),近代的三种思潮都可以从中找到其思想的渊源。激进主义不仅表现为对社会变革采取的暴力或革命的方式,更为主要的是对传统和经验的立场和态度。激进主义崇尚“宏大叙事”,颠覆传统、摒弃经验,它对陈旧的观念、制度具有杀伤力,但其本质是一种“乌托邦工程”且难以避免自身的异化。“英国经验主义”则崇尚传统和经验,通过自发的演变实现社会的转型和发展。当然英国社会转型历史上也有过革命,政治家并没有放弃调动民众激情去实现特定的目标,但这不是一种常态,而是一种“非常政治”(阿克曼),问题解决后,它们具有重新回到“日常政治”的机制。激进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能对其产生制衡的是保守主义。在西方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两者尽管主张不同,但对现代性的核心价值观都是认同的,所谓保守主义其保守或捍卫的主要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在中国近现代不同时期社会思潮中占主流的是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两者的混合(即在推行市场化改革中融入了社会主义的公平、公正思想),但就对中国社会的变革方式及对中国传统和经验的立场和态度而言,它们都带有激进主义的色彩。中国所谓的保守主义,无论是近代儒家纲常秩序的信徒还是当代阶级斗争理论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捍卫者,都是反现代性的,不能对激进主义思想形成制衡。由于长期的集权制度,中国的传统和经验中缺乏现代价值和制度的基因,难以自发地走上现代性转型的路径,这就使激进主义获取了在中国生存和发展的诱因。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近现代的社会转型始终伴随着激进主义对保守势力的挑战、抗争,而又未能避免最终自我异化、走向反面。因此,在推进中国现代性转型的过程中,认识激进主义在中国存在的某种必然性,保持对激进主义的警觉,避免陷入“激进—异化”的怪圈,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应具有特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