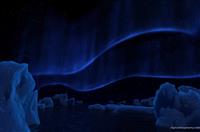二
我五岁那年,邻家小五姑已经八岁了,她要去上学。她是我最好的玩伴,所以我也吵着要和她一起上学,母亲除了干农活,还要照看四岁的妹妹和三岁的弟弟,没时间管我;奶奶也要忙地里的农活,也不想管我。让我去上学,是最好的选择。
开学了,我背上三叔的旧书包,包里有两个母亲用父亲从单位里拿回来的废纸订的本子,扛着一个小板凳(那时候上学要自带板凳)跟小五姑一起去上学。学校就在村子里,离我家也就二、三百米的距离,老师都是村子里的熟人。除了校长是正式教师,其余都是民办教师,平时一边种地一边教书。
学校其实非常简朴,一排五间土墙草屋,分成两口教室,一年级单独一口较小的教室,较大的那口是二年级和四年级共用。门口有一大片空地,就是我们的操场。操场旁边还有一片树林,夏天,屋里热时,这里也常常成为我们的临时课堂。学校后面不远,是一个面积很大的麦场(打麦子,打稻子用),在不打庄稼时,这里也常常做我们的操场。三年级的教室在学校后面约五六十米的地方,是借用一家农户的房子,这家人全家都移居到外地去了。
教室更是简朴,地面是泥土的地面,坑坑洼洼的,墙是土墙,也是坑坑洼洼的。课桌是用砖块撑起的几条长木板,没有涂油漆,就是原木的颜色,但用得时间久了,又旧又暗。学生从自家带来的凳子各式各样,大小不一。老师的办公桌就放在教室的前面。一年级的老师既教数学,也教语文。老师没有专门的办公室,就在教室里办公。
我个子很矮,幸好小五姑的个子也很矮,我就紧靠着小五姑坐在第一排最里面的一个位子,紧靠着北墙摆放着老师的办公桌。
第一堂课,还没有发课本。许多学生既没有笔,也没有本子。教我们的老师姓徐,大致四十余岁。他把粉笔掰成许多小段,一人发一段,就在课桌上学写字。第一堂课,他教我们拼音字母“a”。我在课桌上画了一个“0”,那个长出的“豆芽”我怎么也写不好,徐老师于是把着我的手教我写。这节课我学会了写“a”。
上第二节课时,校长拿着从村里开过来的户口资料核实学生情况,核实到我时,发现我只有五岁,按规定显然不能上一年级,校长就让我搬着凳子回家了。
被学校撵出来,我非常难过,忍着眼泪,扛着凳子回家。母亲下地干活了,我把书包塞在灶屋里父亲冬天支起的大炭炉子里,就去找奶奶了。
奶奶听说我被学校撵回家了,就开始骂起来,拉起我的手就去学校。一路上奶奶都骂骂咧咧,也就几分钟就到了。迎面遇到住在奶奶家后面的吴老师,他喊奶奶表婶。奶奶指着他的鼻子就骂,说凭什么不让我上学。吴老师赔着笑脸,说是校长的主意。即使这样,奶奶还是又骂了他两句才拉着我去找校长。
按辈分,奶奶要喊校长叔叔,而且是同姓的叔叔。奶奶没办法骂校长。但奶奶仍大声地质问他凭什么不让我上学,学费我们会按时交。校长解释说年龄太小,学不会东西,跟不上班。奶奶说,不要求我学会什么东西,家里没人带,就全当你给我们带孩子了,学不好明年还上一年级。奶奶就站在教室里,一直拽着我的手,大声地跟校长理论,学生就围在周围看,有的是我本家的叔叔和姑姑,还过来拍拍我的头。
既然不要求学会什么,学费还能按时交,乡里乡亲的,校长最后终于同意我跟在班里玩吧,明年年龄够了,接着再上一年一年级。我终于成为正式的一年级学生了。
那时候,不上学的小孩比比皆是。而我有幸走进学校,就像为我的人生打开了一扇光明之门。
我并没有像校长说的那样因年龄太小学不会东西,我不仅学会了,而且学得很好。我是班里最小的学生,班里有好几个都是我同姓的姑姑和叔叔,年龄大我两岁、三岁,甚至四岁的也有,他们考试竟然考不过我。小五姑坐在我的旁边,平时做作业常常要抄我的答案。坐在我后面的小霞也要抄我的答案,可小五姑说只许她抄我的答案,别的人不给抄,小五姑的话我惟命是从,小霞来看我答案时,我就用手死死捂住不让她看,有时她还会抢我的本子,小五姑就会帮我。寒假过后,因为要交两块钱的学费,小五姑退学了。
后来我才知道小五姑退学对我的人生影响太巨大了,从此,我就开始了被同学欺负的日子,直到小学毕业。
第一个欺负我的就是小霞,每次小霞从我身边经过,都会用手指戳一下我的额头,恶狠狠地说一句:“可恶!”,我不敢反抗,也不敢告诉家里人。刚开始,每次被她骂过,我的眼里就会充满好一会泪水,到后来,我就开始忍受,也不再流泪。
我当时用的本子都是父亲从单位带回来的作废的操作票,正面用过了,背面却是白纸,且纸质很好,其他同学大多用草纸订成的本子,黄乎乎的,且非常粗糙。邻家本姓的一个叔爷是班长,他要求我每天向他进贡一张这样的白纸,如果不给,就罚我站。徐老师常常要回家干农活,他不在时,班长就行使他的权力,甚至可以打人。我害怕被罚站,只能每天向他进贡一张白纸。幸好,那时父亲带回来的纸还是非常充裕的。
每到夏天,父亲的单位就会发一把写着宣传标语的小纸扇,我觉得好玩就带到了学校,徐老师上课时就拿着我的扇子扇风,我感到非常骄傲,于是每天都把扇子带到学校给徐老师扇风。有时,徐老师讲完课,坐在座位上抽烟,发现没带火柴,他就会让我跑回家去帮他拿盒火柴来,点完烟之后他还会把火柴还给我。做这些事情,我心里都非常高兴,觉得自己好像比其他同学特殊了。
学会了认字,我就开始找书看,在我们家里,除了我的教科书之外,还有一本就是我母亲用来夹鞋样的画报。画报是十六开的那种,没头没尾,只剩十余页。为了防止书页继续破损,母亲在每页的边上都贴上了黑色的胶布,这样书就显得特别厚实。平时画报被母亲收起来不让我碰,只有当母亲做鞋要找鞋样时,我才有机会翻看它。画报是父亲当兵时带回来的,里面画多字少。我记得里面有好几页都是介绍一个叫陈爱莲的跳舞的女子。长大了,我才知道陈爱莲是我国建国之后非常著名的舞蹈家,那时,我不知道陈爱莲是谁,但我喜欢画报里她穿着彩色舞衣跳舞的样子。
每次母亲找鞋样,我都要把画报翻上几遍,有时,母亲还会斥责我不许看,害怕我把她的鞋样翻丢了。有时,母亲很长时间也不找鞋样,我也会趁母亲不在家时,偷偷地把画报找出来看。因为,母亲每次收画报时,我都特别留意。她就放在衣柜上面,以为高一点我够不着。其实我只要把家里的坐床(一种方的稍大的凳子)放在下面,再在坐床上摞一个板凳,我站在上面就可以够到。
我最初的课外读物就是这一本残缺不全的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