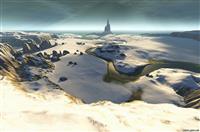我是个从小被长辈寄予厚望的孩子。除了秉承他们对我的光荣使命以外,我很少有其它方面的涉猎。
然而从童年的萧瑟中逃脱出来,我发现自己除了发展文学的梦想以外一无所获。有的仅是少数人怪癖的缺点。世人接纳钱钟书的骄狂,但他们不一定会接纳我。再加之学业的日益繁重,我渐渐对人生的辽远感到迷惘。
庆幸的是我,我到现在对生命之轻都未感到失望。生活气息的倾注自然占一个方面,但我想更多的是文学情怀的介入。
上小学的时候,我就可以写出一手很精妙的日记。每当语文老师有雅兴,点出几篇值得入眼的文章时,我几乎都有幸拔得头筹。它们是我少年时的风光之作。里面记载着的自己亦或邻里朋友之间洋洋洒洒的玩笑琐事,宛如成了众人茶余饭后孜孜不倦的谈料,饶有余香可寻,这些浅淡的回味勾勒出我人生中最初浓墨重彩的一笔。
到上中学的时候,我已经能够写出一篇流畅华丽的散文。虽然其中不免根植太多狂妄的设想,它到底是令我知足的。我得意洋洋地把它们写在作文本上交了上去,希望以一种年轻活跃的气象给予她们奢望的享受,然而我的老师在看了以后,冷淡地对我说:“孩子,你务实些吧!离了常规不一定就会高人一等的”。她对我的评价较为和气诚恳,且她属于中规中矩的人群,大抵是不提倡这种不切实际的谬论,故而我的的散文,一再被当作异类打了下来,从此一蹶不振。
总得算起来,散文与我的相识,也不过是一面之缘。
后来,我听取了她们的奉告,一股热转而写开了小说。小说是高贵的情感之流,它到现在依旧活艳艳地流淌于我的生命行迹当中。浇灌着我不断壮大的梦。我痴迷地投奔了小说,渐渐也就把散文忽略了下来,以至于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无暇去碰它,渐而渐之,也就把它忘却了。
我的记性于我而言,如同是迟缓笨重的机器,我总是在不停地召唤它良久以后,它才受宠若惊地跳了出来,附在了我的笔端。
可是我至今都清晰地记得自己写得第一部小说,它的确是个意外。然而这样的意外,我总是能够轻松的收敛自如,并且奋力地把它推向极致。这是一个微妙隆重的开始。它描述的是一位聋哑男孩,如何克服日常中时隐时现的磨难,从而成就学习上的巅峰的。我把写在初三一次月考的卷子上,期待以崭新的方式博的大家的欢迎,结果和预想虽是千差万别,可它依旧振奋了我继续进行下去的勇气。
读高二的时候,我写完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它来的较为突然,是围绕一对中年情侣展开的,写他们的悲欢离合,结局亦是同样的令人黯伤。尽管其中的情景大多数来源于我的假想,人物却是真真切切的“选购”于现实,这样强烈的形象对差,令我刚开头的时候就存在着不好的预感。我想我还是不大擅长驾驭这种类型的故事体裁的,故此彷徨的很。生怕它砸坏自己刚刚树立起来的招牌。然而当我鼓起自信,把它拿给我的好朋友看时,他们却深深地迷恋上了,这倒令我出乎意料。
一直以来我都是秉承为自己而写的念头,来支持这略微薄命的事业。这倒是颇像劳弗兰的风格,可我远没劳弗兰那么走运。以至于后来谈到王家卫,我的眼睛里几乎都嵌满了渴望的追随。我在想,一个人有追求固然是再好不过的事情,可偏偏弄得像是拖泥带水一般。纵然有好的心思,掺杂进来也甚为不爽。人就是这个样子,不顺心的时候,总乐于自己糟蹋自己。与其说断绝了生命,却尤为的可惜。活着真是一件困苦的事情。
我的父亲在看了我写的文章以后,对我说:“你多修改修改,争取写些特别的东西出来。”可是阅历欠佳的我,怎么可能也如张爱玲一般,把《半生缘》或者《连环套》里面的人生百态世故人情描绘的那么惟妙惟肖呢?但我想让我的文章像一个人一样,在这个世上体面地活着。我会为这个可敬的生命生生不息地奋斗。
当你喜欢上一样东西的时候,你就明白自己的能量远不止估算的这些。大多数的人对于自己的喜爱,既怕太过于接近,又怕太过于疏远,不知不觉地纠缠于其中,最后难以自拔。被这一心理所驱驰,久而久之,自己身上的锐利也就渐渐被磨光了。
但我不想如他们这样。 生命是一部精致的电影,里面排满了太多暗淡的片段 。
纪念 一二年十一月 写于西安